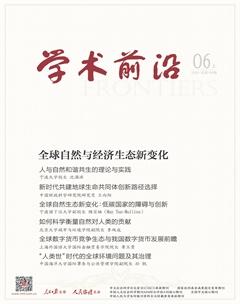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遺傳資源的法律適用
金夢
【摘要】由于存在巨大科研與經濟價值,國家管轄范圍外的海洋生物遺傳資源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2015年,聯合國大會決議制定了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以規范國家管轄范圍外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問題。但至今為止,圍繞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遺傳資源的法律地位與適用機制問題的爭議不斷。現階段,國際社會應當選擇更加務實的解決路徑,以積極應對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遺傳資源領域相關問題。
【關鍵詞】國家管轄范圍外? 海洋生物資源? 資源獲取? 利益分享
【中圖分類號】D99?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1.017
國家管轄范圍外區域(ABNJ)占海洋表面積的64%,占海洋總面積的95%。[1]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海洋知識的增多,海洋生物遺傳資源(MGRs)被發現具有巨大科學潛力與經濟價值,多年來一直是國際論壇中的熱門話題。然而,在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引發了對MGRs進行法律規制的思考。一方面,作為“海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文簡稱《公約》)并未提及MGRs相關內容。另一方面,專門針對MGRs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管轄權不包括國家管轄范圍外區域,導致ABNJ海洋生物資源陷入“無法可依”的困境。
為彌補這一法律空白,聯合國大會于2015年設立了解決相關問題的預備委員會,決定根據《公約》制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ILBI),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國家管轄范圍外區域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包括對生物遺傳資源的管理。[2]但迄今為止,有關ABNJ生物遺傳資源的適用原則與利益分享問題,仍懸而未決。
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遺傳資源的法律適用爭議
自1992年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國際社會始終關注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遺傳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問題。[3]其法律地位與適用法律制度問題,本質在于ABNJ的MGRs是適用公海自由機制的“公有物”,還是適用人類共同繼承遺產原則(CHM)的“全人類共有資源”。
《公約》第十一部分與《關于執行1982年12月1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一部分協定》共同構成管理國際海底區域活動的法律規范,明確將“區域”定義為“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底土”,與公海水域進行區分。“區域”內的活動由國際海底管理局負責監督,任何國家、集團或個人未經允許,不得自行勘探或開發。《公約》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區域”礦物是“人類共同繼承遺產”,并應確保所有人都從中受益。具體來說,CHM為“區域”承包者設定具體法律義務,包括禁止將“區域”或其資源據為己有,專為和平目的利用“區域”,“區域”活動應保護海洋環境,及資源應惠及全人類。[4]最后一項義務專門針對“區域”內的礦產資源,要求“區域”活動應考慮所有國家和所有人,而不論其地理位置,特別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需要,并在無歧視基礎上,公平分配財政或其他經濟利益,[5]使任何國家都不能成為“區域”資源的唯一獲利者。據此,適用CHM機制意味著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遺傳資源應與“區域”礦產資源活動一樣,獲取與開發行為均應受到某一國際組織或機構的嚴格管理,并與全人類共同分享利益。
《公約》關于CHM機制的規定與公海自由機制形成鮮明對比。第八十七條明確規定,“公海對所有國家開放,無論其為沿海國或內陸國”。盡管之后第八十九條規定,任何國家都不能主張對公海的任何部分享有主權。但對公海發現的資源,各國仍可自由獲取。如,公海漁業資源。捕魚權一直采用先到先得原則,為公海發現MGRs適用公海自由機制提供了先例。
事實上,堅持公海資源自由獲取的觀點忽略了現實情況。盡管捕魚自由是公海自由之一,但魚類資源并非取之不盡,過度捕撈嚴重削弱了公海魚類種群數量,最終推動1995年《魚類種群協定》的生效,一定程度限制了捕魚自由。截至2020年4月1日,已有90個國家和歐盟批準該協定。[6]可見,公海自由并非絕對自由,而是有限度自由,包括“不能主張主權”,必須適當顧及其他國家利益及《公約》所載保護海洋環境和海洋科學研究等諸多義務。
適用的法律制度比較
對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遺傳資源應適用的法律機制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呈現截然相反的觀點。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從鼓勵資源開發與科學研究角度出發,主張適用公海自由制度。而77國集團和中國則從全人類利益角度考慮,主張適用人類共同繼承遺產制度。
適用公海自由原則的法律剖析。公海自由原則的支持者,包括美國在內的某些發達國家認為,由于《公約》第十一部分并不包含MGRs,所以對其獲取和開發活動應適用公海自由原則。對當前正談判的新的法律文書,美國認為其只能約束“區域”內的MGRs,而不應對公海水域內MGRs加以限制。并且這種分別管理方式,在《公約》中有先例可循。即便未來正式出臺相關法律文件,美國態度表明它只承認其對“區域”內的MGRs有約束力。
這一觀點存在明顯缺陷。首先,對位于公海水域和深海海底MGRs適用不同的管理機制給物種分類帶來困難。實踐中,有些物種既生活在海底也生活在水域中,遷徙物種到底屬于位于何處的MGRs,取決于在其生長期哪個階段被捕獲,而其本質相同。如對不同地理位置MGRs采用不同管理原則,會導致對同一物種適用不同法律制度。《公約》對公海與國際海底區域劃分主要從法律層面考慮。事實上,由于海水的流動性以及海洋的特殊構造,在地理層面對兩者進行劃分恐怕不切實際。因此,對位于公海水域及國際海底的MGRs分別適用不同法律機制既無法律依據,也缺乏現實可行性。其次,美國主張適用公海自由原則前提假設是,《公約》關于公海自由清單并不詳盡,只要未被明文禁止,都應列入公海自由范疇。然而,第八十七條“除其他外”用語表明,公海自由清單并非如美國所說那樣無限開放。再次,由于MGRs利益主要基于知識產權,如專利所賦予的專有權,就無理由反對知識產權在該領域的適用。而知識產權的排他性并不要求利益分享。因此,公海自由制度實際排除了對MGRs利益分享。這對現階段無法參與該領域活動的國家來說,非常不公平。
適用人類共同繼承遺產原則的可行性分析。關于如何管理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多樣性與生物遺傳資源,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立場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包括G77和中國在內的幾個發展中國家向預備委員會提交聲明表示,在新的法律文書中應將MGRs作為人類共同繼承遺產加以管理。[7]包括公平分享MGRs開發利益,同時兼顧發展中國家和無法獲得該資源國家的合理需求。G77和中國的觀點表明,利益分享應既包括貨幣分享,也包括非貨幣形式分享;還應考慮“遺產”一詞所暗含留給后代的利益;應包括獲取MGRs具體規定,并需建立統一、完整的國際制度對開發活動實施監督。
CHM是為國際海底區域礦產資源特別設計的概念,但并不表示ABNJ的MGRs不能借鑒。適用CHM優勢在于,該原則既包括對資源獲取的管理,也涉及資源利益公平分享,既能有效保護生物遺傳資源,也能實現為全人類利益開展活動的目的。
爭議問題的解決路徑
有關爭議本質屬于意識形態層面的沖突,而非法律層面的較量,很難通過談判加以解決。因此,當下應考慮是否可暫且擱置關于法律制度方面的爭議,就已具共識的問題先行談判,將重點集中在現實措施方面,以及時應對該領域產生的實際問題。
擱置爭議,就共識問題先行談判。各國在這一問題上立場大相徑庭,又因摻雜政治因素而難以妥協。如何才能繞過關鍵問題上的分歧?是否能暫且擱置爭議,轉而就容易達成共識的內容先行談判?對此《南極條約》存有先例。其主要成就之一是處理有關南極領土要求的實際和潛在爭端方式。阿根廷、澳大利亞、智利、法國、新西蘭、挪威和英國都聲稱南極洲部分地區是其主權領土。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荷蘭和印度雖是《南極條約》締約國,但不承認其中任何一項主張的有效性,而俄美都保留對南極洲提出主張的權利。盡管在對南極洲各種主權要求問題上存在根深蒂固的觀點,《南極條約》第四條依然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來調和在主權問題上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即不討論與主權歸屬有關內容。[8]
關于人類共同繼承遺產問題,是否可采用類似方法?特別受到《南極條約》第四條第二款啟發。如,擬設置如下條款,對所有國家均適用:注意到各國對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海洋空間中發現的遺傳資源地位存在分歧,在人類共同繼承遺產或其他情況下,各締約國同意在本條約(議定書或協議)有效期所發生的一切行為或活動,不得構成主張、支持或否定對國家管轄范圍外遺傳資源主權要求的基礎,不論其是人類共同繼承遺產或具其他地位,都一致同意該遺傳資源可持續管理、獲取和利益分享應受本條約(議定書或協定)規定的制度管轄。
客觀上,這樣的條款可能有助于彌合在共同遺產問題上的意識形態分歧,[9]能促使談判重點集中在資源獲取和利益分享及其他更重要資源保護與監管層面等實質性問題上,如設立海洋保護區,促進各國技術能力建設和海洋生物技術轉移,等等。
加強軟法義務的履行與實施。現有全球、區域和部門組織對國家管轄范圍外大部分人類活動發揮了監督和管理作用。航運、漁業和深海采礦是國家管轄范圍外區域海洋環境及其生物多樣性最為關注的活動。通過與海洋治理有關協議、文書和決定,每個領域均受到不同程度監管。包括國際性海洋組織,如國際海事組織和國際海底管理局;也包括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如國際大西洋金槍魚養護委員會,東南大西洋漁業組織和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其與更專注于促進和保護區域內生態系統的機構并存,如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委員會,及針對特定物種保護的國際捕鯨委員會和《瀕危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締約方會議。其他區域組織包括根據聯合國環境署“區域海洋”計劃頒布的區域海洋組織,及諸如東北大西洋漁業委員會等海洋保護組織,具有跨部門廣泛權限,對國家管轄范圍外區域具有不同程度約束力或責任。
任何區域性或全球性國際組織,都要求締約國履行相應國際義務,但并非強制性,大部分情況下僅具軟法效力,需各締約國自覺遵守。實際上,一個國家往往會參與多個國際組織,而各個國際組織的宗旨與任務常常出現交叉或重疊,使該國需履行不同國際組織所規定的多個相同或類似國際義務。被概括為預期義務的增強,而非施加沖突的義務。[10]如,當各國開始將瀕危物種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限制野生動物貿易時,各國并未破壞糧食及農業組織促進海洋資源保護和管理任務,而是認識到需通過多領域措施來支持保護和管理目標。即使有些國家是某一機制成員而另一國家不是,依然加強了各組織間的合作與協調。同樣,加強各國在國際組織中與生物資源保護有關條約義務的履行,有助于實現保護與管理的最終目標。
結語
國家管轄范圍外區域總面積遠大于國家管轄范圍內所有區域總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國家管轄范圍外的生物遺傳資源領域,現有國際法律規則卻無法提供有效規制。盡管預備委員會已著手擬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律文書,但各國基于政治、經濟原因所持立場不同,至今未能就已倡導的提議達成共識。
為推動下一步談判和協商程序,采用“迂回戰術”可能更具可操作性。若各國能暫且擱置就“適用法律制度”的爭議,將談判重點集中在利益分享方式、生物資源保護多元化工具等方面,或許更易取得實質性進展。另外,當下應采取更加務實的措施,以應對生物遺傳資源相關問題,包括敦促各國對現有國際條約義務的履行,加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法在法律解釋與法律適用方面的協調與互補,進而緩解制定新法的壓力。
注釋
[1]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rea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2]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Knowledge Hub, Secon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BBNJ.
[3]Broggiato A.; Amaud-haond S.; Chiarolla C.; Greiber T.,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ridging the gaps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 Marine Policy, Vol. 49, No. 3, 2014, pp. 176-185.
[4][5]《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三七條、第一四〇條、第一四一條、第一四五條、第一四〇條,1982年。
[6]"Chronological lists of ratifications of accessions and successions to the Convention and the related Agreements", Oceans &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7]"Group of 77 and China's written submi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United Nations.
[8]《南極條約》第四條,1959年。
[9]Leary D., "Moving the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Debate Forward: Some Reflecti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27, 2012, p. 442.
[10]Young M. A. and Friedman A.,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Regim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Vol.112, 2018, p. 125.
責 編/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