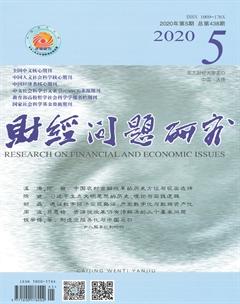資源稅改革仍有待解決的三個基本問題
摘要: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資源稅改革加速,資源稅法實施在即,但我國資源稅制度在功能定位、資源利益關系調整以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三方面仍存在內生缺陷。因此,應基于資源租、稅、費聯動機制,平衡資源租、稅、費利益分配失衡格局,校準資源稅功能定位。優化資源稅制要素設計,漸進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設定合理的資源稅計稅依據、征收方式和稅率標準,為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創造有利條件。
關鍵詞:資源租、稅、費聯動;資源稅改革;利益關系調整;功能定位
中圖分類號:F8104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20)05007408
推進資源稅改革不僅是牽涉資源稅功能定位校準的理論問題,更是妥善處理資源收益分配格局的實踐制度設計問題。2019年8月,經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法》將于2020年9月1日施行。值得實務和學界審慎思考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密集資源稅改革,不僅吸納了學界政策建議,而且也積極回應了資源稅制度缺陷。但彌合資源稅擴圍分歧、理順資源租、稅、費聯動關系進而確定資源稅功能定位、資源稅是否作為地方主體稅種等問題還遠未達成共識,使得資源稅立法缺乏堅實基礎。而且,總體來看,我國現行資源稅費制度在合理分享資源收益、保護環境以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等方面仍有待加強。若這些問題沒有被妥善解決,資源稅制度的內生缺陷有可能隨著資源稅法實施而被固化。
一、資源稅功能定位校準
我國現行資源稅基本延續《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1993 年出臺草案、2011年修訂)構建的整體制度框架。審視我國自1984年以來的資源稅費制度和政策嬗變進程,有助于厘清我國資源稅功能定位邏輯,并為進一步校準我國資源稅功能定位提供鏡鑒。
(一)我國資源稅費制度演進進程
1資源租、稅、費并存制度建設
首先,1984—1993年,我國建立資源稅費并存管理體制,主要處理政府與企業分配關系。一方面,1984年,我國正式建立起針對原油、天然氣和煤炭企業的資源稅制度。考慮到資源稅征收過程中針對企業銷售利潤率超過12%的部分進行超率累進征收,郭焦鋒和白彥鋒[1]、盧真等[2]、李勝和李春根[3]以及張德勇[4]認為,這個階段的資源稅制度發揮著調節資源級差收入的職能。另一方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條例》(1982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1986年),遵循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原則,不僅開采海洋石油資源應征收礦區使用費,而且,開采礦產資源應繳納資源補償費。此后,我國國家礦產資源財產權益實現方式探索進一步定型化。這集中體現在,《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1994年)確定礦產補償費率,《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1996年修訂)確定礦產資源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應該注意到,出于緩解國家財政資金緊張問題的需要,與探索國有企業“利改稅”進程相伴,緊密圍繞調整稅收與國有企業利潤以及國家與資源企業之間資源收益分配關系,區分基于政治權力參與資源產品剩余價值分配亦或基于資源所有權取得資源補償收入,亦即資源租和資源稅關系中的國家身份問題并未顯得過于急迫。
其次,1994—2013年,以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為重要時間節點,我國資源稅制度改革,由此前主要解決政府與國有企業以資源租和資源稅為表現形式的自然資源收益分配關系,轉變為主要處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資源收益分配問題。一方面,除海洋石油資源稅外,其他資源稅收入都劃歸地方政府。周波和范叢昕[5]指出,與此前礦區使用費以及石油特有的特別收益金歸屬中央財政收入相反,1994年以來各項資源租費,如礦產資源補償費、礦區使用費、探(采)礦權使用費、探(采)礦權價款等專門稅費,均系中央與地方比例分成收入或按中央與地方隸屬關系進行分配。另一方面,雖早在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就規定“普遍征收”原則,但考察我國資源稅制度建設實踐可以發現,普遍征收原則并未被有效恪守和落實。相反,資源稅征稅范圍呈現出漸進擴圍趨勢。具體而言,繼鐵礦石在1991年被納入資源稅征稅范圍后,進而煤炭、天然氣、石油、其他非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礦、有色金屬礦原礦和鹽七類自然資源,長期以來是我國資源稅核心稅目。與此相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四條規定,“未列舉名稱的其他非金屬礦原礦和其他有色金屬礦原礦,由省級人民政府決定征收或者緩征資源稅,并報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備案”。因而,全國開征條件不具備進而未能納入資源稅稅目的非金屬礦原礦和其他有色金屬礦原礦開征權被下放給地方政府,固然可能因為能形成的稅收收入相對較小未能納入資源稅征收范圍,但從地方政府層面看,則可實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功效。比如,山東省針對頁巖、天然礦泉水、建筑用砂、粘土和其他建筑石料征收資源稅,而廣西和陜西等省亦針對非金屬礦原礦和各種礦石征收資源稅。
表1我國礦產資源租費制度一覽
類型依據對象及方式政府間分享礦區使用費《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條例》(1982)、《開采海洋石油資源繳納礦區使用費的規定》(1989)和《中外合作開采陸上石油資源繳納礦區使用費暫行規定》(1990)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的中國企業、外國企業、開采陸上石油,按照每個油、氣田日歷年度原油或天然氣總產量,超過起征點的部分在1%—125%范圍內超額累進征收;繳納礦區使用費的企業不再繳納礦產資源補償費且暫不征收資源稅中央財政收入礦產資源補償費《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1994年)開采礦產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礦產品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從價計征,費率為05%—4% 中央與省、直轄市5∶5分成,中央與自治區4∶6分成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礦產資源法》(1996年修訂)、《礦產資源勘查區塊登記管理辦法》和《礦產資源開采登記管理辦法》前者依勘查年度逐年繳納:1—3年繳納100元/平方千米/年;從第4年起每年增加100元/平方千米/年,最高不超500元/平方千米/年;后者按1 000元/平方千米/年逐年繳納探(采)礦權使用費分別由國務院和省級礦產主管部門收取,繳入中央和省級國庫探礦權采礦權價款《礦產資源勘查區塊登記管理辦法》、《礦產資源開采登記管理辦法》申請國家出資勘查并已經探明礦產地的探(采)礦權申請人繳納評估確認的國家出資勘查形成的探礦權和采礦權價款中央和地方按2∶8分成,省以下分成由省級政府確定石油特別收益金《石油特別收益金征收管理辦法》(2006)銷售國產原油月加權平均價格超過一定水平獲得超額收入,起征點為40 美元/桶,20%-40%范圍內5級超額累進從價定率計征中央財政非稅收入,納入中央財政預算管理資源性收費、基金項目礦業企業繳納礦產資源勘查登記費、采礦登記費等中央部門行政性收費,以及各地設立的水資源費、土地復墾費、防止水土流失費、森林植被恢復費、育林基金、林業建設基金、林木采伐許可證費、征地占用林木補償費、排污費、價格調節基金等;以山西省為例,煤炭領域中央批準行政事業性收費15項、國定政府性基金6項、省定經營服務性收費2項、其他收費3項。
結合以上兩方面來看,分稅制財政體制建立后,主要資源稅收入歸地方所有,以及中央與地方資源收費分享向地方政府傾斜,都具有彌補地方政府財力相對下降進而降低地方政府反對改革阻力的目的。此后,稅額標準調整改革,原油、天然氣從價計征在新疆試點、擴圍至12個省區,以及在2011年推向全國,進一步放大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效應。就此而言,除調節資源級差收入外,在我國資源稅費制度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使得地方政府獲得補償收入、增強地方政府財力的財政收入職能。
2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資源租、稅、費體系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資源租、稅、費體系改革呈現出:資源稅不斷強化、資源費在弱化而資源租角色和具體實現形式未明確的鮮明特點。
首先,加速推進資源稅進程。其一,持續推進資源稅計征方式改革。除水資源從量計征改革由河北試點擴圍至北京、天津等九省份外,我國主要針對經濟價值較大的金屬和非金屬礦產推進從價計征。比如,2012年兩廣地區試點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改革,2013年在部分地區針對部分金屬和非金屬礦資源進行從價計征改革試點,2014年和2015年煤炭以及稀土、鎢、鉬資源分別從價計征,2016年從價計征覆蓋到《資源稅稅目稅率幅度表》列舉名稱的21種資源品目和未列舉名稱的其他金屬礦。與市場價格聯系更為緊密,從價計征資源稅,不僅能夠使得資源稅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資源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真實價值,而且,使得政府可以從資源市場價值增值中分享到更大份額的經濟收益。其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維度,增強向省級人民政府資源稅稅政管理權分權。各省級人民政府被授權根據本地區森林、草場、灘涂等資源開發利用情況,在規定稅率幅度內提出開征資源稅具體方案建議,上報國務院批準后實施。全面推行“營改增”致使地方政府缺失主體稅種背景下,資源稅向省級政府稅政管理權分權以及推進從價計征,都具有充實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客觀效果。
其次,與加速推進資源稅進程相伴隨,以相應資源稅適用稅率由5%提高至6%為置換條件,著力解決稅費重疊、功能交叉問題,加速資源“清費立稅”工作。其一,資源補償費費率不僅多年未曾調整,相反,原油、天然氣、煤炭和礦產資源補償費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第五條規定相沖突的,因而,應盡快通過資源法修訂予以確認。其二,為銜接資源稅與現有資源收費制度安排,以2011年11月1日為界,若此前已簽訂中外合作油氣田及海上自營油氣田合同,則繼續繳納礦區使用費而不需要繳納資源稅,若此后簽訂的合同,只需要繳納資源稅而不需要繼續繳納礦區使用費;而開采海洋油氣資源的自營油氣田,同樣只繳納資源稅而不再繳納礦區使用費。其三,清理取消各類與資源有關的收費和基金項目。這不僅包括與煤炭、原油和天然氣等資源有關的價格調節基金,而且,也包括省以下各級地方政府違規設立的各類收費基金。如新疆地區煤炭資源地方經濟發展費、青海省原生礦產品生態補償費和山西省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等。
審視2016年以來我國資源清費立稅改革可以發現,不僅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被清理,而且,礦產資源補償費和價格調節基金等各種資源收費,亦與其他收費基金一起并入資源稅。應注意到,資源稅改革并非簡單的費改稅,資源稅一定優于資源費的思維定勢是片面的,而且,無論取消不合理收費,還是實現資源稅環境保護政策功能,都不足以替代或否定國有資源收益權。因此,應警惕資源稅費交叉重疊以及為加速推進資源稅改革進程而忽略資源所有權價值。
(二)與我國資源稅費制度演進進程相伴的資源稅功能定位嬗變
1資源租、稅、費的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
資源租、稅、費都存在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并非簡單替代關系,相反,應是并行關系。根本而言,依據國家財產所有權,資源必然參與經濟系統生活的初次分配,資源租是資源收益權的體現形式;對應地,體現政治公權力和管理權力,資源稅及與資源有關的收費則參與資源收益再分配。更具體結合資源轉讓、生產經營及消費各環節的制度現實進行闡釋,可以發現:
首先,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的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支配和使用權力的法律制度依據,不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條“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宏觀界定,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也分別都在第三條界定了礦產資源和水資源的國家所有。從產權理論發展趨勢看,張富剛和李凱[6]認為,以所有、占有、處分和受益權利為核心的資源產權權利集束,并不必然集中于所有人統一行使,相反,具有可分離性,即資源所有權與使用權、收益權相分離。因此,施文潑和賈康[7]認為,資源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情況下,資源經營者和使用者應就其開采、使用的稀缺性國有資源,在權利轉讓環節進行經濟權益補償。這就是資源租。因而,資源租事實上是資源國家所有的產權權利集束中收益權的實現形式。
其次,資源讓渡給生產經營者后,國家依據政治公權力針對采掘、冶煉加工和運輸過程征收資源稅,實現外部性內部化和可持續發展。這構成資源稅的理論基礎。就外部性而言,資源開采開發過程中往往伴隨地面塌陷、泥石流、山體崩塌,破壞礦產資源地區水源、大氣、土地、植被等生態環境。劉明慧和趙敏婕[8]集中于礦產資源研究發現,2010年我國資源開發排放的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分別占全部三廢排放的843%、236%和4029%。資源開采者會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將成本轉嫁他人。就可持續發展而言,資源不僅包括可再生的水和地熱、可更新的生物和森林以及不可再生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呈現范圍廣、形態多但稀缺性各異的特點。蒲方合[9]指出,到2020年,我國45種主要礦產資源儲量仍能保證需要的只有6種。或因為部分稀缺資源未能形成有效的排他性產權,或在當代和后代人公平維度,資源所有者為當代人收入和效用賦予過高權重,對重視子孫后代權益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貫徹不力,產生資源消耗的代際負外部性。Hotelling[10]以及高洪成和徐曉亮[11]都指出,資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性難以通過市場定價機制得到充分體現,其市場均衡價格低于“真實”水平。依據資源價值構成理論,資源價值的恰當縱向時間序列配置,可以彌補代際內和代際間資源開發利用成本。因此,征收資源稅,不僅可以通過增加資源開采者和使用者成本來內部化資源開采活動外部性,彌補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背離,而且,亦可籌集資金用于改善和保護環境。
最后,遵循成本補償和非盈利原則,政府可以在管理環節征收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形式的資源費,一則補償政府提供的部分準公共產品和服務成本,避免過度消費,二則增加違反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成本。
從資源收益獲益主體以及使用用途看,張海星[12]認為,資源租、稅、費都由國家享有,最終體現為政府收入,且都用于實現公共利益。因而,資源稅表面上具有“租”的相貌。
2我國資源租、稅、費制度未能有效維護國家資源的財產權益
在我國資源租、稅、費制度體系中,礦產資源補償費、探礦權采礦權價款以及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資源租性質。但進一步深入分析發現,這些都不是資源的真正有償價值,至少不是資源的完全價值補償。
首先,就礦產資源補償費而言,雖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其在設計之初就被賦予了部分地實現資源所有權收益的資源租職能。但從實際使用情況看,按照《礦產資源補償費使用管理辦法》(財建[2011]809號),除用于礦產資源勘查以及礦產資源保護外,礦產資源補償費還用于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部門經費補助。這與國家憑借國有資源所有權對礦產資源開發者收取耗竭性資源的財產權益補償存在根本差異。因而,周波和范叢昕[5]認為,文正益[13]、范振林和馬茁卉[14]以及蒲方合[9]等主張的資源補償費為租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相反,礦產資源補償費本質上卻兼具資源稅和資源收費的某些屬性。這是因為:其一,從測算公式所對應的影響因素看,資源補償費由礦產品銷售收入、補償費率和開采回采率系數三者共同決定。鑒于礦產資源開采回采率系數具有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功效,因而,資源補償費事實上具有針對礦產資源開采污染進行補償收費的功能,這就與資源稅承擔的保護環境、資源節約功能重合。從這個意義上說,礦產資源補償費并入資源稅且同在開采銷售環節由稅務機關征收管理就是合理的。其二,資源補償費用于滿足相關部門機構運轉經費之需,不僅未真正反映資源國家所有權的權益金,而且,被納入行政事業性收費名下而異化為部門利益,這恰是典型的資源收費。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與企業取得資源權后即有權開采國家所有資源對應,國家同時轉讓資源勘查投資收益以及資源內含的所有者權益。就探礦權采礦權價款以及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而言,某種程度上,都具有權利金的共同屬性,差別在于,分別針對資源權轉讓進行一次性和有效期內按年度征收。考慮到探礦權采礦權價款只限于“申請國家出資勘查并已經探明礦產地”的制度規定,只針對國家出資勘查形成的探礦權采礦權收費,事實上只向國家支付了地質勘查投資回報,而沒有為資源價值付費。對應地,非國家出資勘查形成的礦業權不收取礦業權價款,以及國家出資勘查形成的礦業權可以申請和協議方式出讓,不僅沒有為資源價值付費,甚至也未支付地質勘查投資回報。
3資源稅功能定位校準
資源稅功能表現為征收范圍、計征方式、稅率標準、清費立稅以及下放部分權限給地方政府等內容,我國資源稅政策嬗變,在最初調節資源級差收入的基礎上,功能定位逐漸擴展到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以矯正負外部性、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從國有資源占用和開發權讓渡中取得財政收入,以及逐漸打造成地方稅等多重職能。
不論1984年建立資源稅制度,還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再到2011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都將調節資源級差收入作為重要目標。從設計初衷來看,根據地段、位置、交通、豐度、品味、噸位和開采難度等資源稟賦條件差異,針對不同資源產品和開采單位,基于不同稅額標準進行多級超率累進調整。由于計算復雜、稅收成本較高,我國在1986年將計征方式改為對應稅產品從量定額征收。從量定額征稅不能反映資源產品價格變化,安體富和蔣震[15]認為,無法體現稅收量能負擔原則,政府亦難以分享資源市場繁榮帶來的收益,與丁丁等[16]所指出的資源稅稅率過低以及張海星和許芬[17]所強調的資源稅征收范圍過窄等問題交織在一起,資源稅調節級差收入和資源配置作用趨于減弱,資源節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目標也受到影響。而且,以資源稅調節資源級差收入,存在混淆國家政治權力和自然資源所有者兩種不同身份依據的理論缺陷。
吳迪[18]認為,承載眾多政策功能的資源稅,頗似兼具流轉稅、所得稅、行為稅、生態稅特性的“萬能稅種”。試圖使資源稅承擔多種職能的良好愿望可以理解。但以此主導資源稅改革設計,劉植才和劉榮[19]以及馬蔡琛和李宛姝[20]認為,則很容易使得資源稅改革迷失在多元目標斟酌取舍之中,導致制度設計復雜化和征稅阻力強化。因而,需要科學校準資源稅功能定位,為促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應發揮資源稅完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引導生產經營者行為、維護代際資源利用公平和校正外部效應等政策功能。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考慮到資源補償費以及探礦權采礦權價款和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都不是真正的資源租且已并入資源稅,國家資源的財產權益沒有得到有效維護,國家礦產資源所有權被虛置。因而,應將推進資源稅費改革構筑在明晰資源租、稅、費征收依據及厘清資源租、稅、費關系基礎之上。進而,促進國家以資源所有者身份實現所有者權益,調整中央、地方與企業利益格局。
二、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資源利益關系調整
資源稅制度牽涉政府與企業和居民、中央與地方政府、財稅部門與行業主管部門等眾多利益主體,國家與資源開采企業分配關系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利益關系緊密相關。我國2%—10%幅度的煤炭資源稅率,就是兼顧煤炭資源分布不均衡進而對各省市煤炭資源財政收入規模和比例的差異性影響而設定的。
(一)將資源稅界定為中央政府專有稅種
自資源稅制度設立之初,除海洋石油資源稅作為中央政府專有稅收收入外,資源稅都被作為地方政府專有稅,構成地方政府專有財政收入。置于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特定歷史背景,事實上,資源稅承擔著強化地方稅體系建設進而增強地方政府支持分稅制改革的職能。這本是資源主要集中在經濟落后省市、資源稅征收范圍有限、資源稅占比較低進而對國家財力格局影響不大且我國資源約束特征不明顯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從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資源稅費改革來看,鑒于礦產資源補償費被取消以及部分資源收費和基金被歸并到資源稅,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按照某種比例分成或按行政隸屬關系分別繳入中央和地方政府國庫的各項專項收費收入,亦將在資源稅費改革后歸地方政府所有。在此背景下,繼續將資源稅作為地方政府專有稅種則值得審慎斟酌。
首先,將資源稅作為地方政府主體稅種,存在理論沖突并缺乏法律依據。與制度事實相對應,學界贊同將資源稅作為地方政府專有稅種的理由主要包括:施文潑和賈康[7]認為,陸上礦產資源具有只能就地開發、稅基更顯地域化等屬地性特點決定,而張海瑩[21]認為,這是出于發展中西部地區經濟、充實當地財政收入考慮。此外,馬蔡琛和李宛姝[20]建議將資源稅作為專門目的稅,強制性地規定,地方財政從資源稅收入中提取70%—80%建立專款專用的資源代際補償基金,以補償資源損耗和環境破壞。值得注意的是,將資源稅作為地方政府主體稅種,事實上對應著,自然資源國家所有被固化為地方政府所有的實現形式,中央政府代表國家享有的自然資源收益權被異化為資源所在地地方政府收益。周波和范叢昕[5]指出,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四十五條“國有財產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相矛盾。事實上,即便能如馬蔡琛和李宛姝[20]所建議的那樣通過指定資源稅使用用途增強地方政府專有稅種的正當性,但“收支相屬”又使得本就在地方政府一般性財政收入中占比較低的資源稅收入比重進一步降低,進而對于增強地方政府財力并沒有根本性影響。
其次,從多層級政府框架視角看,地方政府擁有資源稅征稅權將在地方政府之間引致消極影響。這是因為,在我國廣袤的幅員范圍內,自然資源呈現出區域儲量分布極不均衡態勢,在此情況下遵循資源產地課稅原則,一方面,受到獲取資源稅收入激勵,對于企業掠奪式乃至破壞性開采和經營自然資源行為,資源稟賦充裕大省有可能采取默許乃至縱容措施,而這將導致資源低效過度開采,加劇資源代際間不公平;另一方面,將資源稅作為地方稅種,使得資源稟賦大省能夠將資源稅稅負輸出到資源消費所在省份,這進而帶來資源產地與資源消耗地之間的橫向稅收分配失衡。
相反,樓繼偉[22]認為,應基于堅實的資源國有產權依據以及資源稟賦地區間分布不均勻的現實情況,將資源稅調整為中央政府專有稅。這不僅能夠在資源開發利用、生態保護和穩定稅負等方面發揮中央政府統籌全局的優勢,而且,也有利于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資源產地與資源消耗地政府之間資源收益關系。重要的是,應建立相配套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合理分配的資源稅收入制度。其一,如劉尚希[23]觀點,為防范資源枯竭的公共風險,應在全國層面建立資源儲備基金,著力解決資源的代際公平問題。其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資源事權和支出責任框架內,建立中央政府對資源產地政府的財政專項轉移支付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2014 年修訂)第六條,我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承擔確保本行政區域內環境質量職責。資源開采、加工和運輸過程中會造成土地占有、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進而增加資源地政府履行環境質量事權對應的支出責任。因此,應將資源開采、加工和運輸過程中所產生的外部性程度以及地方政府與資源密切相關的環境治理績效作為重要標準,確定中央對資源地地方政府專項轉移支付額度。
(二)完善資源收益歸屬結構性調整
從資源的自然屬性角度看,類型豐富、特性不同和功能分異,往往成為不同政府職能部門承擔專業的資源管理、規劃、調查和確權登記等相關職責的理由。與承擔專業資源管理職能相對應,承擔資源管理職能的各政府職能部門,同時成為資源收益體系中的重要利益主體。因此,國土資源、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水利、農業、林業以及海洋等各政府職能部門,事實上都參與資源收益分享。譬如,以收取水費、耕地開墾費、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灘涂資源使用費、征地林木補償費等資源性收費形式。這實際上也意味著,資源管理制度并非簡單的資源稅設立、征繳及使用管理問題,相反,應在協調和權衡各資源有涉職能部門發揮專業管理職能及尊重合理利益訴求的基礎上,調整資源收益歸屬結構。其一,2018年,我國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關于資源管理進行重大體制調整,成立自然資源部。應基于機構職能進一步整合優化內設部門職責,在落實國家所有資源資產所有權人權益的基礎上,使資源主管部門承擔監測資源數量、共享資源涉稅信息、配合資源稅征收工作等義務,為資源稅稅款征繳提供來自資源主管部門的專業支持和配合。譬如,建立礦產資源開采回采率、水資源取水量以及森林資源砍伐林木數量等專業指標和依據。其二,在資源收費清理并部分改革為資源稅的特定背景下,曾由多部門分散征收并作為部門履職經費的相關收費基金亦在清理之列。因此,應基于自然資源部各內設部門職能,通過規范的部門預算給予其承擔專業資源稅管理以及資源稅征繳協力所需經費支持。
三、建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資源稅制度
因牽涉眾多資源性產品價格聯動效應,資源產業在發揮重要保障和支撐作用的同時,亦會具有顯著的資源約束特征。趙凡[24]指出,以礦產資源為例,我國一次能源、工業原材料、農業生產資料以及工業和居民用水的90%、80%、70%和30%均源于此。為推進工業化進程,我國設置整體偏低的資源稅稅率,將部分發展成本轉嫁給生態環境,使得資源及資源產品價格長期低于其社會成本,人為扭曲資源價格市場形成機制。微觀市場主體資源要素投入決策,在源頭就埋下非市場機制運作的隱患,經濟增長對資源要素和產品投入形成路徑依賴,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發揮。因此,資源稅改革應堅持市場化導向,優化資源稅制要素設計,正確處理政府與資源企業利益關系。
(一)全面實行資源有償取得制度
利改稅之前,資源主要由國有企業開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礦產資源無償取得制度可以通過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實現國有資源財產權益。即便探索國有資源有償使用,但我國企業無償或者繳納極低費用就獲得資源開采權,與資源稅稅額標準偏低、征收范圍窄和計稅方式不合理結合起來,不僅使資源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比重很低,而且,李冬梅和馬靜[25]認為,由于對資源開采企業約束力較弱,阻礙了資源稅發揮資源節約和合理補償功能。為維護資源國有收益權,應在自然資源部主導下,針對我國資源開采和使用權配置中存在的行政與市場“雙軌”出讓狀況,通過建立科學的自然資源產權制度體系,推進競爭性出讓方式主導資源配置。
首先,基于資源儲量以及當前和未來潛在經濟社會價值等客觀因素考量,建立完善科學的資源評估機制和競爭性定價機制,確立資源開采和使用權一級市場招投標程序和標準。其一,應針對新進入市場的資源開采和使用權,引入招標、拍賣和掛牌等市場化出讓方式。就此而言,水、國有森林和草原都可以作為突破口。其二,針對已存在的以行政方式出讓的資源開采和使用權,在規定時限內妥善對接,漸進替代為市場化出讓方式。這主要表現在煤炭、石油等礦業權上。
其次,完整的產權權利集才能確保產權實現真實價值。因此,應建立規范的資源開采和使用權二級市場,確保資源開采和使用權可以順暢地流通和轉讓。
(二)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
類礦產資源,以及各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四條規定對“未列舉名稱的其他非金屬礦原礦和其他有色金屬礦原礦”征稅外,資源稅征稅范圍過窄,對共伴生礦普遍不征稅。雖然海南、山東、內蒙古等省份陸續對葉臘石、海砂、硅砂、建筑用砂等開征資源稅,但絕大多數省份對未列名且附加值不高的非金屬礦原礦重視不足。這種制度安排有悖市場經濟公平公正原則,不僅產生國家放棄掉部分資源產品稅收權利的收入效應,而且,存在以不征稅資源產品替代征稅資源的替代效應,扭曲非稅和負稅資源相對價格比。兩者都扭曲企業決策,帶來非征稅資源掠奪式開采、過度使用和浪費。為促進資源產品橫向稅收公平,應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
針對資源稅擴圍問題,學界的一種觀點是全面擴圍,安仲文[26]主張涵蓋一切可能的自然和社會資源。就此而言,根據資源的自然屬性,被分類為礦產、生物、森林、土地、農業、海洋、水氣和氣象等資源大類,都應納入資源稅征收范圍。與之相對,相對擴圍論認為,應綜合考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分階段逐步擴大征收范圍,因此,賈康和王桂娟[27]與安體富和蔣震[15]認為,資源稅擴圍應限于自然資源領域,且應著重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的稀缺性資源。事實上,以上兩種觀點其實是融合的。因為前者可以視作未來發展趨勢,而后者因現實約束更具有現實可操作性。因此,我國應立足于充分考慮各類資源儲量、資源開發利用成熟度、資源保護需求及稅收征管手段完備程度等因素,漸進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而不必苛求一步到位對所有資源征稅。
其一,針對目前已征資源稅的某些資源類別,進一步完善制度,擴大征稅范圍。就礦產資源而言,應盡快細分能源、金屬、非金屬等礦產形式和鹽等二級稅目,并充實擴大三級稅目。比如,在“有色金屬礦原礦”稅目下增加汞、鎂、鈷和鉍,在“黑色金屬礦原礦”稅目中增加釩和鈦。其二,認真總結我國地方政府層面所進行的資源稅試點經驗,盡快針對水和森林資源開征資源稅。其三,針對草原和灘涂等主要分布在西部和東部沿海的資源,考慮到區域間資源稟賦特色迥異,應選擇部分地區進行資源稅試點,在總結成熟經驗的基礎上由中央政府統一開征草原和灘涂資源稅。值得注意的是,資源稅征收范圍擴大至水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會沖擊到現行相關法律。遵循稅收法定原則,為提升資源稅法法律效能,應通過制定新法律或修改現有法律方式做好法律銜接。比如,迫在眉睫的是,礦產資源補償費并入資源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第五條相沖突,征收水資源稅同樣需要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第四十八條有關規定。
(三)重視資源稅負轉嫁與歸宿問題
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有色金屬等資源構成工業企業基礎投入原料,所生產出的產品進而作為中間品成為產業鏈下游企業的投入品。從價征收資源稅,將提高資源行業企業稅負。面臨稅收沖擊,因存在稅負轉嫁機制,資源企業沿著商品流通方向將稅負轉嫁給下游企業或最終消費者的實際效果,不僅取決于資源性產品供求彈性,更取決于資源企業治理結構與產權結構。資源性產品需求彈性較小,資源性產品供給近似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提高資源企業稅負轉嫁能力,經產業鏈影響其他國民經濟部門。正是基于提高資源稅負→增加企業成本→影響企業發展空間→危及國家能源保障以及抬升居民最終消費價格和影響居民生活理由,資源企業往往游說政府給予降低資源稅費待遇。原油、天然氣從價計征改革后,油氣企業稅費負擔提高,但政府調高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征點,起到了對沖資源稅增加的效果。而且,針對油氣田企業的諸多稅收優惠政策,更是顯著降低了企業的實際資源稅負水平。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實施資源稅改革,無疑加大了改革難度和壓力。考量國際資源市場價格異動、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艱難等經濟、政治和社會因素,選擇恰當時機推進資源稅改革進程是必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不提高原油、天然氣等國有壟斷資源企業整體稅費負擔為前提,過于強調資源稅費推動經濟發展的工具屬性,事實上是以降低國家資源所有者權益為代價,人為降低資源完全真實價值,雖可減輕企業成本壓力,但并不必然增強企業創新激勵和競爭力,反而難以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方面有大作為。通過產品價格上漲將稅負轉嫁給下游企業以及進而轉嫁給最終消費者,經由消費者行為選擇再上溯到資源開發利用環節,將促進資源開采企業外部成本內部化,恰能實現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效應。其正當性取決于經濟合理性。進而言之,資源稅改革進程中,降低綜合稅負應綜合施策。這不僅需要考慮資源性產品和資源開采企業綜合稅費,而且,亦不能局限于資源稅單一稅種。一方面,應在規范清理各種不合時宜的收費基金的基礎上,協調綠色稅收關系,在資源開采環節征收資源稅,在資源生產消耗環節征收環境保護稅,針對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征收消費稅,為資源稅改革騰挪政策操作空間;另一方面,應配套完善資源行業企業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法人治理結構,增強資源行業企業市場競爭、客戶需求、市場價格信號乃至價格形成機制敏感性壓力。
參考文獻:
[1]郭焦鋒,白彥鋒資源稅改革軌跡與他國鏡鑒:引申一個框架[J]改革,2014,(12):52-61
[2]盧真,李升,芮東,等資源稅制改革:基于功能定位的思考[J]稅務研究,2016,(5):72-75
[3]李勝,李春根資源稅改革研析[J]稅務研究,2017,(8):38-42
[4]張德勇資源稅改革中的租、稅、費關系[J]稅務研究,2017,(4):58-62
[5]周波,范叢昕資源稅改革相關問題探討[J]稅務研究,2019,(7):23-27
[6]張富剛,李凱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新路徑——權利分置理論與實踐[J]中國土地,2018,(8):15-16
[7]施文潑, 賈康中國礦產資源稅費制度的整體配套改革:國際比較視野[J]改革, 2011,(1):5-20
[8]劉明慧, 趙敏婕資源稅改革應厘清三個問題[J]稅務研究, 2015,(5):32-38
[9]蒲方合基于資源節約的我國礦產資源稅之功能定位及其制度重構[J]經濟體制改革,2015,(3):38-42
[10]Hotelling,H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39(2):221-256
[11]高洪成, 徐曉亮資源稅改革中的價值補償問題研究[J]軟科學, 2012,(5):36-40
[12]張海星深化資源稅改革:重建立稅依據與平衡利益關系[J]稅務研究,2013,(8):39-44
[13]文正益厘清稅費制度關系, 推進資源稅費改革——關于資源稅與礦產資源補償費制度關系的思考[J]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11,(7):9-11
[14]范振林, 馬茁卉反思資源稅改革[J]國土資源, 2012,(6):30-32
[15]安體富,蔣震我國資源稅:現存問題與改革建議[J]涉外稅務,2008,(5):10-14
[16]丁丁,周冏,嚴巖,等我國資源稅改革面臨的問題及對策[J]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 2008,(5):55-57
[17]張海星,許芬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資源稅改革[J]稅務研究, 2010,(12):34-38
[18]吳迪基于CGE模型的資源稅改革對能源行業的影響研究——以煤炭行業為例[J]當代經濟管理,2014,(7):62-65
[19]劉植才,劉榮論我國資源稅的職能定位[J]稅務研究, 2012,(10):42-46
[20]馬蔡琛,李宛姝我國資源稅改革思辯[J]稅務研究,2014,(10):29-32
[21]張海瑩我國資源稅改革的意義、問題與方向[J]當代經濟管理,2013,(4):42-50
[22]樓繼偉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再思考[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
[23]劉尚希資源稅改革應定位在控制公共風險[J]中國發展觀察,2010,(7):2-8
[24]趙凡保障發展成就繁榮——新中國六十年地質礦產事業回顧[N]中國國土資源報, 2009-09-24
[25]李冬梅,馬靜我國資源稅改革的經濟效應分析[J]東南學術, 2014,(2):99-104
[26]安仲文可持續發展理念完善和改革我國現行資源稅[J]宏觀經濟研究,2008,(4):38-42+82
[27]賈康,王桂娟改進完善我國環境稅制的探討[J]稅務研究,2000,(9):43-48
(責任編輯:于振榮)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5009
[引用格式]周波,呂思锜資源稅改革仍有待解決的三個基本問題[J]財經問題研究,2020,(5):74-81
收稿日期:20200222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財政分權、政府間經濟職能分工與我國宏觀經濟穩定:生成機制、實證檢驗與改革方略選擇”(71873024)
作者簡介:周波(1977-),男,內蒙古赤峰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財稅理論與政策研究。Email:yourab@163com
呂思锜(1986-),女,遼寧丹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財政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