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海陽省菊浦遺址出土的“萬歲”瓦當及相關問題
【關鍵詞】越南菊浦遺址;“萬歲”瓦當;東漢至三國時期;交趾郡;縣治
【摘要】越南海陽省博物館共收藏了8件菊浦遺址出土的“萬歲”瓦當,根據當面文字的排列方式,可分為A、B兩型。對比可知,其與越南北寧省隴溪城址出土的部分“萬歲”瓦當形制相同,年代應相近,為東漢至三國時期。由于隴溪城址和我國南方地區出土“萬歲”瓦當且附近有大型墓葬群的6處遺址的性質均屬于王都、郡治或縣治,結合相關歷史文獻及菊浦遺址所在地的自然地理信息推測,菊浦遺址可能為交趾郡下轄某縣的治所。
菊浦遺址位于越南海陽省寧江縣菊浦村,地處富農江北岸,西北距首都河內約60公里。2019年12月,筆者應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歷史系邀請,赴海陽省博物館進行學術訪問期間,從該館副館長處得知,1999年在對疊壓在菊浦遺址上方的越南國家級歷史遺跡曲乘喻祠進行修繕時,在偏殿地基下發現大量筒瓦、板瓦、瓦當等建筑構件,海陽省博物館赴現場進行了調查,并采集了部分器物入藏博物館。筆者對這批器物進行了觀察,發現其中有多件“萬歲”瓦當,為考察越南北部地區漢晉時期城址提供了一些線索。本文擬在介紹菊浦遺址出土“萬歲”瓦當形制的基礎上,分析其年代,并結合其他“萬歲”瓦當遺址的出土情況和歷史文獻記載對菊浦遺址的性質進行討論。
一
目前海陽省博物館所藏菊浦遺址出土的“萬歲”瓦當共8件,根據當面文字的排列方式可分為A、B兩個類型。
A型2件。“萬歲”二字橫向排列。瓦當邊輪內有凸弦紋一周,當心為一乳丁,當面以穿過乳丁的單線為界分為左右兩區,分別書寫“萬歲”二字。編號BTHD7439-1,當背接粗繩紋筒瓦,當面直徑13.5厘米(圖一,1)。編號BTHD7439-2,當面殘長9.9厘米(圖一,2)。另外,據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歷史系副主任鄧鴻山副教授惠告,2019年12月,該系在菊浦遺址發掘出土了1件帶筒瓦的“萬歲”瓦當,與海陽省博物館所藏A型“萬歲”瓦當形制相同,因材料尚未正式發表,暫未列入統計。
B型6件。“萬歲”二字縱向排列。瓦當邊輪內有凸弦紋兩周,當心為一乳丁,乳丁外飾凸弦紋一周,左右兩側分別飾一組相背的卷葉紋,并以此為界將當面分為上下兩區,上部書“萬”字,下部為“歲”字。編號BTHD7440,較完整,當背接筒瓦,殘存瓦鉤,“歲”字的寫法省略了“止”字[1],當面直徑14.7厘米(圖一,3)。編號BTHD7441,邊輪略殘,“歲”字的寫法省略了“止”字,當面直徑14.5厘米(圖一,4)。編號BTHD7443,殘損嚴重,當面僅見部分“萬”字,當面殘長10厘米(圖一,5)。編號BTHD7442,殘損嚴重,當面僅見部分“萬”字,當面殘長12厘米(圖一,6)。
由于1999年調查菊浦遺址時出土現場已經被破壞,出土的“萬歲”瓦當均缺乏地層信息,我們只能通過其他出土“萬歲”瓦當且年代明確的遺址判斷其年代。
根據筆者搜集到的資料,越南境內出土“萬歲”瓦當、可與菊浦遺址進行比較的只有隴溪城址。該城址位于越南北寧省,地處紅河支流天德江南岸,西距河內約22公里。1968年至2019年,越南境內外多家單位陸續對該城址進行了多次考古調查與發掘[2]。城址內發現東漢至六朝和隋唐時期的排水渠、滲井、建筑基址、冶煉遺址、灰坑、柱礎等遺跡[3]。共出土4件“萬歲”瓦當。其中1986年出土1件,編號BTBN66,邊輪內有兩周凸弦紋,當面無界格,“萬歲”二字橫向排列(圖二,1)[4]。2015年出土1件,編號LL2015H1L15b5_049,邊輪內有兩周凸弦紋,當面無界格,“萬歲”二字橫向排列(圖二,2)[5]。2018年中山大學和越南河內國家大學聯合發掘隴溪城址(資料尚未正式發表)時,出土2件:編號LL2018H1L18a2,邊輪內有一周凸弦紋,當面有單線界格,“萬歲”二字橫向排列(圖二,3);編號LL2018H1L10,邊輪內有一周凸弦紋,當面無界格,“萬歲”二字縱向排列(圖二,4)。

經對比,菊浦遺址A型瓦當“萬歲”二字的字體、字形與隴溪城址編號LL2018H1L18a2瓦當相同,且瓦當邊輪內均有凸弦紋一周,當面皆由穿過乳丁的單線界格分為左右兩區,只是“萬歲”二字的書寫方向相反;B型瓦當“萬歲”二字的排列方式與隴溪城址編號LL2018H1L10瓦當相同。由此可知,菊浦遺址出土的“萬歲”瓦當應與隴溪城址2018年出土的“萬歲”瓦當年代相同。筆者曾參與隴溪城址2018年發掘資料的整理工作,發現這兩件“萬歲”瓦當與葉脈紋陶甕、菱形紋陶罐、素面瓷盆等器物殘片共出,而這些陶瓷器常見于越南東漢至三國時期的墓葬中[6],故“萬歲”瓦當年代應為東漢至三國時期,進而可知菊浦遺址出土的同類型瓦當也應屬于此年代范圍。
二
除文字瓦當外,菊浦遺址還出土有云紋瓦當、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陶器殘片等生活用器,表明該遺址曾存在較高規格的建筑。此外,越南考古學院于1976年在遺址北部發現一處墓葬群,保存有多座帶封土堆的墓葬,墓葬等級相對較高[7]。越南考古學院對其中一座被破壞的豎穴土坑木槨墓進行了發掘。由于被盜嚴重,該墓僅出土有三足釜、溫酒樽、盆、提筒、器蓋等陶器[6,7],但從殘留封土堆和木槨的規格來看,該墓的等級應較高。菊浦遺址既存在高規格的建筑,周邊又有高等級的墓葬群,其究竟屬于什么性質的遺址呢?
針對上述問題,越南境內外其他出土“萬歲”瓦當的遺址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參考。其中,越南境內可供分析的遺址僅有隴溪城址一處。城址面積約28萬平方米,由外城、內城兩部分構成。外城平面近方形,周長約2000米,墻基寬20~40米,殘高2~5.5米;內城形狀不規則,周長約500米,殘高1.5~2米。城址內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瓦當和陶瓷器[3]。其中,瓦當種類較多,包括“萬歲”“君宜高官”“位至三公”“吉宜子孫”等文字瓦當,以及人面紋瓦當、蓮花紋瓦當等[2]。該城址為東漢交趾郡治龍編縣的所在地[8]。城外東南發現清姜、三亞、月德等三組漢六朝時期墓葬群[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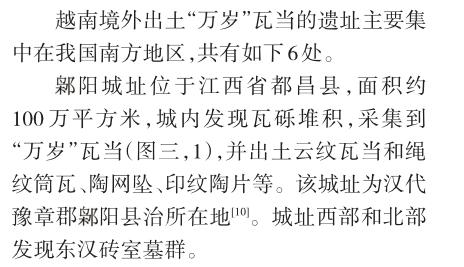
城村漢城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興田鎮,面積約48萬平方米,發現城墻、城壕、城門、道路、排水系統等遺存,城外南面和東北面發現漢墓5座。考古工作者對其中的高胡南平甲組建筑遺址、下寺崗一號建筑遺址、北崗建筑遺址、門前園遺址等大型建筑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陶器、鐵器、銅器等[11,12]。其中,高胡南平甲組建筑遺址出土40件“萬歲”瓦當(圖三,2),門前園遺址出土1件“萬歲”瓦當。該城址為閩越王無諸初封時的都城“冶城”,使用年代可分為西漢前期和西漢末至王莽時期兩段[13—15]。
屏山遺址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面積約35萬平方米。其中,屏山地鐵站發現了夯土臺基、水溝、水塘、水井、窯等西漢時期遺存,在水溝和灰坑中出土了目前福州地區數量最多的西漢時期“萬歲”瓦當(圖三,4),發掘者認為其應屬宮殿遺存[16]。在來自屏山菜市場工地的堆土中也采集到3件“萬歲”瓦當(圖三,3)[17]。發掘者推測福州屏山遺址可能為閩越國都城冶城[16],但多數研究者認為該遺址為西漢中后期閩越國越繇王的都城“東冶城”,閩越滅國之后為漢冶縣縣治[15]。
中山四路南越國遺址位于廣東省廣州市,主要由宮署遺址和宮苑遺址兩部分組成。其中,宮署遺址包括一號宮殿、二號宮殿、一號廊道和磚石走道等,宮苑遺址包括蕃池遺跡和曲流石渠遺跡,共出土南越國時期“萬歲”瓦當120余件(圖三,5)。除南越國時期遺存外,宮苑遺址還發現西漢中期至三國時期的文化層、房址、建筑柱洞、水井、灰坑、溝等遺跡,共出土“萬歲”瓦當45件(圖三,6)。相關發掘報告認為,南越國都城及王宮就位于今廣州市中心,且在漢武帝平南越之后仍有人活動并建有大型建筑[18—20]。此外,在廣州城北象山崗發現了第二代南越王趙眜的墓葬[21],近郊處有上千座官吏和平民墓葬,年代自南越國時期一直延續至東漢末期[22]。
二橋村漢代遺址位于廣東省徐聞縣五里鎮,目前清理了墓葬、灰坑、房址、水井、燒土面、柱洞等遺存,采集到1件“萬歲”瓦當(圖三,7)。該遺址年代為西漢早期至中期,是漢代徐聞縣的治所[23,24]。遺址北面東起紅坎村、西迄北部灣濱海一線、北到檳榔鍋村的狹長地帶分布有大量漢墓,先后清理兩漢墓葬近300座[25—27]。
貴城遺址位于廣西省貴港市,面積約26萬平方米,發現人工河道、水溝、灰坑、房基等漢代遺存,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筑構件以及壺、鈁、甕、罐、釜、缽等陶器,其中瓦當包括云紋瓦當、“萬歲”瓦當(圖三,8)等[28]。據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謝廣維副研究員惠告,貴城遺址2018、2019年發掘出土“萬歲”瓦當數量較多。該遺址為漢代郁林郡郡治布山縣的治所。遺址以東2公里的羅泊灣發現南越國時期大型木槨墓[29],遺址北部貴縣火車站[30]、貴縣高中[30]、馬鞍嶺[31]、孔屋嶺[32,33]、深釘嶺[34]、梁君垌[35]等地發現超過300座漢六朝時期的墓葬。
綜上可知,“萬歲”瓦當多與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和陶質生活器具共出,且出土該類瓦當的兩漢時期遺址附近存在大規模墓葬群,遺址性質為王城、郡治或縣治。由此筆者推測,“萬歲”瓦當應主要用于諸侯王都城的宮殿或郡治、縣治的官署等高等級建筑。對比來看,菊浦遺址與上述遺址有兩個共同之處。首先,除“萬歲”瓦當外,還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并發現陶器殘片。其次,遺址附近有墓葬群。因此,菊浦遺址也應存在高等級建筑遺存,其性質可能為王城、郡治或縣治。
三
考察《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等文獻可知,越南北部在東漢至三國時期屬于漢王朝統治范圍,且這一時期朝廷未在該地區分封諸侯王,因此菊浦遺址的性質不可能為王宮、宮苑,只可能是郡縣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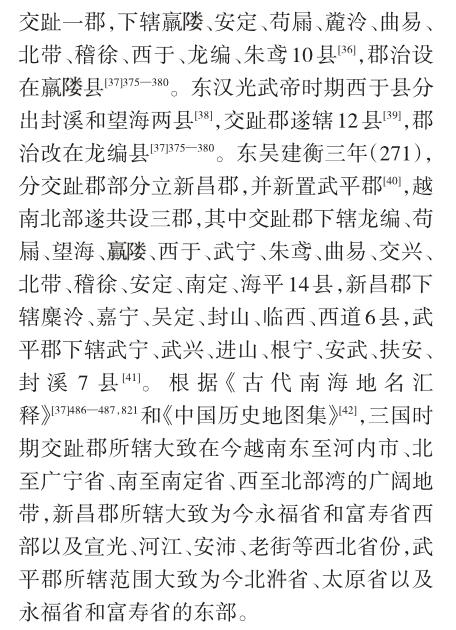
從地形上看,菊浦遺址所在的海陽省寧江縣地處紅河下游三角洲沖積平原地區,地勢平坦,遺址距現今海岸線的最短距離約為30公里。相關研究表明,紅河三角洲的海平面高度自全新世開始不斷下降,在距今1000年左右到達現在的高度,紅河河口的沖積平原不斷發育,海岸線以每年大于10米的速度后退[43],因此東漢至三國時期的寧江縣應更靠近海岸線,屬于濱海平原地區。由于東漢時期的新昌郡位于越南西北山地,武平郡位于紅河中游丘陵地帶,兩郡皆“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44],故可排除菊浦遺址所在地屬于新昌郡和武平郡的可能性,其應屬于交趾郡管轄范圍。
根據西村昌也先生的考證,今越南北寧省隴溪城址為東漢至三國時期交趾郡的郡治龍編縣所在地[8],而菊浦遺址在其東南約45公里處,又出土了相同類型的瓦當、筒瓦,故筆者推測,菊浦遺址可能為交趾郡所轄某縣的治所,可惜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尚不能確定菊浦遺址具體屬于哪個縣,期待今后進一步開展的考古工作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和線索。
本論文調研得到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鄭君雷教授、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歷史系鄧鴻山副教授的幫助,謹致謝忱!
[1]許仙瑛.漢代瓦當研究[D].臺北:臺灣大學,2005:273.
[2]韋偉燕,DANG HONG SON.越南北寧省隴溪漢唐時期城址[J].大眾考古,2018(4).
[3]Trình Cao T??ng,T?ng Trung Tín,Lê?ình Ph?ng.Luy Lau-Mùa Khai Qu?t 1986[J].Kh?o C?H?c,1989(4).
[4]Bùi Minh Chí.Thành Luy Lau[D].HàN?i:Lu?n V?n T?t Nghi?p Khóa 27 Tr??ng??i H?c T?ng H?p HàN?i,1986.
[5]??ng H?ng S?n,Nguy?n Xuan M?nh,??Th?Van Anh.K?t Qu?Khai Qu?t Thành Luy Lau N?m 2015[M]// Vi?n Hàn Lam Khoa H?c X?H?i Vi?t Nam Vi?n Kh?o C? H?c.Nh?ng Phát Hi?n M?i v?Kh?o C?H?c N?m 2016.HàN?i:NhàXu?t B?n Khoa H?c X?H?i,2017:237—239.
[6]韋偉燕.越南境內漢墓的考古學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7.
[7]Nguy?n?ình Chi?n. Ng?i M?Quách G??Cúc B?,Ninh Giang,H?i H?ng[Z]. HàN?i:Phòng T?Li?u Vi?n Hàn Lam Khoa H?c X?H?i Vi?t Nam Vi?n Kh?o C?H?c,1976.
[8]西村昌也.ベトナムの考古?古代學[M].東京:同成社,2011:155—176.
[9]黃暁芬.交趾郡治·ルィロウ遺跡Ⅱ:2014—15年度發掘調查からみた紅河デルタの古代都市像[M].福岡:フジデンシ出版,2017.
[10]都昌縣文物管理所.陽城址初步考察[J].考古,1983(10).
[11]福建博物院,福建閩越王城博物館.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發掘報告:1980—1996[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12]福建閩越王城博物館.武夷山市城村北崗三號建筑遺址發掘簡報[J].福建文博,2011(1).
[13]吳春明.再論福建崇安漢城遺址的年代等問題:兼答楊瓊同志[J].考古與文物,1995(2).
[14]張其海.閩越國“冶”都探究[M]//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閩越文化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107—127.
[15]吳春明,林果.閩越國都城考古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
[16]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福州市地鐵屏山遺址西漢遺存發掘簡報[J].福建文博,2015(3).
[17]福建省博物館,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博物館,福州市晉安區文管會.福建福州市新店古城發掘簡報[J].考古,2001(3).
[1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宮博物館籌建處.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2000年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2002(2).
[19]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宮博物館籌建處.廣州市南越國宮署遺址2003年發掘簡報[J].考古,2007(3).
[20]南越王宮博物館籌建處,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宮苑遺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21]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2]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3]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館,徐聞縣博物館.廣東徐聞縣五里鎮漢代遺址[J].文物,2000(9).
[24]申云艷.中國古代瓦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34—135,141.
[25]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徐聞東漢墓:兼論漢代徐聞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J].考古,1977(4).
[26]崔勇.徐聞二橋村漢代遺址與漢代徐聞港的關系[J].嶺南文史,2000(4).
[27]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徐聞縣凸嶺仔東漢墓發掘簡報[J].四川文物,2016(3).
[28]謝廣維,韋江.貴港市貴城漢至明清時期遺址[M]//中國考古學會.中國考古學年鑒2009.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366—367.
[29]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貴縣羅泊灣漢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30]廣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西貴縣漢墓的清理[J].考古學報,1957(1).
[31]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貴港市馬鞍嶺東漢墓[J].考古,2002(3).
[32]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貴港市文物管理所.廣西貴港市孔屋嶺東漢墓[J].考古,2005(11).
[33]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貴港市博物館.廣西貴港市孔屋嶺漢墓2009年發掘簡報[J].考古,2013(9).
[34]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貴港市文物管理所.廣西貴港深釘嶺漢墓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2006(1).
[35]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貴港市博物館.廣西貴港馬鞍嶺梁君垌漢至南朝墓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2014(1).
[36]班固.漢書: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1629.
[37]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8]范曄.后漢書:馬援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827—867.
[39]范曄.后漢書:郡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5:3531—3533.
[40]陳壽.三國志:孫皓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9:1168.
[41]房玄齡,等.晉書: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4:464—466.
[42]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三國、西晉時期[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57—58.
[43]SUSUMU TANABE,KAZUAKI HORI,YOSHIKI SAITO, et al. Song Hong(Red River)Delta Evolution Related to Millennium-Scale Holocene Sea-Level Changes[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2003(22):2345—2361.
[44]房玄齡,等.晉書:陶璜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1558—1561.
〔編輯:張曉虹;責任編輯:谷麗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