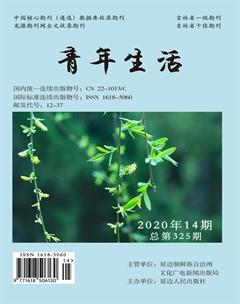我國破產(chǎn)重整計劃性質(zhì)問題研究
童廣賢
摘要:我國破產(chǎn)重整計劃的性質(zhì)是一種決議法律行為,本質(zhì)上仍屬于私法自治范疇。契約說、司法文書說、法律規(guī)則或規(guī)范說、相機(jī)浮動說等既有學(xué)說均存在難以消解之理論困境,無法自恰、周延地揭示出破產(chǎn)重整計劃之性質(zhì)。破產(chǎn)重整計劃不同于傳統(tǒng)的契約法律行為,而是依多數(shù)決原則形成的團(tuán)體(債權(quán)人會議或關(guān)系人會議)意思,決議過程中參與表決的債權(quán)人個別意思表示之獨(dú)立性為多數(shù)決原則所吸收,形成單一的集體意思——決議。決議法律行為說較既有學(xué)說更具解釋力,一定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對重整計劃性質(zhì)解釋范式的螺旋式發(fā)展。
關(guān)鍵詞:破產(chǎn)重整;重整計劃性質(zhì);決議法律行為;契約法律行為
一、破產(chǎn)重整計劃性質(zhì)之爭
200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yè)破產(chǎn)法》(以下簡稱《破產(chǎn)法》)正式引入重整制度,其是在克服破產(chǎn)清算與和解程序不足的基礎(chǔ)上應(yīng)運(yùn)而生的積極拯救程序。重整計劃的內(nèi)容涉及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經(jīng)營投資關(guān)系、稅收關(guān)系、勞動關(guān)系等多重法律關(guān)系。重整計劃的形成亦可謂諸種力量交融博弈之過程,有意思自治,有司法強(qiáng)制,甚至是行政干預(yù)。
上述特性使得重整計劃被蒙上了一層迷霧,難以透過現(xiàn)象辨其本質(zhì)。所謂性質(zhì),是指事物成為自己的原因,一經(jīng)變化就不能不喪失事物自身的同一性。現(xiàn)行《破產(chǎn)法》中無從找到界定重整計劃概念或性質(zhì)的描述。學(xué)界對于重整計劃性質(zhì)的認(rèn)識也莫衷一是。
一是契約說。
顧名思義,該說認(rèn)為重整計劃雖名為“計劃”,實(shí)乃“契約”。在破產(chǎn)法學(xué)教科書、學(xué)術(shù)專著或論文中,對重整計劃下定義的落腳詞上不乏見到“契約”“合同”或“協(xié)議”這樣的字眼。契約說是目前對重整計劃性質(zhì)進(jìn)行分析時使用較為普遍的一種范式,其基本分析模型如下:重整人擬定重整計劃,以重整計劃之內(nèi)容作為“要約”之意思表示,向關(guān)系人會議請求表決;經(jīng)關(guān)系人會議之可決而接受重整計劃之意思表示則為“承諾”。當(dāng)此二意思表示合致,該法律行為,即重整人與關(guān)系人會議所合致的重整計劃之“契約行為”即為成立。對契約說為進(jìn)一步細(xì)分,則復(fù)有團(tuán)體契約、強(qiáng)制契約、命令契約、組織性契約等諸說,此可視為契約說之延伸,本質(zhì)上仍未超出契約說之范疇。
二是司法文書說
其認(rèn)為重整計劃是按照《破產(chǎn)法》所要求的形式和內(nèi)容制作的必備性法律文件或者說是程序性法律文書,經(jīng)法院依職權(quán)裁定后具有強(qiáng)制執(zhí)行效力。該說要旨是:重整計劃,是指重整程序中形成的規(guī)范債務(wù)人營業(yè)振興措施和債權(quán)債務(wù)清理方案的法律文書。在法院裁定批準(zhǔn)后,是與生效的法院判決效力相同的司法文件。重整計劃是指由債務(wù)人或管理人擬定的,在重整過程中起指導(dǎo)性作用的,以維持債務(wù)人繼續(xù)營業(yè)、謀求債務(wù)人的再建、厘清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為目的和內(nèi)容,并經(jīng)關(guān)系人會議通過和法院批準(zhǔn)的程序性法律文件。
三是混合行為說。
此說認(rèn)為重整計劃是由重整之申請、關(guān)系人會議之決議、法院的認(rèn)可三要求結(jié)合而構(gòu)成的特殊行為的混合行為或稱結(jié)合行為。其理由是:法院對重整計劃之認(rèn)可,只能是全面地認(rèn)可或否定,無權(quán)加以修改,故只重視法院認(rèn)可的觀點(diǎn)是有疑問的。此外從重視重整計劃合法性、提升重整效率的角度出發(fā),又是不允許輕視法院之認(rèn)可的。就重整計劃的成立生效而言,重整之申請、法院的認(rèn)可與關(guān)系人會議之可決處于同等重要之地位。
二、破產(chǎn)重整計劃性質(zhì)之辨
(一)契約說之檢討
(1)契約效力通常僅及于締約主體,此即合同相對性原則之體現(xiàn)。而重整計劃的效力不僅及于參加表決投贊成票的主體,同樣及于投反對票甚至是未參與投票的當(dāng)事人。在這一點(diǎn)上,契約說也難以對重整計劃的性質(zhì)作出有效詮釋。
(2)依據(jù)要約承諾規(guī)則,受要約人拒絕要約的,要約失效。但在重整實(shí)踐中,重整計劃經(jīng)過第一次表決未通過時,并未因此“失效”,其中一些未通過表決的重整計劃甚至是原封不動地隨即進(jìn)行二次表決。
(二)司法文書說之檢討
司法文書說或程序性法律文書說強(qiáng)調(diào)重整計劃之“公法”屬性,凸顯公權(quán)力對私人自治之干預(yù)以及重整計劃的程序性功能,并認(rèn)為其具有同生效裁判同等的效力。該說的謬誤在于將重整計劃的生效要件或者說裁定行為的性質(zhì)視為重整計劃性質(zhì)本身,如此則有違重整計劃的本來面目,有以偏概全之嫌。
(三)混合行為說之辨析
混合行為說及相機(jī)浮動說都看到了重整計劃的多重屬性,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故在此一并進(jìn)行梳理辨別。混合行為說中將重整申請行為、關(guān)系人會議決議行為、司法裁定行為三者置于同等重要之位置,認(rèn)為重整計劃是上述三項(xiàng)行為的共同作用的產(chǎn)物。實(shí)質(zhì)上這只是動態(tài)地描述了重整計劃形成的過程,并未揭示出其性質(zhì),事實(shí)上重整計劃的性質(zhì)顯然亦非上述三種行為性質(zhì)的簡單疊加。混合行為說看似周延全面,似乎兼顧了契約說與法律文書說的某些特性,但實(shí)質(zhì)上是將同一事物和現(xiàn)象的重整計劃人為地進(jìn)行切分孤立定性,未能準(zhǔn)確抓住定性的對象或者說是客體,也不符合對事物定性的整合性和融貫性的基本原則。
三、決議法律行為與重整計劃性質(zhì)之契合
對重整計劃私法屬性的肯定,為其法律性質(zhì)的最終確定指出了方向。事實(shí)上,重整計劃本質(zhì)上仍是一種法律行為,但非契約或合同法律行為,實(shí)屬決議法律行為。
重整計劃實(shí)質(zhì)上是依多數(shù)決原則形成的團(tuán)體(債權(quán)人會議或關(guān)系人會議)意思,決議過程中參與表決的債權(quán)人個別意思表示之獨(dú)立性為多數(shù)決原則所吸收,形成單一的集體意思——決議。未參與表決或投否定票的意思表示原則上不影響決議的成立,除非該意思表示影響到?jīng)Q議足數(shù)。某種程度上債權(quán)人個人并非決議的當(dāng)事人,決議乃是債權(quán)人會議或關(guān)系人會議的行為,其效力范圍涵蓋整個破產(chǎn)財團(tuán)的利害關(guān)系人。根據(jù)《破產(chǎn)法》規(guī)定,重整計劃須經(jīng)法院裁定后方可生效。在決議達(dá)成時,決議法律行為就已經(jīng)成立。重整計劃中的裁定行為很大程度上只是對重整計劃的一種合法性審查或者說確認(rèn)行為,而非對意思自治的消滅或取代,相反實(shí)則是對意思自治的一種“保駕護(hù)航”。即使在重整計劃強(qiáng)制裁定情況下,結(jié)論依然如此。正如學(xué)者所言,法院對“意思自治”的“積極干預(yù)”是有限度的、中立的,只能在法律規(guī)定的裁量權(quán)范圍內(nèi)行使批準(zhǔn)權(quán)。
綜上,重整計劃實(shí)質(zhì)上是以法院的司法裁定為生效要件的決議法律行為。決議法律行為說在克服既有學(xué)說不足的基礎(chǔ)上,對重整計劃性質(zhì)進(jìn)行了較為精準(zhǔn)的法律定位,還原了重整計劃性質(zhì)的本來面貌,較既有學(xué)說更具解釋力與融貫性。一定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對于重整計劃性質(zhì)之解釋范式的螺旋式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