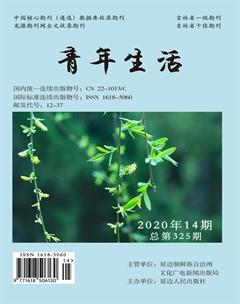淺析阿普特的亞洲現代性思考
盛國誠
摘要:2013年,紐約大學艾米莉·阿普特教授出版了其著作《反世界文學:基于不可譯理念》,出于一種“不可譯”思維下的世界文學體系,阿普特重點關照了亞洲的現代性問題。
關鍵詞:不可譯;亞洲現代性;世界文學
在《反世界文學:基于不可譯理念》中,阿普特敏銳地注意到近年來國際現代主義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促使人們需要新的文學史范式,以便將“亞洲現代性”提升為一個具備理論高度和文化特性的術語。的確,對于亞洲,人們越來越關注其現代性的多重帝國主義性,正如“東方學”所解讀的那樣。如今,在亞洲內部世界體系的背景下,西方現代主義繼續作為文學技巧和流派的一個重要標準,但重點是西方形式如何使亞洲現代性重新定義現代主義。阿普特援引臺灣中央研究院彭小妍的話,“當新感覺主義從歐洲傳到日本再傳到中國時,它引起的時間上、地域上的民族對現代主義的反思”,[1]即歷史遺留的所謂“跨文化現代性”,因此基于歐洲中心論的現代性周期參數標準的根深蒂固被彭小妍視為比較文學史中一種時間框架的障礙,阿普特對此持完全贊同的態度。她舉例論證在20世紀早期美國和歐洲所進行的實驗性寫作,包括意識流敘事,自由詩體和多語言詩論,在這些進程涌動的同時,舊有的現代主義時間框架概念迫使亞洲現代性被分割出局至邊緣地帶,歐洲的“格林威治標準時間”配合著資本化、同質化的世界主義范式奪去了亞洲的民族主義與西方化、世界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個人主義與激進集體主義、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文化現象進入世界文學討論圈子的民主權利,這是一種迥異于賽義德的“后殖民批評”的思考路徑卻又殊途同歸。
無奈之處在于,上述問題的思考在二戰后現代性解放中并未得到體現,學術視野上的零星發聲也未能起到集體觀念更迭的作用,尤其對于比較文學界而言,1958年教堂山會議時韋勒克等人針對法國學派使“比較文學成為文化功勞簿這樣一種奇怪現象”[2]的批評倒更類似于新舊兩個權力中心的相互掣肘,而不是備受期盼的邊際話語的解放。這正如查爾斯·泰勒所謂:“爭取解放的時候,我們以為自己在逃避舊的權力模式,事實上我們生活的新的權力模式之下”。[3]而1978年后中國的改革崛起令阿普特感嘆道:“這種異質的現代主義并不希望歐洲和美洲的現代主義方式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理所當然的發生,而是繼續在鄧小平1978年改革的覺醒中,作為一個通稱來表示對‘民主的渴望。”[4]阿普特道出了亞洲以非“他者”形象進行現代性討論圈子的訴求似乎更近于政治、經濟、軍事強大的饋贈,對于進入現代性圈子的“民主”需求倒反向成為了西方應對中國崛起的籌碼。
因此,筆者更傾向于在闡釋阿普特教授對亞洲現代性的關切基礎上引導一種亞洲內部的自我反思及對該問題腐朽本質的思考,因為亞洲現代性的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特定地域、時間、族群內文化政治問題的代名詞,而是根須扎進更為寬闊深遠的世界權力關系格局的一個刺出地表并對特定族群和國度造成傷害的毒刺,同時這也刺醒抱有實力主義幻想的民族,依靠實力提升來爭奪話語權,并憑此進入“經典”圈子的做法實則與為虎作倀別無二致,這意味著亞洲以及其他被現代性規則標識為邊緣的地區需要尋求一種新的解放,并且還要從被歐洲思維模式占據的權力中心所把持和定義的庸俗化多元、平等語境的溫水中勇敢上岸。
參考文獻
[1] Peng Hsiao-yen, 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Dandy, the Fl?neur, and the Translatot in 1930s Shanghai, Tokyo, Par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 [美]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危機》,見干永昌等編選:《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129.
[3] Charles Taylor, “Foucault on Freedom and Power”. Michel Foucaul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VEd. Barry Smart. London: Routledge, 1995, 334.
[4] Emily Apter,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Verso Press, 2013,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