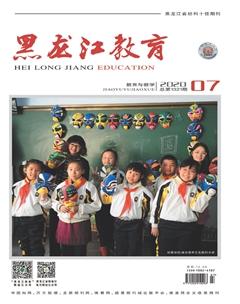“對不起,老師錯了”
趙明明
美麗的景色總是讓人流連忘返,美好的回憶總是讓人駐足凝望,可是,生活中那些意外的疏忽與遺憾,也會讓我們久久難以忘懷。記得那是我剛上班不久發生的一件事。
初秋的一天上午,擔任小學四年級班主任的我在語文課上檢查學生課文的背誦情況。有幾位學生沒能完成,于是我很憤怒地說:“中午再背不下來,就別吃飯了!”
中午放學前,有幾個沒能完成背誦的學生也都會背了,檢查完我便轉身走了。其實,說不讓學生吃午飯也只是嚇唬他們而已,只想著讓他們盡快背下來,哪能真不讓學生吃飯呢。而且,我的中途離開也給剩下幾個沒有背會的學生,一個“偷偷”吃飯的機會。
下午第一節課,是我的數學課。講完幾道題后讓學生自己練習,當我巡視,當走到小偉身旁時,無意中聽到他和同桌在說什么。
我生氣地問:“你倆在說什么?為什么不認真做題!”
小偉同桌怯怯地站起來,吞吞吐吐地說:“老師……是我擺弄小偉的包子。他讓我把包子放到書桌堂里邊,他說看到包子他饞。”
聽到這兒,我如夢中驚醒,我怎么忘了叮囑他吃飯呢?小偉的一句“看到包子我饞”像針扎一樣刺痛了我的心。那哪是饞,他是餓了。我恨我自己,是我把小偉給餓著了,再看看他那委屈而又害怕的樣子,我慚愧極了。我帶著十分復雜的情緒上完了課。
下課后,我讓小偉拿著包子到我辦公室里面,讓他坐在椅子上,并給他倒了一杯熱水。只見他怯懦地低著頭,一小口一小口地啃著包子。我俯下身子側著頭小聲問:“中午沒吃飯,餓了吧?”他不敢大聲說話,只是微微地點一下頭,還“嗯”了一聲。我遞了個杯子給他,說:“喝點兒熱水吧,包子已經涼了。”他沒有出聲,只是搖了搖頭,繼續吃著包子。“中午老師不在班級,你為什么不偷著吃點兒呢?”內疚心理驅使我帶著似乎有責怪又心疼的語氣問。“我不會背。”多么聽話、誠實的學生啊!可是我的心卻是酸酸的。“餓了為什么不跟老師說呢?”“我不敢”。這三個字又一次刺痛了我的內心。
我用帶著歉意,用手輕輕地摸了摸他的頭說:“以后再有什么話就跟老師說,即使不會背,老師也不會不讓你吃飯的。今天是老師錯了,老師忘了叮囑你吃飯,對不起,讓你挨餓了。”他抬起頭羞澀地看著我說:“老師,沒事兒,我現在不餓了!”雖然我發自內心地道了歉,小偉也吃飽了,但是這種內疚心理還是久久揮之不去。
那一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我每天只顧著完成教學任務,提高學習成績,卻忽視了與學生的情感溝通,我和學生的關系太疏遠了,甚至讓學生每天都在懼怕中學習,這是我教育方法的缺失。其實不僅僅是小偉不敢和我說,班級很多學生都知道小偉沒有吃飯,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告訴我。什么是教育?到底應該怎樣教育?老師和學生之間到底應該保持什么樣的關系呢?教室應該是什么樣的氛圍?是恐懼嗎?
后來,我是在雷夫老師的《第56號教室》里找到了答案。第56號教室之所以特別,是因為雷夫老師從不用強硬手段或者命令式的語氣來管理班級,他用信任取代恐懼,做學生可以信賴的依靠,講求紀律公平,并且成為學生的榜樣。那一刻我醍醐灌頂,這種理念、這種思想正是我極其需要的,這正是我的不足,是我應該學習和努力的方向啊!
隨著時間的流逝、閱歷的增加、經驗的豐富,我明白了這絕不是一件單純的偶然事情,也不僅僅是因為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問題,同時也是我的教師語言藝術問題。教師的語言不能被情緒所控制,每一句話都應該是理性的、可操作性的,而不是感性的、隨意的。一句“如果不會背的話,中午就別吃飯了”,本意是督促學生背課文,卻被學生深深地記在心中,并確確實實地遵守起來。在學生心里,老師的話具有權威性,對于學生來說就像“圣旨”一樣,尤其是小學生,一定會言聽計從。所以,從那以后,我在學生面前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盡量不再出現任何遺憾。
自從有了那一次疏忽,在以后的教學中,我都會很好的處理,呵護我和學生的關系,時時刻刻控制自己的情緒,對自己的語言負責,切記自己的教師身份,不讓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謹言慎行,也是教師的一項基本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