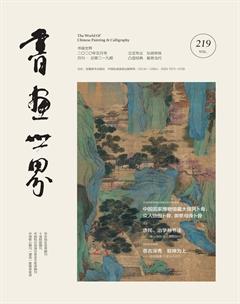蒼古深秀 取神為上
杜志東



“層次分明點畫工,啟人心事見毫鋒。他年畫苑三千輩,個個毋忘念此翁。”這是1926年64歲的齊白石為35歲的胡佩衡所題的詩句,詩中齊白石對這位忘年交的山水畫成就贊賞有加。作為民國初期北京畫壇重要的傳統派畫家,胡佩衡的山水畫淵源彌正,氣息古雅,加之其社會交游廣泛,藝術活動豐富,在京城畫壇享有較高聲譽,與當時的另外兩位山水畫家蕭俊賢、蕭謙中并稱“二蕭一胡”。盡管現在這位似乎被遺忘的畫家遠沒有同時期其他畫家那么為人熟知和受人矚目,但在當年,他也是京城畫壇響當當的人物。
胡佩衡(1892—1962),號冷庵,原名錫銓,又名衡,蒙古族,原籍河北省涿縣,祖上遷居北京。雖與“二蕭”畫風接近,同為畫壇備受關注的人物,但胡佩衡與他們在出身背景及生舌經歷上有諸多不同。民初京城畫壇風氣多由南方籍畫家引領,“二蕭”中的蕭俊賢來自湖南衡陽,蕭謙中是安徽人,他倆很早就受到過傳統文人畫的熏陶,到京城后不久即成名。但胡佩衡是地道的北方人,生于北京,家庭早先從商。他個人先后畢業于私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新華專門鐵路學校。關于其學畫經過,在《我怎樣畫山水畫》一書中胡佩衡曾提到,他自幼喜繪事,從臨摹入手,后來受到西陵山水畫家李靜齋的教導,開始臨摹明清古畫,并以古法進行寫生和創作。經過自身不懈修習和鉆研,胡佩衡在20多歲時開始獨立創作,步入畫壇。名家輩出的北京畫壇為胡佩衡的繪畫成長提供了廣闊空間,他不僅得到了姜穎生、林琴南兩位先生的指授,也通過結識金城、陳師曾、齊白石和陳半丁等畫家,在交游往來中使個人的藝術風格逐步走向成熟。
中國美術館藏有胡佩衡1926年創作的《深山小徑》一幅。這是一件表現山林隱士的作品,為胡佩衡早期的創作。胡佩衡喜作山林隱士圖,山林是淡泊者的逍遙天地,士人在隱居山林中找尋著自己與社會的契合點,追尋著自己的人生目標,對寄身山林的隱士生活和行旅人物的表現也成為歷代文人畫的經典主題和士人們的精神寄托。該作品為高遠與平遠相結合的全景式構圖,分近景、中景、遠景三個層次。近景以左側山林巨石為主體,樹石繁密,雜樹古松枝干交錯穿插,右下角溪水岸邊一文士執杖而行,幾條隱現在山林之中的野徑蜿蜒而上,呈“S”形逶迤遠去,直到山間深處,將觀者的視線引入掩映在深山竹林中的茅屋。遠處高山重巒疊嶂,山勢雄偉秀麗,更加襯托了隱士閑居山野的暢快。作品以潤筆勾廓,枯筆干皴,以淺絳設色,赭石濕染又復施以淡花青色,樹濃山淡,頗具林木蔥郁、水復山重之致。畫面右上有題跋:“翠疊深山小徑斜,層層磴道倚云霞。峰巒缺處茅檐露,知有閑居隱士家。墨井道人宗法山樵,沉雄渾厚,自成一家。后世學之者難得其神,蓋漁山畫寓縹緲于覺著之中,沉著易學縹緲不易學也。丙寅秋日,胡佩衡并識。”款題后有鈐印“胡佩衡印”。
題跋前半段的自作詩是對整幅作品的描述,頗具畫面感。胡佩衡常會在畫作中題寫自作詩,詩、書、畫相結合是傳統文人畫的典型特征。這也反映了胡佩衡長于古詩文的傳統文化學養。
在題跋的后半段里,胡佩衡別提及了兩位歷史上著名的文人畫家,其中“墨井道人”“漁山”指的是“清初六家”之一的吳歷(1632—1718),吳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山樵”則說的是“元四家”之一的王蒙(1308—1385),字叔明,號黃鶴山樵,浙江人。吳歷早年跟隨山水名家王鑒和王時敏學畫,畫風工整嚴謹,講求法度,中年之后開始宗法黃公望、王蒙、吳鎮等人,筆墨厚樸渾重,氣韻深淳,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深山小徑》是胡佩衡擬吳歷筆意的一幅創作。從蒼勁沉著的筆法和嚴密的章法布局中,觀者可以感受到吳歷、王翚、王蒙各家對他的直接影響。胡佩衡對吳歷畫作頗有研究,曾多次擬寫,并常在跋語中對其筆法風格進行分析品評,如胡佩衡在1923年創作的《秋山行旅》題跋中所言,“墨井道人秋山無盡圖,筆墨全法山樵,氣韻蒼莽,有洪谷子云中山頂,四面峻厚之勢”。從他自1923年出版的《胡佩衡畫存》中來看,黃公望、王蒙、沈周、吳鎮、石豁、王翚、吳歷等南宗畫家是他臨寫的主要方向。此外,胡佩衡也學北宗,他甚至認為他摹習的南宗繪畫“多有北宗意焉”。在這件意境深遠的作品中胡佩衡糅入了北宗之力,北派山水的雄峻厚重亦有顯露,所以說胡氏早期的畫法風格基本上是在摹習南北宗各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民國是自清以來的又一個繪畫摹古高峰期。清末民初,各地繪畫精英聚集京城,特別是陳師曾、金城、王夢白、齊白石、姚茫父、湯定之等一批傳統派畫家的出現使得北京畫壇的摹古之勢呈現出勃勃生機。從胡佩衡的藝術經歷及存世畫跡來看,臨仿古畫是他20世紀20年代藝術創作的一個主要特點。1920年,胡佩衡加入了金城、陳師曾、周肇祥等人創辦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為第一批中國畫學研究會的研究員。此后,胡佩衡于1927年升為助教,后又升任評議。畫學研究會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為宗旨,是北京最重要的畫學會社。胡佩衡從臨習明清諸家真跡入門山水畫創作,繼而上溯宋元山水,此后又得金城等傳統派畫家的影響,對摹古自然有著個人獨到的見解。在其所著《冷庵畫旨》中他指出:“今之人不知途徑,或專摹一家,不敢變化,或爭尚狂怪,自眩新奇,甚至習畫數十年尚不能有自己之面貌。”正如吳歷宗法山樵卻能沉雄渾厚而自成一家一樣,摹古貴在跳出藩籬而獨出機杼,如《深山小徑》所示,作品中雖有吳歷、王蒙的影子,但從披麻層層皴寫的積墨效果和不似吳、王繪畫那么邃密的構圖來看,這件作品無疑還有新的突破。
題跋中“后世學之者難得其神”以及“寓縹緲于沉著之中,沉著易學縹緲不易學也”代表了胡佩衡法古所獲的心得體會。他認為:“仿古以取神為上固已,然所謂取神者,言畫法已通,臨摹時不必過拘形似,當于神理處用功,倘于畫法尚為諳習,即高談神理,無如手與心違,其結果終難美滿。”“沉著”與“縹緲”可與上述引文中的“畫法”與“神理”對應,在跋語中胡佩衡表面上是在探討摹寫吳歷繪畫的筆法問題,實則代表了他對山水畫創作的精髓——“氣韻”以及不同創作境界的體悟與認識。胡佩衡曾將山水畫的“氣韻”分為兩類,“一望而知大凡有氣勢而又有風韻(趣味)的叫作‘雅氣。有氣勢而沒有風韻的叫作‘俗氣”。雅氣之下又分雄厚、蒼潤、靈爽、淡寂和清秀幾種。綜觀這幅作品,畫面山石結體雖然復雜,但讀來并無刻板遲帶之氣,整幅畫面在層巒疊嶂中反倒富于韻律,于蒼古渾厚中給人以清幽深秀、氣韻周流的通暢之感。“取神以為上”,或許這正是胡佩衡在題跋中所謂“寓縹緲于沉著之中”的旨趣。畫家對傳統繪畫駕輕就熟的研究與剖析功力可見一斑。
20世紀上半葉,隨著美術革命思潮的興起,圍繞中國畫的革命與改良以及對西畫的模仿與創造成為中國畫發展過程中激烈爭論的主題。1918年胡佩衡加入蔡元培創辦的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被聘為中國畫導師。其間,在新文化運動等新思潮的影響下,為加深“對西畫的認識與學習”,胡佩衡隨比利時畫家蓋大士學習了素描、油畫以及水彩等西畫。博學多能的胡佩衡不僅在繪畫上杰出,同時也是出色的美術編輯,他先后兼任《繪學雜志》《造型美術》《湖社月刊》等雜志主編,這些美術活動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對當時美術發展有了清晰的判斷。
從摹古門徑入手的胡佩衡一方面強調摹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在中國畫革新思潮風起云涌的社會時代背景下清醒地認識到晚清“四王”的僵化流弊對傳統文人畫的影響。他積極倡導“用古法寫生,由寫生而創作”以及“師造化”傳統的回歸,他指出:“中國山水畫在唐朝和宋朝為最盛。當時善畫山水的名人,都具有創造的能力,去繪畫天然的好風景,開了后世畫山水的門徑。可惜后世學畫的人,只在他們的皮毛上用功,不知道在根本上去講求,將‘師古人不如師造化的解說全都拋開。所以美術的前途也就一天退步一天了……目下教育部立了一處美術研究會,為的是參酌西洋的新美術,改良中國的舊美術,并不是把外洋的尊為神圣,把自己的說得一錢不值。所以我們愿意改良中國山水,當注重寫生。”胡佩衡并沒有主張完全割裂中國畫的傳統價值,而是力圖要在回溯傳統的過程中發掘新的可能性。他的這種理性的、漸進式的態度對于中國畫的革新無疑更具建設意義。
然而,盡管“古法寫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即已提出,但胡佩衡在當時及隨后的創作中卻鮮有踐行,這也是《深山小徑》等作品沒有在根本上與古^拉開距離的原因。直至新中國成立,特別是1956年桂林、韶山寫生之后他才開始大膽擺脫傳統的視覺觀念。中國美術館藏《香山紅葉》(見扉頁)就是他這一時期的作品,設色妍麗,濃墨、焦墨相輔相成,頗有視覺沖擊力,在構圖上尤具真實性和寫生效果,將之與《深山小徑》對比后會發現,二者除了蜿蜒小徑、深山屋舍等一致的圖像元素外,面貌早已大有不同。摹古不再是繪畫的目的,而成為創作的手段,胡佩衡從舊社會與新時代的角度解釋了其夙愿得圓的緣由:“回憶在三十八年前,我就想要推陳出新,想把中國山水畫推進到寫實的境地,而不要死守成規,總拘束在古人的圈子里。但是,舊社會里仿古的風氣很重,使我的主張得不到響應與支持……只有在今天,到了人民的時代,在黨的領導下……為了發揚民族風格的繪畫,要用傳統技法去寫生,由寫生而創作。”
百年來中國山水畫的變革之路充滿了各種曲折和探索,回顧這段歷史,除卻繪畫和美術出版與教育方面的成就,胡佩衡在其中的價值更多地體現在:作為一名以摹古出身的傳統派畫家在中西新舊思潮交鋒激蕩的文化語境中對中國畫的傳統價值從最深層面所做的思考和努力。“他年畫苑三千輩,個個毋忘念此翁”,這位立于歷史潮頭的藝術先賢應該被我們銘記。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