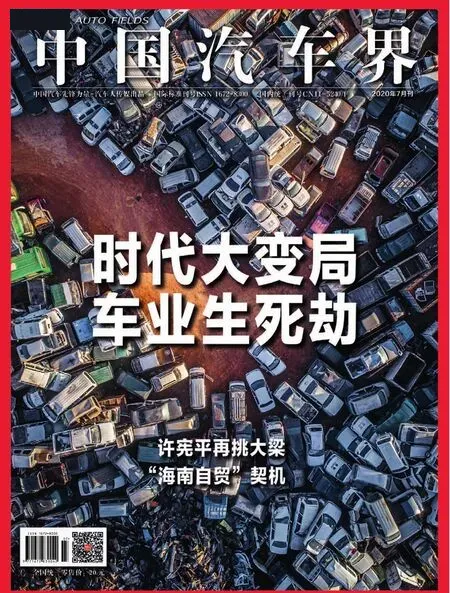“代工”受益者不是“新勢力”
文/
在兩會“部長通道”上,工信部部長苗圩表示:將進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有序放開新能源汽車代工生產。
這一表態雖然只有寥寥數言,卻表達了中國政府對于新能源行業健康發展的關注,透露了對于“代工生產”模式的支持,強調了對于汽車生產供給側改革的重視與謹慎,更在倡導汽車行業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錮。
“有序放開新能源汽車代工生產”似是直指未形成產能的造車“新勢力”,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受益的群體一定是擁有體系力、品牌力與研發力的企業。
前期成本讓代工出位
談到“代工生產”,很多人會下意識地想到“造車新勢力”。
在中國造車,發改委的準入標準、工信部的39號部令是兩道無法迂回的“門檻”。前者是《新建純電動乘用車企業管理規定》(2015年7月1日起實施),后者是《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準入管理規定》(2017年7月1日起實施)。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這兩條規定是針對新能源車項目,咱們去造燃油車好啦。且不說新入行者的技術儲備、品牌號召是否能與傳統車企比肩,《汽車產業投資管理規定》(發改委)的第十一條就明確禁止“新建獨立燃油汽車企業”、禁止“現有汽車企業跨乘用車、商用車類別建設燃油汽車生產能力”。
即使有汽車企業申請擴大燃油汽車生產能力,也應在“上兩個年度”完全符合“汽車產能利用率均高于同產品類別行業平均水平”、“新能源汽車產量占比均高于行業平均水平”、“研發費用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均高于3%”等五大條件。
在關了門上了鎖又扔了鑰匙之后,新進入者就只有新能源車一條路,回到了準入標準與39號部令前的“起點”——造新能源車仍然要滿足前述兩項規定,才能取得造車的資質。拜騰出資收購一汽華利,便是為那稀缺的資質。
僅僅拿到資質,拜騰就付了8.5億元,此外還要買地建廠、買設備調試、奠基研發體系、理順供應鏈……這一條龍走下來,至少還要花上50億元人民幣。為什么這么肯定?因為剛剛有人打了樣。

大眾-江淮合資項目,年產10萬輛純電動乘用車:利用江淮汽車現有建設用地,而不需要現金支付;僅新建沖壓車間、焊裝車間、涂裝車間、總裝車間、電池包車間、研發中心、公用動力及辦公設施等,項目總投資大約50.6億元,其中建設資金大約29.5億元,流動資金21.09億元。
汽車看起來簡單,但“汽車不是你說造,說造就能造”。所以,苗部長一說“代工”的事,大家自然而然就想到:這是在原本很難以斡旋的規定之下,為“新勢力”打開了一道門縫。
如果代工者既被占了產能,又沒有叮當響的實惠,更沒有值得吹噓炫耀的背景……這樣的合作,便很難走得長遠。
產能放空者短期受益
客觀評價,“代工生產”是在為資金缺乏、產能放空者提供了一個“臨時解渴”的方案。
首先,“有序放開新能源車代工生產”,確實是應勢而生。
一方面,瑞幸咖啡造假,使得投行對于“中概股”的信心全失。華爾街不會為造假企業買單,“中概股”和中國大量待上市公司所面臨的資本市場環境可想而知。或有新技術、新概念、新模式產生,但信任已逝、信心不再。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襲擾,社會總消費需求在短期內受到抑制,旅游、餐飲、交通等面對消費者的行業受到最大沖擊。水平分工結構的產業鏈(全球),在疫情之下表現出物流成本高、運輸時間長的缺陷;在自然災害、社會動蕩、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機之下,產業鏈斷裂的風險也在提高。
今天的中國汽車產業,產能放空已不再是坊間流傳的隱患,而是血淋淋的現實。
除了《汽車產業投資管理規定》中的嚴格禁止,國務院2016年發布的《關于發布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2016年本)的通知》中就已提出:“嚴格控制新增傳統燃油汽車產能,原則上不再核準新建傳統燃油汽車生產企業。”
至2018年,我國汽車產業的計劃年產能已超過6000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產能規劃(2020年)將超過2000萬輛,是《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銷量目標的10倍。而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2019年全國汽車產銷量分別為2572.1萬輛和2576.9萬輛,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124.2萬輛和120.6萬輛。
至長安福特哈爾濱工廠建成、福克斯下線(2017年),長安福特的5家工廠規劃完美實現,總產能攀至160萬輛。而其在2019年的銷量僅為18.39萬輛,僅為全部產能的11.5%。同在放空產能的還有神龍汽車,四家工廠總產能近百萬輛,2019年的產能利用率為11.16%。
以拜騰為例,雖然能夠以1元的代價收購一汽華利,但未必能以30億元的投入,將三通一平的空地變成滿足現代制造需要的產線,更不要談工人的經驗、供應鏈的運轉、品控的保障、環保的達標……而如果有體系完備的代工方合作,一切問題都可以找到相對簡單、高效的解決方案。
由此可見,“代工生產”的有序放開,確實可以推動“產能放空者”與“造車新勢力”互補互助。
產能共享或是趨勢
從敞開發展看,此次苗部長談“代工生產”,更是在為“電動化、智能化大潮重構產業鏈”而提前預熱。
當龍飛船載著兩位宇航員成功升空后,阿波羅4號、航天飛機與龍飛船的操控平臺對比照也同步亮相。阿波羅4號的控制面板上有密集如迷宮的按鍵;航天飛機減少了按鍵的數量,增加了9塊單色顯示屏;龍飛船則以3塊17英寸觸屏來取代按鍵、撥動開關和控制桿等2000余個斷路開關,就像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智能化程度更高,操作更簡單。
需要強調的是,以觸控屏替代按鍵、旋鈕等實體操控開關,不僅是炫耀科技感、為使用者帶來更好的體驗,更是在幫助削減控制系統的自重、提高系統安裝的效率。而特斯拉轎車上裝配的巨大觸屏,同樣是為了減輕自重與提升效率。
從特斯拉第一輛車下線,馬斯克就從未停止對優化工藝、提高生產效率的努力,甚至有聲音批評他因追求自動化而導致整條生產線的生產效率下降,也在所不惜。來自特斯拉的數據顯示,最新車型Model Y的電氣化程度躍升,車內傳感器線束的長度已經從初代的3000米削減到100米!
微觀經濟學中的規模經濟,單位產出的成本隨著規模的增加而降低,企業因此而獲得成本優勢。而在現代制造業中,成本優化的方向已不再限于規模增加、供應鏈縮短,而是在追求模塊化、集成化的方向上不斷加速。
未來的汽車不僅擁有平臺化的特質,其制造也會如接插樂高一般簡單:“三電”成為汽車的基礎,軟件成為汽車的靈魂,其余只是附庸。車輛的設計研發環節,軟件工程師成為主角,硬件工程師“退至”二線。而前者對于代碼的完善并不十分執著,只要出廠時沒有Bug,隨后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在線升級、即時補丁而完成。
未來的汽車制造更會在以軟件為靈魂的基礎上實現重構:用戶打開App、登錄帳號,跟隨指示輸入需要,不要說車身的顏色與形式,座椅的材質和摩擦系數、水杯架希望放利樂鮮奶還是蘇打水,都能實現預設。
性能可以預設,而運費需要自付,何不就近選擇工廠生產,何必讓順豐、京東再薅一次羊毛?代工生產成為主流——武漢制造天然擁有成本的優勢,預先在新疆布局的大眾可以“獨占藍海”,長三角、珠三角的制造基地反而需要“競價出位”……

代工并非靈丹妙藥
在代工生產中,有OEM與ODM之分。OEM指原始設備制造商,通常是掌握核心技術、控制銷售渠道的強勢品牌,將生產任務委托給“他人”,只在隨后低價買進、貼牌銷售。接受蘋果委托生產的富士康就是OEM。
ODM指原始設計制造商,因產品的新設計、新功能被其它品牌看中,而拿到生產訂單(可能會對設計稍作修改)。委托方貼牌銷售,以節約設計資源、縮短研發周期。小米的很多產品就具有此類屬性。
同是代工生產,OEM沒有設計、品牌和渠道,依靠委托方派駐工藝、品控專員,幫助提升生產與工藝能力,產品品質因此得到保障。富士康為蘋果代工,不僅有代工費落袋,有“蘋果制造商”作背書,還有與蘋果合作開發模具等工作提高經驗值……但這些都建立在蘋果公司品牌優勢、技術領先的前提之下。
ODM則擁有研發設計與工藝保障能力,但產品品質完全依靠自身保障,貼牌商只能開啟“拼人品”式。在家電行業,類似的貼牌生產很多,特別是小家電領域。因為有規模效益的傳導,雖然利潤微薄,但產業鏈上的各方都能從中獲益。
汽車行業卻是另一番天地,既強調規模效益帶來的成本優勢,更重視委托方對于工藝品質的把控、對生產效率的提升,甚至包括市場響應的節奏。
長安福特代工生產沃爾沃S80 L、S40轎車的時日,沃爾沃“四大經銷商”對產品供應的評價只余“痛苦”。有沃爾沃經銷商回憶說,沃爾沃在長安工廠并沒有“話語權”,導致生產對市場的響應過于遲緩:假如市場上“黑色S80 L熱銷”,今天向大區反饋“,待工廠開始調整產能、增加黑色車身的供貨,時間已經是數月之后——市場恐怕早已另有“新歡”。
離岸外包同樣存在各種不確定性。在東南亞負責CKD工廠的安德說,其復雜性在于語言和文化差異,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了解。比如組織員工團隊建設,上午爬山、中午燒烤,中國人會覺得是件開心的事,周末也不是問題。當地人卻會問我,是否要算加班。此外,旅行距離、工作日/時區不匹配,以及建立信任和長期關系,都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從產能看,處于“產能饑渴”中的“新勢力”似是代工生產的必然受益者。但從代工生產的本質看,惟有在品牌、技術、體系等方面擁有比較優勢的企業,才能放心地將生產“外包”,而將有限的資源聚焦于擅長的、高價值的產業鏈。
從實力看,“新勢力”初入市場,品牌尚未形成認知、產品也未形成口碑,很難拋出一個具有足夠吸引力的供貨合同。對于代工者,既被占了產能,又沒有叮當響的實惠,更沒有值得吹噓炫耀的背景……這樣的合作,便很難走得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