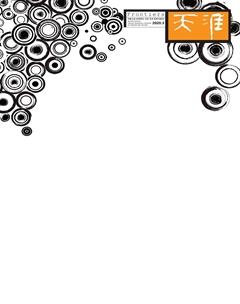童年
出發(fā)和回歸
可能沒人懷疑,作家的童年時(shí)代對(duì)其一生的成長與書寫都是極重要的。就人生來說,童年生活是一個(gè)開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個(gè)特殊階段。雖然童年經(jīng)歷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記憶的一個(gè)“老巢”,各種各樣的生活都從那里開始,都堆積在那里。那時(shí)的記憶尤其新鮮,所以也最難忘記。
拉美作家馬爾克斯曾有一句妙語:“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得住的日子。”一個(gè)人走了很長的人生之路,回頭一看,會(huì)發(fā)現(xiàn)一路上的很多事情和一些細(xì)節(jié)都忘掉了。每當(dāng)回想往事,我們常常會(huì)有一種遺憾:這長長的一段時(shí)間里,能夠清晰記起來的并沒有太多。也許就是這些記得住的片段疊加在一起,才構(gòu)成了我們平常所說的“日子”。從這個(gè)意義上講,童年時(shí)光是最難忘懷的,所以它在人生經(jīng)歷中占據(jù)的比重也就更大,以至于形成了一個(gè)巨大的生活團(tuán)塊。童年經(jīng)歷會(huì)深深地影響一個(gè)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的現(xiàn)在和未來。
從童年開始,人的心中擁有了若干神秘之物。這個(gè)時(shí)段最早的一部分,可能處于能夠記憶和不能夠記憶的交叉點(diǎn)上,所以回憶起小時(shí)候,人們會(huì)說:“當(dāng)年我還不記事。”或說:“那時(shí)我好像記得。”童年時(shí)期的很多元素會(huì)揉入潛意識(shí),它們極其內(nèi)在,若有若無,甚至是虛幻的和不確定的:不知是誕生之初就攜帶了這些意識(shí),還是由后天的觀察、歸納與綜合而成。童年的見識(shí)有不可思議的強(qiáng)韌性和規(guī)定性,它會(huì)制約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