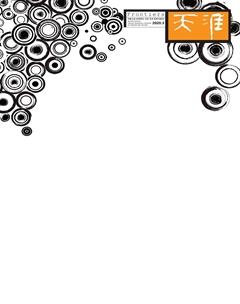昆德拉的“主編式全知視角”
2020-08-07 05:37:54
天涯
2020年3期
關鍵詞:小說
昆德拉的“主編式全知視角”
2020年2月21日的《洛杉磯書評》網站上,刊載了吉娜·弗蘭基洛評論米蘭·昆德拉的文章,題為《在其宏偉中有奇異的相等:論米蘭·昆德拉與手法》。
弗蘭基洛提請我們特別注意昆德拉小說中經常出現、但卻迄今未受到足夠重視的敘事視角:“主編式全知視角”,在他看來,縱觀昆德拉的整個小說創作,從《好笑的愛》到《不朽》,對于此一“主編式全知視角”之變異形態、演進形式以及矛盾沖突的反復實驗,都是昆德拉的自覺追求。
在《好笑的愛》里所收錄的《搭車游戲》中,昆德拉即開始展示這種視角,它既是全知的,又似乎是不動聲色、冷靜客觀的。在這篇小說里,人物的哲學觀點似乎得到了空前深入和精確的發展,但我們還是可以說,這些人物依然還只是一些“類型”,是作者思想的喉舌。從一開始,昆德拉最為關心的,就是即使在面對“自由”時,我們是如何置自身與他人于陷阱之中的;盡管充滿了哲學意味,但昆德拉的小說讀起來卻更像是心理象棋大師賽,而非理論或哲學。而到了《笑忘書》,這一視角又開始從貌似冷靜客觀,向某種更為明確的主觀性敘事轉變,比如,在《天使們》這一篇中,他將自己的第一人稱自傳性經驗,與他筆下虛構人物的經驗混雜在一起,而這些人物有的住在可悲的“真實”世界之中,有的則困在夢魘般的超現實世界之中。就此而言,雖然仍然是在用第三人稱,但作為作者的昆德拉卻把自己也置入文本之中,他就像一個精明而又固執的導游,不僅為我們分析他筆下的角色,而且還告知我們該如何閱讀他的小說。……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