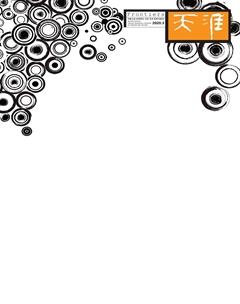唯一者或所有物
2020-08-07 05:37:54蔣浩
天涯
2020年3期
蔣浩
一
再忙的日子,也是有閑的時刻。閑生無聊,而無聊勝于閑。像滑出手心失重的肥皂,無聊的肥皂比肥皂泡泡還輕盈。當有閑與無聊在一個合適的有限的空間反復滲透、疊加一起時,比如孩子在周末晚上去國貿上英語課了,空蕩蕩的房間突然被這種奇怪的氣息全充滿了。需要釋放,需要把某種情緒點燃,像一支煙需要先掐滅后再重新點燃。但今天的問題是,煙還在,甚至那半截灰黑的煙灰也還彎曲地掛在潔白的半截煙卷上。可打火機不在這里。偏偏離婚就像把打火機丟進海里。還真是,他清楚地記得簽了字的那天黃昏,車開到海邊,靠在敞開的車門上抽煙。煙其實只抽到一半,就像現在這樣的一半時,就被他狠狠地丟進了海里。海風把煙灰吹進了沙灘。
燃著的半截煙像只老鼠,在波浪上起起伏伏、躲躲閃閃,最后也消失了。當然,他不可能確切聽見燃燒的煙頭觸水的瞬間發出的嗤嗤聲,那過于細微,是可以忽略的。就算這過于喧囂的海浪的喧嘩,對于他來說,也不及剛才走出民政局的大門時,她從另外的車窗伸出手掌揮動出的無聲。只是輕輕地揮動,凝固的空氣攪起了旋渦,像她身下旋轉著遠去的車輪。他記得那光潔手臂上延伸出來的青蔥指頭,像手指夾著的煙頭,還燙手呢。好吧,抽完這半根,扔掉那另外的半根,算是告別了。
他慢騰騰地往回開車。開得很慢。他是第一次在這個安放了椅子的新筑防波堤邊看海。離家不遠,五分鐘車程,可前四十年他就沒來過,更沒想過會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