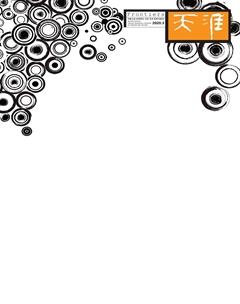虛擬之鄉
2020-08-07 05:37:54陳峻峰
天涯
2020年3期
陳峻峰
往南方去追尋中原人南遷歷史蹤跡,在現時代,連我都猜疑,就是一個文化借口的渺茫企圖。在走過諸多“遷徙地”“聚居地”“集散地”,走訪那些學者、專家、知情者和普通人,我不僅沒有獲得我所需要的歷史描述,把自己也弄丟失了。回來后,不敢去碰那一大堆凌亂的資料筆錄,我判斷不出它們彼此的用心和真假。
其間日子,真是好過得很,大半年光陰流轉而逝。去翻桌邊臺歷,生出遐想,以為這日子,如果能像臺歷頁面,翻過去了還可以翻回來,要有多好。這樣一來,我便知道我正在經歷寫作上的“艱難時刻”,當下時髦之詞日“瓶頸”。
抓不住、看不到、想不出,就像那些光影、畫面、概念、定義、聲音、言辭,就像我們置身其中而又悄然流逝的時間。鬼使神差的,從書架上抽出了馬爾克斯那本深褐色封面的中文譯本《百年孤獨》,遙遠地去和這位偉大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一起,進入他的那個與世隔絕的馬孔多小鎮。霍·阿·布恩蒂亞和他堅強勤勞的妻子烏蘇娜,以及他的長子、次子、小女兒、情婦苔列娜、俏姑娘雷麥黛絲,以及家族最后出生時長有尾巴的嬰兒,都與我似曾相識。吉普賽人帶來另一世界傳說和神奇,帶來磁鐵、望遠鏡、假牙、玻璃球頭痛藥、飛毯和馬孔多人從未見過的鉆石一樣閃光的冰塊,再次令我驚訝和著迷。著迷的還有布恩蒂亞,他不僅為此很快失去了他作為馬孔多一位年輕族長為社會造福的精神——譬如過去,他經常告訴大家如何播種、教養孩子、飼養家畜,跟大伙兒一起勞動——還在磁鐵、科學試驗和天文探索中迷失了自己,并幻想采到金子和發現世界奇跡……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