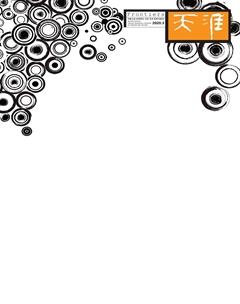追憶黃保真先生
2020-08-07 05:37:54成復旺
天涯
2020年3期
黃保真先生去世后,他那面帶笑意,不緊不慢、侃侃而談的樣子,反而經常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總覺得應該為他寫點什么,但一時又想不好究竟應該寫點什么,也不知道何處可載。前不久,海南師范大學的周泉根先生給我發來了他已經編好的兩卷本、六十多萬字的《黃保真先生文集》的書稿。說實話,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周泉根先生是黃保真先生晚年的學友和同事,我們曾在黃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上見過一面。沒想到,他對黃保真先生懷有如此厚重而實在的師友深情。他約我為此書作序,我不可能不接受。一是為周泉根先生的這種師友深情所感動:二是亦即此了結我自己的一樁心事。
黃保真先生自1979年調入人大,就同蔡鐘祥先生和我在一起,一起上“中國文學理論史”這門課,一起寫《中國文學理論史》這部書。雖然不能說朝夕相處,卻的確是三天兩頭見面。接觸中,覺得他和藹可親、樂于交談、令人輕松愉悅,所以我們很快就從工作上的同事變成了人生中的朋友。其間有件事,我永遠都不會忘。那時,在工資制度上中國還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層層倒掛”的年代,知識分子待遇很低。為了多少能夠貼補家用,黃先生夫婦辦了一家小書店。事成之后他立即來告訴我,并對我說:“以后你想買什么書,就跟我言語一聲,我按照出版社批發給書店的折扣價給你帶來。”我說:“你們辦個書店不容易,今后的經營會很辛苦,有多少收益尚不可知:就按書上的定價帶給我,就已經省了我不少事了,不要再打折扣。……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