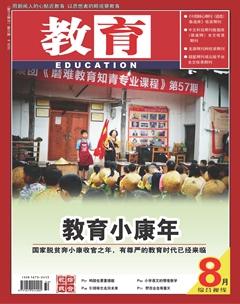教育小康年



編前語
實現全民小康教育,2020年是國家全面脫貧奔小康的收官之年;毫無疑問,2020年的中國教育也要全面達到“小康”。千百年來困擾中華民族經濟生活與教育事業的絕對貧困即將畫上句號。教育事業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這個目標的基本條件。科技現代化與教育現代化相互助力,相互影響,促進教育公平。有專家提出,我國教育是憂心忡忡地邁進了“教育小康年”;“教育小康”關鍵要看全國大中小學生是不是真的享受到小康的實惠:從一人一策的到位幫扶,到工學結合的職業教育,再到推動信息技術普及,助力貧困生上網課,乃至慈善助學機構尊重貧困生尊嚴;小康時代的教育,有尊嚴的完整教育時代已經來臨。
2020:夢想就在眼前
2019年,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最后沖刺階段,全國教育人迎難而上,將人才、科研、文化優勢轉化為脫貧“利器”,書寫了新的篇章。
聚焦義務教育薄弱環節,消除城鎮學校大班額,加強鄉鎮寄宿制學校和鄉村小規模學校建設,推進農村學校教育信息化建設,成為三大重點工作任務,努力補齊貧困地區義務教育發展短板。抓好控輟保學,是拔掉窮根、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一系列文件密集出臺,為打好控輟保學攻堅戰保駕護航。
“培養一名技工,致富一個家庭。”過去一年,職業教育發揮了在攻克深度貧困地區堡壘中的突擊作用,為貧困學子改變命運、實現出彩人生創造了條件。
高校正成為脫貧攻堅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自2012年44所直屬高校納入國家定點扶貧工作體系以來,各直屬高校把自身特色優勢與定點扶貧縣發展短板相結合,逐步形成了具有“高校品牌”的特色扶貧路徑。2020年,75所直屬高校投入扶貧,20個縣實現脫貧摘帽。直屬高校定點扶貧,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中小學生減負一直備受關注,2018年底,教育部等9部門聯合印發“減負30條”,此后,寧夏、重慶等20余省市區份陸續出臺地方實施方案。伴隨地方方案的實施,部分家長對減負提出質疑。這場爭論背后,實際是對家長、政府等各方在減負觀念和目標上的糾偏:減負并非讓學生沒有負擔,而是要讓負擔保持在適度范圍之內。這一年,隨著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規范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校外培訓機構治理的觸角從線下延伸到了線上。全國教育,正在闊步邁向公平而有質量的目標。
“小康”解讀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就把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建設目標。1960年,四個現代化被全國人大正式列為國家戰略目標。四個現代化包括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這是小康概念首次在國家層面被提出來。鄧小平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的水平”,中國“從國民生產總值來說,就是年人均達到800美元”。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2000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80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步戰略目標。
1987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客人時,明確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構思:“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達到500美元,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步,在下世紀再用30到50年的時間,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按2013年發布的《全國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測算,到1999年我國總體已走完溫飽階段94.6%的路程,200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900美元,到2013年底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將突破10萬億人民幣大關,我國進入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教育水平進一步提高——到1999年底,全國已有一半以上的縣市區達到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全國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9.1%,小學和初中升學率分別為94.4%和50%。1999年底成人識字率達87.6%,超過85%的小康標準值。到2000年底,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占比為4.7%。
在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中,對于教育有明確的數字要求。國家有關部門參照國際上常用的衡量現代化的指標體系,考慮我國國情,從十個方面形成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標準,其中明確提出教育標準:國內人均大學入學率20%。在2013年前后,我國大學入學率為11%。隨著科教興國戰略力度的加大,社會力量參與辦學,我國大學入學率到2015年達到15%。當時預計到2020年有可能超過20%,達到25%。
2019年6月,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3833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8.1%。2019年,由于高職將擴招100萬,毛入學率將首次突破50%。這個數據意味著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實現了普及化,這是高等教育從大眾化階段到普及化階段的跨越。
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民眾最實在的感受是高考的錄取率。我國高考錄取率從1998年的33.86%增長到2018年的81.13%,是20年前的2.4倍。雖然2019年的高考報名人數超過千萬,但是以2018年的招生790.99萬為基數,加上高職擴招的100萬,2019年招生數900萬,也就是說高考的錄取率幾近90%。這意味著,所有高中應屆畢業生,只要想上大學,就有90%的概率可以上,這足以說明高等教育確實進入了普及化階段。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總人口中,大學生比例低于10%,嚴格的說是9.5%(不含大專4%)。這是因為很多中老年人沒有上過大學。但這不影響實現適齡青年入學率超過20%這個目標。統計局第六次普查的2017年全國21歲同齡人受教育程度的數據顯示:約28.2%的人接受大學教育(不含大專的話是13%);全國21歲同齡人中,71.8%的人沒考上大學,50.8%的人沒考上高中,6.7%的人沒考上初中。
28.2%,這個數字已經超過小康標準的20%,以及早年預計的上限25%。而且2017年21歲的大學生大多數應該是在2015年前后入學的,在那之后,大學錄取率繼續上升。近幾年大學錄取數字:2015年,錄取700萬人,錄取率75%;2016年 錄取人數為760萬人,錄取率達到76.3%;2017年 錄取人數為810萬人,錄取率達到80.37%;2018年 錄取人數為830萬人,錄取率達到81.13%;2019年全國高校錄取820萬人,錄取率為79.53%,略低于2018年。不管怎樣,這個錄取率已達到小康社會對教育的要求。
2010年8月,《小康》雜志社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中國教育發展現狀滿意度調查。綜合調查結果以及國家有關部門的監測數據,得出2009年至2010年度中國教育小康指數為67.6分,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五項指標中,對教育公平程度的感受最差,其指數為53.6分。
2018年8月,《小康》雜志會再次同有關專家及機構,對“中國教育小康指數”進行調查。經過對調查結果及國家有關部門的監測數據進行加權處理,得出“2018中國教育小康指數”為82.0分,比上年提高6.0分,一舉突破了80分大關。
輟學娃的“人生規劃”
2019年12月,山東省慶云縣慶云四中八年級(15)班一名女生在班會上這樣介紹自己:“我叫程思瑜,競選的職位是班長。我想通過這個機會為更多同學服務,讓咱們班變得越來越好。”在40多位同學注目下,程思瑜額頭冒汗,這個曾因家庭貧困打算輟學的14歲女孩,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班委候選人。
幼年喪父,母親改嫁,2013年爺爺突發心臟病去世后,程思瑜和奶奶被列入建檔立卡貧困戶。雖然學雜費有了基本保障,但她的思想卻發生了變化。“不想學習,只想幫著奶奶干活、養家糊口。”小小年紀的她打定主意,讀完六年級就不再讀書。
慶云縣推出的“三幫一”教育扶貧模式,徹底改變了程思瑜的“人生規劃”,“三幫一”即“干部+老師+愛心企業家”精準結對貧孤學生。2017年,幫扶活動啟動后,程思瑜被認定為幫扶對象。慶云縣產業發展中心主任陳智勇、慶云四中教師邊德星、四川鏈家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副總裁黨杰共同與程思瑜“結成對子”。因此,她被接到慶云四中讀書,生活和學習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三人組合”分別負責孩子們的家庭事務處理、精神上關懷;教師主要是學有所教,對孩子們學習上所有的問題,積極幫扶,積極解決;愛心企業家主要是幫助孩子們學習物質所需,解決孩子們的家庭經濟困難。
邊德星先是鼓勵程思瑜參加班級活動,幫班里做事,逐漸打開孩子封閉的內心。然后是補習功課,“開始時是每天補習知識薄弱點,成績提高后,隔兩三天再補習一次。”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程思瑜的煩心事少了;幫扶老師守在身邊,她放在學習上的心思多了。“這么多人幫助我,我只能以優異的成績回報他們。”程思瑜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一天,程思瑜因為發燒耽誤了一節課。邊德星在課余時間去給她補補課。程思瑜說:“3年來,在邊老師、黨叔叔和陳伯伯的幫助下,我的學習和生活都得到了改變:在學習上,老師會為我解除疑難雜癥,為我一一解答問題;生活上,黨叔叔和陳伯伯常常來家里和我聊天,為我排解心頭上的疙瘩。我很感謝他們。”
邊德星這樣評價程思瑜:“成績一直在進步,她的性格也開朗了很多,自信心增強了。”得益于慶云縣實施的“三幫一”創新助學體系,程思瑜的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
送教到人 ,送網上門
2019年9月,重慶市大足區龍崗中學開展教育扶貧,為特殊貧困家庭學生“建卡送教”,不讓他們在學習上掉隊。
“你可以先記一下這些英語單詞,自己先預習課文……”幾天前,龍崗中學區級骨干教師周平上了一堂別開生面的英語課,課堂就在一名建卡貧困戶學生家中。當天,龍崗中學校長雷明平帶領該校教師等一行6人,來到大足區棠香街道東關社區,為生病在家休養的該校建卡貧困戶學生楊紅蘭送教上門。來到楊紅蘭家,老師先向家長詳細了解楊紅蘭的身體狀況,鼓勵家長堅強面對病情,鼓勵學生積極地戰勝疾病。他們給楊紅蘭送來新課本、作業本等學習用品和牛奶等營養品,對她的學習進行輔導。在對楊紅蘭的學習能力、生活自理能力進行評估后,結合實際情況,老師們當即與她商定了切實可行的學習計劃,鼓勵她在養病之中,能夠有計劃地進行學習,跟上年級的學習進度。
目睹這一切,楊紅蘭的奶奶激動地說:“國家政策太好了,不但給我家貧困補助,還讓娃兒在家里就能上學……感謝老師們對我孫女的關心!”
目前,龍崗中學的適齡學生全部就學,一個不少;貧困生全部受到資助,一個不落。雷明平表示,學校將繼續堅持送教上門活動,使教育精準扶貧落到實處,讓所有孩子都看到明媚的藍天。2020年開年,在家上學成為貧困學生家庭面臨的新難題。重慶市大足區教委精準施策,加強關愛,確保全區的757名貧困生都能線上學習,網上在線學習“一個都不少”。
周香緣、周飛瑤同學是一對姐妹花,她們在大足區龍崗一小分別就讀六年級和四年級,由于家庭經濟困難,學校上報區教委后,將姐妹倆納入了捐助名單,決定贈送她們一臺電視機和一臺平板電腦。在學校的幫助下,周香緣、周飛瑤還享受了免費網絡套餐,以及大足有線教育頻道免費觀看的服務。
2020年 3月,深圳市福田區為河源市和平縣送來一批平板電腦,幫助和平縣42個省定貧困村886名學子順利接受網絡教學,不讓一個學生“掉隊”。在上陵村扶貧助理黃素瓊的指導下,9歲的慧娟很快就學會了在新的平板電腦上上網課。慧娟在上三年級,還有一個妹妹也在上小學,因為缺少設備,之前都是輪流用手機看直播課程,學習效果不理想。拿到平板電腦后,慧娟說:“現在,我也可上網課了。”
工學交替,家庭“新希望”
2019年暑期,陜西省漢中市洋縣職教中心組織140名學生到蘇州紫翔電子、寧波方太廚具進行了為期86天的“工學交替”跟崗實習。來自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的53名學生人均收入超過1.9萬元。
白瓊是洋州街道辦事處東聯村建檔立卡貧困學生,妹妹在上小學,爺爺患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父親務工是他們家庭唯一收入來源,白瓊在“工學交替”期間掙了2萬多元。每月薪資一到賬,白瓊第一時間將錢寄給自己父親,父親白濤說:“女兒一共寄了1.6萬元,還給爺爺買了治病的藥。”
據學校統計,參加跟崗實習的53名貧困學生,將85%以上的薪資寄給了父母。他們的“第一桶金”成了全家脫貧奔小康的“新希望”。“以前上課能學多少是多少,實習時才發現很多知識不會,走了許多彎路。現在上課更認真了,課后還經常找老師解答問題。”學生韓琦說道。“通過真實崗位上的真學實做,學生們感受到知識和技能的缺乏,學習勁頭更足了,學習方向更明確了。”該中心招生就業處副主任何曉波說道。
翻開洋縣職教中心2019年暑期跟崗實習學生手冊,上面詳細記錄著駐廠教師每天的工作內容和突發事件處理情況。實習期間,學校派出4名教師作為學生的“實習導師”,除了負責學生的安全、考勤、生活外,還經常對學生進行職業道德和工匠精神教育,幫助學生明確職業規劃,為人生未來奠定基礎。外出實習還讓學生懂得了立志。鄭土杰是金水鎮許家村建檔立卡貧困學生,暑期實習他第一次走出大山,實習間隙,鄭土杰和他的同學還到杭州灣跨海大橋開展研學活動,“中國橋”彰顯的大國自信,讓他倍感自豪,也讓他在心中立下遠大志向。和鄭土杰一樣,參加“工學交替”的53名貧困學生都是第一次走出家鄉,這次實習帶給他們更多的是眼界的開闊和思維的轉變。
據了解,該中心已經連續4年組織學生到南方企業開展“工學交替”,先后有430名學生通過該活動實現了“強技、立志”的人生目標。
“有尊嚴”的助學
“教育小康”保障的不僅是物質上的生存條件,還有人格上的平等和尊嚴。
2019年8月,安徽省馬鞍山市慈善總會舉行2019年度“慈善助學”助學款發放儀式,234名寒門學子獲得慈善助學金,圓了大學夢。與往年不同的是,為體現人本理念,讓貧困學生有尊嚴地受助,馬鞍山市慈善總會不再邀請受助學生到發放儀式現場“亮相”,改由各縣區慈善機構代領代發助學金。同時,積極引導社會資源愛心助學,進一步加大對貧困學子的助學力度。
2019年的馬鞍山市慈善助學金發放現場,簡樸而又熱烈。整個現場,不見一個受助學生。所有受助學生的助學金,均由各縣區、開發園區民政及慈善機構相關工作人員代領代發。 “今年,我們沒有邀請受助學生代表到發放儀式現場,也不安排新聞媒體采訪報道受助學生,為的就是有效保護貧困生的隱私,呵護貧困生的尊嚴,讓貧困生能‘體面地接受幫助。”馬鞍山市慈善總會相關負責人表示。近年來,國家及省相關部門出臺規定,要求各地在各類助學活動中,注意尊重和保護學生隱私。
馬鞍山市慈善總會一方面做好受助學生的資格審核,確保慈善助學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注重加強對貧困生資助過程的隱私保護,讓慈善助學活動更合規、更有愛、更有溫度。馬鞍山市2019年的“慈善助學”活動,共發放助學款67.7萬元。所資助的234名貧困學生,來自各縣區低保貧困家庭及貧困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這一年,是馬鞍山市慈善助學圓夢行動的第19個年頭,通過慈善助學這一平臺,受到資助的困難學子已超過1萬人次,累計發放助學款近2000萬元。 馬鞍山經貿學校教師侯樹婷介紹說:“2019年,我們學校有171人享受國家助學金政策,967人享受市級助學金,國家免學費學生1622人,另外還有3名同學享受了國家獎學金。”
馬鞍山市學生資助管理中心發布的信息顯示,2019年,國家加大了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力度,擴大了資助范圍。高職院校國家助學金發放資助面提高到了在校生的30%,平均標準為每生每年3300元;中職學校增加了國家獎學金政策,獎勵中等職業學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別優秀的學生,每生每年6000元;義務教育階段對建檔立卡學生、殘疾學生、農村低保家庭學生和農村特困救助供養學生等,家庭經濟困難的非寄宿生補助生活費,標準為寄宿生的50%。這一標準基本覆蓋了所有的貧困生。
同步課堂提升鄉村教學
首都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謝維和教授介紹說,在美國勞動部、商業部、教育部等聯合作出的《21世紀工作技能報告》中,就失業人口列出了兩項指標:一是失業比例,一是丟掉一份工作與重新找到一份工作的時間差。報告分析表明,學歷越高,失業比例越低,而且在丟掉一份工作和重新獲得一份工作之間的間隔時間越短。“學歷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在高收入階層中的比例就越高。”謝維和說,“學歷、文化程度與收入是正相關的,而且高、低收入者之間的差異是很顯著的。”“縮小農村教育跟城市教育的差距,縮小地區間教育的差距。這將是我們是否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惠及十幾億人的、更加公平的小康社會,要求我們的教育更加公平。”
城市居民,尤其是干部和知識分子家庭,從幼兒園開始就為子女創設優越環境,小學、中學更要千方百計上“重點”,為此,花重金、找關系、搬家轉戶口,都在所不惜,一切都為了子女將來上更好的大學。許多大城市高考錄取率已達百分之七八十,上大學不難,但家長仍很緊張,因為上好大學仍然很難。
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更多,留守兒童已成社會問題。鄉村學生如何得到優質的基礎教育,如何在成長道路上與城市學生拉近距離甚至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個困擾中國教育多年的問題,在進入21世紀后,隨著科技進步,我國逐步實現科技現代化,終于等來了解決的辦法。
2019年,“全面推進‘互聯網+義務教育,推進1000所中小學校結對幫扶,讓城鄉孩子共享優質教育資源”成為浙江省政府民生實事項目之一。同年9月,浙江省麗水市蓮都小學高溪校區新安裝的“浙善城鄉同步課堂”里,參加啟動儀式的嘉賓們和麗水各區縣鄉村小學的教師代表一起體驗“互聯網+義務教育”:位于城區的劉英小學五年級數學老師吳偉波在上《分數的再認識》,巨溪校區的孩子們和蓮小高溪校區里的“大朋友”們也跟著一起聽課,問候、提問、對話,都是實時互動,就和在同一間教室里上課一樣。就在這一天, “浙善城鄉同步課堂”公益項目正式啟動。“浙善城鄉同步課堂”公益項目計劃于一年內分兩批先后向麗水市、衢州市各捐贈50套同步課堂硬件設備,安裝到相關縣市區結對的鄉村學校(主要是小規模學校),在100所小規模小學校打造100個城鄉常態化同步教學試點,為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公平教育人人受益”貢獻慈善公益的力量。
蓮小高溪校區教師邱真表示,在城區的小學上公開課,被同步課堂里的交互智能平板一體機、錄播設備所吸引,希望自己的學校也能有一套。9月25日,她第一次看到同步課堂真正使城鄉互動起來。主課堂教師吳偉波時不時會詢問巨溪校區的學生有沒有聽懂。他也會面對著屏幕,直接向巨溪的孩子們提問:“你們覺得什么是二分之一?”巨溪校區的數學老師葉婉瑩鼓勵孩子們舉手,有兩個小女生先后回答了這個問題,得到了兩位老師的贊許。動手環節,劉英小學的孩子們上臺平分黑板上的12個“圓”,巨溪校區的孩子就在葉婉瑩老師的指導下,分小組完成同樣的任務。
邱真一直在蓮都區最偏遠的鄉村小學教學,去那個村子要經過三百道彎。因為上學要翻過山頭,于是哥哥姐姐都帶著弟弟妹妹住校,幾乎沒有機會看一看山外的世界。邱真說,不光孩子們受益,教師也受益;前段時間,蓮都區人民路小學請了國學專家和老師們開展教研活動,與他們結對的泄川校區的老師,就可以通過同步課堂一起上課。
城鄉同步教育體驗結束后,又切換到城鄉同步教研,不同學校的老師通過同步課堂,和麗水市小學數學學科帶頭人沈武君一起“磨課”。在城鄉同步課堂中,鄉村老師要和城市里的老師一起備課、教研,對鄉村老師而言,每堂課也是學習和提升的機會。
教育專家顧明遠表示: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難點和重點是在農村。“我在這里說的農村,也包括以農業為基礎的縣城。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教育的現代化。”顧明遠認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九年義務教育已經普及,適齡兒童不會因為經濟條件差而輟學。但是,中國的農村教育仍然面臨很多困難。
顧明遠認為,農村更需要科技手段促進教育變革。
小康教育:邁向公平與質量
素質教育:一種新的價值觀
在國家發布的教育類文件的英文翻譯中,素質教育被譯為well rounded education,即全面教育。素質教育和“文革”期間樣板戲主人公的“高大全”人物(well rounded person)的譯法一致,這兩個概念都是中國人提出來,然后被吸收到英文中的。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教育界提出學校教育要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之后,“素質教育”一詞多次被寫進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中,并成為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識,體現為全體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實踐。素質教育概念的提出,就說明黨和國家是站在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的高度來認識教育的真正意義。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應該是十六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中的應有之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必須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
素質教育不是權宜之計,更不只是一種新提法而已。素質教育不僅有具體的、操作性的意義和內容,更重要的是素質教育具有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本質意義——在于它的思想性和時代性,在于它提出了新的教育價值觀。教育的價值觀影響著教育活動的各個方面和全過程,它必然會提升為某種理論、方針、政策,指導整個國民教育的實施;也會潛移默化地作用于教育工作者,影響他們的知、情、意、行,并以各種形式影響青少年學生。
素質教育強調學生有個性的發展。學生有個性的發展是學生自身發展的落腳點和最終體現。應試教育因為過于強調統一的標準和篩選淘汰,不可能認真地去關心不同學生的個性的發展。肯定共同性而否定個別性的是這種教育的價值取向,由此,對于在共同性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學生,則不得不放松甚至放棄教育。而在素質教育中每位學生都受到同樣的重視,學生不同的特點都受到尊重,并且主張在課程設置、教學形式、評價方式等各個方面為學生個性的發展創造條件。
素質教育是大眾的教育。近代以來,是英才教育還是大眾教育一直是不同的教育理想和政策的根本分歧。大眾教育并不排斥英才教育,并且為英才的成長提供多種可能,但在制定教育政策,安排教育財政時,不再將英才教育作為優先考慮的對象,而是以多數人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
小康教育的重新審視
“2019中國教育小康指數”調查結果顯示:52.4%的受訪者認為我國基礎教育在評價內容方面,過多側重學科知識特別是課本上的知識,忽視考查實踐能力、創新精神等綜合素質。推動中國教育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型是無數家長的共同心愿和期待,66.4%的受訪者認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存在最嚴重的問題是“應試教育”。
雖然我國針對教育不斷進行深化改革、強調素質教育,但應試教育的問題仍然突出。對此,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要改變這一形勢,需要從高考指揮棒入手,建立一套科學、完整的教育評價體系。“通過考試選拔人才,這種方式沒有問題。問題在于,需要打破‘唯分數的單一評價方式。”有人說,2020年的一場疫情把素質教育落實了。能夠嚴格自律的人,無論是在校學習,還是居家學習,都絕對不會差。2020年因為特殊原因,學校遲遲不能開學,即使是開學最早的青海省高三年級,也比往年推遲了一個月時間。很多人認為推遲開學,上網課,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而有教育專家認為,2020年高考中脫穎而出的,就是人才,不是為了應試拼命備考的結果,而是自我提高素質的結果。
他們認為,網課教學環境,能夠讓真正的人才冒出來,他們的分數就是素質的體現,因為這些學生,都有很強的自律性,有很強的自控能力。這些學生,能夠嚴格制訂并執行自己的學習計劃,這是一種最體現素質的因素,在沒有老師督促的情況下,完成學習計劃。能做到這一點的人,或是出于學習的興趣,或是出于良好的習慣,或是出于對責任的理解。
新目標:公平而有質量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發展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要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自身命運,成就人生夢想。
教育公平與否,事關每個孩子的成長和幸福。沒有教育公平,就沒有起點平等和機會平等。近年來,國家連續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的比例,從“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到包括清華大學“自強計劃”、人民大學“圓夢計劃”等名校招生政策,措施不同,但目標一致——拓寬貧困生進入名校的渠道,讓更多貧困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得以實現。
但是,事實上,城鄉教育差距問題依然突出。“現在城市與鄉村、大城市與一般的城市、首都與其他城市教育,最根本的差距在教師。”在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長朱永新看來,村里的好教師到鎮上去,鎮上的好教師到縣里,縣里的好教師到市里,市里的好教師到省會去,省會的好教師到北京、上海、深圳去,這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怎么應對和遏制這種現象?一方面要通過加大鄉村教師支持補貼力度,鼓勵優秀教師到農村去,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調動退休教師、知識分子、科學家等民間志愿者的力量。
國家早已認識到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于2015年6月開始實施《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華中師范大學課題組,通過對湖北、河南、安徽、四川、云南、陜西等省12個縣(區)120余所農村中小學進行問卷調查和結構性訪談得出的結論是:該計劃實施3年來,效果明顯,初步解決了鄉村教師“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問題。成都乾躍教育集團磨難課程實施多年,已吸引大批大學生與教育志愿者參與,“讀好書”與“好習慣效能養成”成為當地學生家長信奉的“霸氣項目”,接受有質量的教育已成為學生與家長的自覺意愿。
2020年,已走過脫貧攻堅的關鍵之年,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門檻上,作為“兩不愁三保障”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實現義務教育全面保障。過去的一年,教育部把控輟保學擺在“重中之重”,納入2019年“奮進之筆”,密集出臺了一個接一個的文件,層層壓實工作責任,健全精準控輟長效機制。這一年,政府在兜住義務教育質量的底線上持續發力,義務教育“城擠村弱”得到有效緩解,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取得明顯成效。
(本期照片均為成都乾躍教育集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