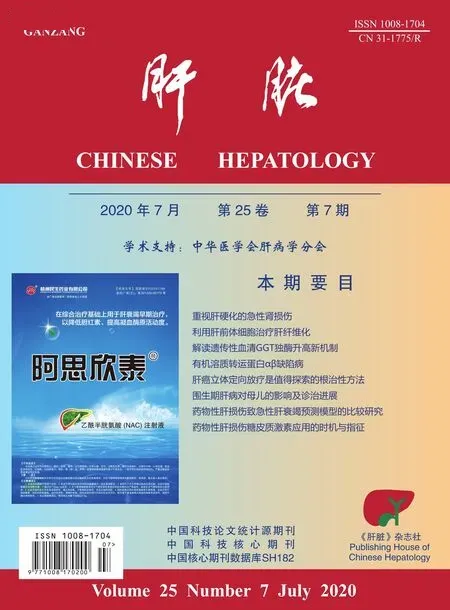藥物性肝損傷致急性肝衰竭預測模型的比較研究
楊瑞園 劉立偉 羅娟 李軻鑫 田秋菊 王艷 趙新顏 賈繼東
藥物性肝損傷(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臨床常見的肝臟疾病之一,也是美國及歐洲急性肝衰竭最常見原因[1-3]。法國前瞻性研究提示DILI發生率為13.9/10萬,美國發生率為2.7/10萬,韓國回顧性研究提示DILI的發生率為12/10萬/年[4-6]。我國一項納入25 927例DILI病例的多中心回顧性研究中,DILI發生率為24.20/10萬,明顯高于其他國家,其中13%發展為慢性DILI,1.08%發生急性肝衰竭[7]。
DILI導致急性肝衰竭可危及患者生命,早期、及時、準確識別急性肝衰竭,從而采用更為積極的治療策略是DILI診治過程中的重要環節[1, 8, 9]。各國學者提出多種模型,如Hy’s法則、新Hy’s法則等能夠較為準確識別急性肝衰竭的發生[10]。
本研究比較上述模型預測急性肝衰竭的效能,為臨床醫師合理選擇上述模型、準確識別DILI所致急性肝衰竭及預后判斷提供依據。
對象和方法
一、研究對象
收集自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診斷為藥物性肝損傷的住院患者298例。納入標準:年齡≥18歲;使用Roussel-Uclaf因果關系評估法進行評估,RUCAM評分需≥3分[11, 12]。排除標準:合并其他肝臟疾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酒精性肝病、遺傳代謝性肝病、膽道梗阻、缺血性肝炎等,影像學提示肝臟、膽系或胰腺惡性占位;臨床或實驗室數據缺失或不全。
二、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基線資料(性別、年齡)、導致肝損傷相關用藥史(藥物類型、服藥時間及劑量、療程、起止日期、藥物肝毒性信息等)、既往史、飲酒史、住院時間、實驗室檢查(血常規、肝功能、凝血指標等,除外其他肝損傷原因相關病毒、免疫、代謝檢查指標)以及腹部超聲、CT、MRI。
DILI的臨床分型采用由國際醫學組織理事會制定的判斷標準:肝細胞損傷型:ALT≥3×ULN,且R≥5;膽汁淤積型:ALP≥2×ULN,且R≤2;混合型:ALT≥3×ULN,ALP≥2×ULN,且2 DILI嚴重程度劃分標準依據2015我國年DILI指南[15],急性肝衰竭診斷標準依據美國肝病協會(AASLD)定義,即既往無肝硬化,出現膽紅素增高且凝血功能異常(INR≥1.5),伴不同程度精神異常,病程小于26周[16]。 Hy’s法則[17]:ALT或AST>3×ULN和TBil>2×ULN,ALP< 2×ULN;新Hy’s 法則:TBil>2×ULN,nR ≥5(nR值定義為:(ALT或AST兩者中的高值/ALT或AST ULN)/(ALP實測值/ALP ULN);Robles模型[10]:AST >17.3×ULN且TBil>6.6×ULN的患者,及AST ≤17.3×ULN但AST/ALT 比值>1.5的患者。 通過HIS系統查詢、電話咨詢等方式對患者信息進行隨訪,記錄出院后實驗室檢查,結果記錄肝硬化、肝移植和肝病相關死亡等事件的發生情況。隨訪起始時間為出現肝損傷時間,隨訪時間間隔為從隨訪起始時間后1年或發生肝移植或死亡的時間。肝臟生化學指標恢復正常定義為ALT或AST<1×ULN,且TBil<1.5×ULN,ALP<1×ULN[18]。 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 24.0軟件進行分析。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校正卡方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98例DILI患者中,女性211例(70.8%),年齡為(54.7±14.7)歲,常見臨床癥狀為乏力(32.5%)、納差(29.3%)、黃疸(21.7%)。 根據國際醫學組織理事會制定的判斷標準,本組病例表現為肝細胞損傷型230例(77.2%),膽汁淤積型為19例(6.4%),混合型49例(16.4%)。不同分型間DILI患者的ALT、AST、AST/ALT、ALP、GGT、TBil、TBA、Alb等生化學指標及PTA、INR等凝血功能指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各型DILI患者實驗室檢查結果比較[例,M(QR)] 在298例DILI患者中,13例(4.4%)出現急性肝衰竭,5例(1.7%)患者因肝臟原因死亡或行肝移植,14例(4.7%)發展為肝硬化。而在藥物致急性肝衰竭病例中,61.5%是因中藥引起的肝損傷。13例ALF病例中,12例為肝細胞損傷型,1例為混合型。 如表2所示,144例(48.3%)DILI由中藥引起,38例(12.8%)為中西藥聯用者;各類化學藥物及生物制劑引起肝損傷為116例(38.9%),其中聯合用藥12例。除中草藥外,前3位引起DILI的單藥為心血管系統藥物(20例,6.7%)、抗感染藥物(18例,6.0%)、非甾體類抗炎藥(15例,5.0%)。 表2 引起藥物性肝損傷可疑藥物分布情況 在298例患者中,160例符合Hy’s法則標準,其中9例(5.6%)發展為急性肝衰竭。208例符合新Hy’s法則標準,其中12例(5.8%)發展為急性肝衰竭。73例符合Robles模型標準, 11例(15.1%)發展為急性肝衰竭。如表3所示,Robles模型具有最高的特異度和陽性預測值;新Hy’s法則敏感度最高。通過配對卡方檢驗,分別比較各個評估指標在不同方法間的差異,Hy’s法則與新Hy’s法則兩種方法敏感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特異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前者約登指數為0.16,后者為0.24。新Hy’s法則與Robles模型比較,敏感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特異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表3 DILI致急性肝衰竭預測模型對比 通過比較三種臨床分型在1、2、3、6及12個月肝臟生化學指標恢復情況,發現不同臨床類型肝臟生化學指標恢復正常情況在3、6、12個月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但經兩兩比較調整后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4)。 表4 3種DILI臨床類型患者肝臟生化指標恢復正常時間比較[例(%)] 比較三種預測模型在不同隨訪時間生化指標恢復正常百分比,Hy’s法則及新Hy’s法則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達到Robles模型標準的DILI患者肝臟生化復常率在1、2、3、12個月顯著低于未達到該標準的DILI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圖1)。 注:A:符合Hy’s法則模型判定標準與不符合該標準肝臟生化指標在不同隨訪時間恢復正常比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B:符合新Hy’s法則模型判定標準與不符合該標準在不同隨訪時間恢復正常比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C:Robles模型符合判定標準與不符合標準肝臟生化指標在不同隨訪時間恢復正常比例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ns:P>0.05;*:P<0.05;**:P<0.01;***:P<0.001 DILI是急性肝損傷的常見原因,多為特異質損傷性、具有不可預測性,臨床后果嚴重。在歐美國家藥物引起的肝衰竭位居首位,有研究表明在未行肝移植的藥物致急性肝衰竭病例中,病死率達80%[10]。在我國藥物性肝衰竭已成為亞急性肝衰竭最主要原因,急性肝衰竭的第三位原因[19]。重視對于藥物性肝損傷嚴重程度及預后的早期判斷,是診治過程的關鍵點。既往研究建立了很多DILI預后模型,這些模型多采用臨床常用指標,在DILI發病初期,通過不同指標的組合,預測肝衰竭,實用性強。 本研究中的DILI患者,以中年女性為主,導致肝損傷的藥物主要為中藥及中西藥聯合用藥,有4.7%的DILI患者發展為肝硬化,4.4%出現急性肝衰竭,出現肝衰竭比例高于既往研究,主要考慮為選取病例皆為住院患者,嚴重程度高于門診就診患者。研究表明,肝細胞型肝損傷較淤膽型和混合型更易發展為肝衰竭,如APAP所致肝損傷在肝細胞型損傷患者中肝衰竭出現頻率最高(7%~13%),在混合型肝損傷患者出現頻率較少(2%)[20],本研究亦能驗證該觀點。 本研究比較三種預測模型的敏感度及特異度,綜合評估各個模型預測價值,供臨床醫師參考。結果表明,符合Robles模型的DILI患者,發生急性肝衰竭或行原位肝移植風險更高,其敏感度、特異度高,陽性預測值優于傳統方法,該算法也被更多指南所認可并推薦[21]。相比之下,新舊兩種Hy’s法則敏感度較高,但特異度均較差,相比之下,Robles模型優勢更為明顯。 本研究中,肝細胞損傷型為主要臨床分型,與既往文獻報道相符合[22],對于入組病例肝臟生化學指標恢復情況來看,提示臨床分型對于預后評估欠佳,混合型及膽汁淤積型DILI預后無法通過臨床分型區分。本研究還發現Robles 模型的另一作用,可預測患者1年內生化指標復常率,即符合Robles模型的患者,其生化復常率顯著低于未滿足該模型的患者,提示Robles模型除預測急性肝衰竭效果較佳外,還具有預測長期預后(肝臟生化指標復常率)的能力。相比之下,Hy’s法則與新Hy’s法則均不能有效預測患者1年內肝臟生化指標的復常率。 本研究比較了3種預測模型的效能,系統梳理了三種模型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對臨床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然而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入組均為住院治療患者,無法真實反映DILI總體特征。此外本研究樣本量中等,急性肝衰竭病例量少,需多中心大樣本量的前瞻性研究進一步評估預后模型的效能。 綜上所述,與Hy’s法則及新Hy’s法則比較,Robles模型預測DILI患者出現急性肝功能衰竭的特異度及陽性預測值最優,該模型還能更準確的預測患者1年內生化復常率,值得在臨床實踐中加以推廣。三、預測模型
四、隨訪
五、統計學方法
結 果
一、人口學特征及基本資料
二、各型DILI患者實驗室檢查結果比較

三、嚴重預后
四、致DILI藥物種類

五、不同預測模型效能比較

六、比較不同臨床類型及預測模型對生化指標恢復時間的判斷


討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