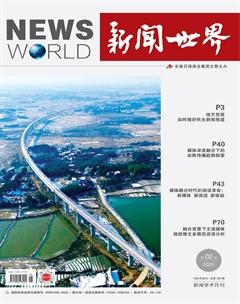文博類紀錄片媒介儀式的雙重建構
米雅璐 袁文麗

【摘? ? 要】儀式傳播是通過一系列儀式符號來表達意義和傳遞情感以實現文化共享的傳播活動。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立足于文物特有的歷史文化價值,通過年輕化的語態,營造了一個守護國寶、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電視媒介儀式,從而激活了觀眾深藏心底的民族文化記憶。本文從新媒體語境下電視媒介儀式建構的雙重路徑入手,揭示文博類紀錄片的模式創新與傳播機制。
【關鍵詞】文博類紀錄片;媒介儀式;彈幕文本;如果國寶會說話
作為傳播民族風貌和文化內涵的重要媒介,電視紀錄片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構民族身份認同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文物是華夏文明的遺存和見證。文博類紀錄片通過影像語言對文物及其背后故事進行二次創作,既完成了對傳統文化的創新性表達,也實現了對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價值堅守。2018年伊始,由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制作的百集微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走進大眾視野。從新石器時期到宋元明清,從三星堆到古滇國,該片精選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時期的100件國寶級珍貴文物,每集5分鐘以全新視角講述文物的前世今生,被譽為“紀錄片里的一股清流”。在《如果國寶會說話》中,文物不再是塵封在博物館里的藝術品,而成為勾連起傳統和現代的文化符號,彰顯著中華文化的厚度和深度。本文以該片為例,梳理文博類紀錄片建構媒介儀式的雙重路徑。
一、文博類紀錄片媒介儀式建構路徑
現從電視媒介儀式建構的兩個主要維度即儀式主體和儀式客體入手,以《如果國寶會說話》為例,剖析文博類紀錄片建構媒介儀式的方法與路徑。
(一)儀式建構主體:群體關聯中的自我實現
儀式本是宗教術語,指傳教士和前來參加儀式的信徒們共同參與禱告的過程。不同于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儀式傳播最主要的特點是強調儀式參與者的主體性地位。[1]在儀式傳播框架下,傳受雙方不再被視作信息接收過程的兩端,而是所有人協商合作、平等交往,共同建構儀式的意義,進而成就現實,規范社會秩序。在《如果國寶會說話》每集短短的5分鐘里,作為虛擬主體存在的詩意解說、接受采訪的各界人士及屏幕前的觀眾合力建構了一個溫情而莊嚴的媒介儀式。
首先,詩化解說引領擔綱。作為儀式建構的虛擬主體,解說詞在電視紀錄片媒介儀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如果國寶會說話》中,散文詩般優美的文案讓節目充滿了詩意,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來自泥土,頭微微揚起,仿佛仰望天空。六千年時光流轉,仿佛剎那間,村落成了國,符號成了詩,呼喚成了歌”,來自新石器時期的紅陶器皿人頭壺承載了敘述者對宇宙、時間、生命的思索。借助現代的視聽語言,歷史文物完成了以器傳道的文化使命,在凝練、思辨、靈動的表達中仿若再生。在介紹殷墟嵌綠松石甲骨時,敘述者更是以豐富的想象穿越歷史時空,為觀眾搭建起獨立的思考空間。“此刻,我們寫出的橫豎撇捺,曾經一筆一畫地刻在骨頭上。因為刻骨,所以銘心。”敘述者既借文物追問了歷史時空,又與現代時光呼應,幫助畫面實現了意義擴容,建構起歷史與現實共生的敘事空間,充滿了哲理與思辨意味。
其次,采訪嘉賓站在平民視角敘事。一直以來,我國文博類紀錄片多采用宏大敘事框架,站在國家、民族的高度展開敘事,往往缺乏對個體生命與現實生活的關照。《如果國寶會說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博類紀錄片在敘事框架上的范式轉向:在表達立場上,該片弱化了官方表達,以平等的姿態與觀眾交流;在內容方面,該片關注普通人的內心世界,注重其個體命運和生活狀態的表達;在視角方面,該片以小人物、小故事為切口,透過個體表達勾連出微觀生活背后的宏觀社會背景。這樣的創作取向尤其體現在節目對采訪嘉賓的選擇上。《如果國寶會說話》沒有與其他同類題材的紀錄片一樣,邀請權威的專家學者為觀眾做講解,而是將鏡頭轉向了大批默默工作在行業一線的普通人,他們中有兼職服裝設計師,有鬧市中的說書人,有從業近十年的博物館講解員,也有中央民族樂團的青年演奏家……節目從他們與文物之間的故事出發,以樸素的鏡頭、平實的語言及生活化的場景展現出文物背后的歷史議題,風格溫暖而親切、淳樸簡單,激發了觀眾高度的情感共鳴。
最后,觀眾聯動實現反向傳播。相比傳統傳播范式,儀式化傳播更加強調群體關聯,傳受雙方不再通過簡單的信息傳遞連接,而是以文化共享的形式共同參與到儀式的建構中,并最終實現對參與者的文化認同動員。儀式中多個異質主體之間并不是獨立的,媒介儀式的建構有賴于儀式主體間的互動行為和互動關系,這一點在新媒體語境下體現得更為明顯。當《如果國寶會說話》被同步到彈幕視頻網站bilibili后,其詩意、唯美的敘事風格迅速得到了年輕觀眾的認可,他們對傳統文化強烈的價值期待使得節目的粉絲呈現“井噴式”增長。在青年群體的推動下,該片在社交平臺的口碑持續發酵,形成熱門話題,進而得到了傳統媒體的關注和報道,實現了文化產品由新媒體平臺至傳統媒體的反向傳播。
(二)儀式建構客體:價值載體與文化認同
在媒介儀式中,一些具有強烈文化意向和歷史隱喻的標識物通常被設定為儀式的重要載體。文物是華夏文明的遺存和見證,蘊含著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傳統和數千年的文化記憶。在《如果國寶會說話》中擔當標識物的是100件精心挑選的國寶級文物,它們代表了每個時代頂級的工藝水平,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和藝術價值。總體而言,這些文物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地域性折射鄉土情結。傳播儀式觀認為,人們之所以能生活在同一個社區,在于他們擁有共同的信念目標、知識框架及情感傾向,這也是一個群體得以建構的基石。[2]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由于受到農耕文明傳統和儒家倫理的長期浸染,一直以來,鄉土情結是中國人身上一枚特殊的烙印,是民族向心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國寶會說話》中的文物選自21個不同省市,反映了各地政治、歷史、人文等區域特征,帶有鮮明的地方色彩。這其中有來自山東考古研究所,代表黃河中下游地區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杯;有出土自四川廣元三星堆遺址的神秘青銅人像;還有發掘于河南安陽殷墟的婦好鸮尊……各地文物在節目中得到推廣和認同,對于當地觀眾而言是值得自豪的事,基于地域的身份認同在此時被激發出來,進一步喚醒了觀眾內心深處潛藏的鄉土家國情懷。
形式美提升美學意境。形式美是一個美學詞匯,指構成事物物質材料的自然屬性及其組合規律所呈現出的審美特性。它是體現美學境界的一個重要指征,其基本法則包括對稱、均衡、節奏、比例的和諧、方圓的變化等。在形式美諸多基本法則中,多樣統一是最高表現形式,體現在作品里即和諧。《如果國寶會說話》中呈現的國寶,其所屬時代、鑄造工藝、用途都不盡相同,既有用于大型祭祀的禮器,也有柔美多情的女性飾物;既有調動千軍萬馬的兵符,也有發出兩千年前中國之聲的古樂器。它們在造型上既各具特色,又彼此關聯、交相輝映,既豐富又純粹,既發散又內斂,既多樣又統一,形式美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擬人化吸引年輕受眾。擬人化本是一種修辭手法,是將非人的事物人格化,賦予其“人性”色彩。在《如果國寶會說話》中,歷史文物常被賦予人的思想情感和生命體征,以第一人稱視角穿越古今向觀眾傾訴衷腸。如在介紹葡萄花鳥紋銀香囊時,節目突破了傳統解說的形式,大膽地將文物擬人化,借香囊之口述說了唐玄宗與楊貴妃之間唯美的愛情故事。輕松活潑的語態消解了傳統文化類紀錄片的嚴肅刻板,營造了觀眾與遠古文物對話的現代語境,猶如朋友間的閑聊,消弭了歷史文物的神秘感和距離感,在網絡上吸引了大批年輕受眾。“萌”是當下火熱的審美現象,節目在介紹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遺存——陶鷹鼎時也借用了這個網絡熱詞,將陶鷹鼎描述為有著“胖胖腿”的鷹,用“萌萌噠”的形象展示著“肌肉萌”,靈動而傳神。
二、基于彈幕場域的媒介儀式再建構
傳播渠道方面,《如果國寶會說話》最大的特點是采用了臺網同播的模式,年輕受眾能夠通過B站關注節目,并依據觀后感受自由發送彈幕,與其他網友互動。通過彈幕再生產,節目將松散的網民聚集為網絡文化共同體,共同建構起彈幕場域中傳統文化傳播的媒介儀式。[3]
(一)作為群體黏合劑的網絡表達
觀眾在互動過程中,通過彈幕文本的生產主動參與傳播儀式的框架建構,在彈幕場域內搭建的網絡話語體系連接了節目內容與傳播儀式,建立起想象的共同體,并由此對節目內容產生情感共鳴。在文化形態上,傳統文化與新生代文化存在著天然的差異。傳統文化給觀眾的印象是嚴肅、厚重、遙遠的。今天,傳統文化傳播的關鍵在于如何擺脫嚴肅刻板的話語體系,以年輕人樂于接受的方式進行傳播。作為一個以彈幕互動為標簽的新媒體平臺,B站提供了一個傳統文化與網絡文化的對話空間。在紀錄片播放過程中,屏幕上方懸浮著大量匿名評論,且多為二次元風格表達。盡管題材嚴肅、目的性明確、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博類紀錄片在網絡敘事下被多重解構,甚至被重塑為二次元的網絡符號,可從現實的傳播效果來看,新媒體形式的解讀卻并未偏離節目原有的價值取向和情感內核,反而因彈幕互動使觀眾增強了觀看樂趣,增進了情感和文化認同。《如果國寶會說話》每集臨近結束時彈幕都會掀起一個贊美文物、表達民族文化自信的小高峰,出現頻率最高的內容是希望傳承民族傳統文化,引發了網友的刷屏行為。在這一過程中,網民們以文本狂歡的形式構建網絡敘事話語體系,并通過與他人頻繁的符號性互動,形成了借由符號認知、認同而確定的群體關系。[4]
(二)借助擴容與重構實現文本再生產
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認為,電視文本應具有開放性,它甚至可以被描述為主流意識形態與觀眾之間的博弈場。基于電視文本具有“開放式”特征,費斯克提出了“生產者式文本”的概念(即承認受眾自我解讀和創作權力的文本),用以描述電視這種“大眾的作者式文本”。[5]原初文本被擴展了解釋空間,向受眾提供了對內容進行二次加工的機會,從而實現文本擴容與意義重構。紀錄片中許多場景和畫面沒有過多的旁白和解說,在原初文本空白、充滿不連貫性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B站受眾以發送彈幕的方式對紀錄片進行了大量的細節補充,使得該片在B站的意義呈現更加豐富。受眾通過發送彈幕對視頻內容進行實時評論、吐槽、補充,這種彈幕再生產,使B站受眾實現了對傳統電視紀錄片的文本生產,其主體性是借由技術中介在特定文本的創造性生產過程中獲得的。例如在《后母戊鼎:國之重器》一集中,當節目以動畫形式還原四千年前后母戊鼎的鍛造場景時,大量關于青銅器冶煉原理和鑄造工藝的彈幕刷屏,這種對歷史背景的補充和探討使節目的知識量得到拓展。而《曾侯乙編鐘:中國之聲》一集,短短5分鐘,節目采用播放歷史音頻(1986年采錄于湖北博物館)的呈現方式。由于整個過程沒有解說,網友們自發充當講解員角色,在彈幕中討論編鐘及其他中國傳統樂器的發聲原理和相關的樂理知識。在彈幕的討論中還會發現許多未詳細說明的細節,如一些文物上刻畫的圖騰和附著的紋飾,盡管紀錄片解說詞中并未提及,但觀眾會在彈幕里自發討論,闡釋其合理性,甚至塑造出與原片完全不同的意義空間。
注釋:
[1]張孝翠.論儀式傳播與參與主體性[J].國際新聞界,2009(04):41-44.
[2]詹姆斯·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M].丁未 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3]張錚,鄧妍方.從《國家寶藏》探析傳統文化在彈幕場域的建構[J].電視研究,2018(07):35-37.
[4]譚宇菲.新媒體場域中傳統文化傳播儀式建構研究——以《我在故宮修文物》為例[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7(09):114-116.
[5]張瀟揚.“生產者式”電視文本的現代性解讀——基于約翰·費斯克的媒介文化研究視角[J].當代傳播,2014(04):23-25.
(作者:米雅璐,山西大學新聞學院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袁文麗,山西大學新聞學院新聞系主任、副教授)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