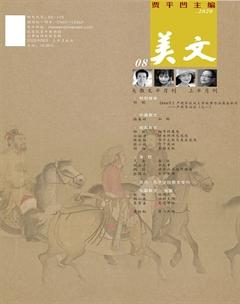書中太極與意在筆先
陳俊哲

悟書中太極 得筆力驚絕
人類在大自然的巨大力量面前,覺得無比卑微和渺小,因而與生俱來產(chǎn)生了對(duì)“力”的向往和崇拜之情,這種感情在中國(guó)書法藝術(shù)中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無論甲骨、鐘鼎,還是秦篆、漢隸,抑或魏碑、唐楷,無不表達(dá)了對(duì)力量的追逐。《筆陣圖》云:“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王僧虔《論書》云:“張芝、索靖、韋誕、鐘會(huì)、二衛(wèi)并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yōu)劣,惟見筆力驚絕耳。”書法藝術(shù)一開始就把“筆力”放到了至為重要的位置,奉為衡量書家水平高低書作優(yōu)劣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而成為書家的終生追求。然何得“筆力”以至于“筆力驚絕”之境?
用筆能“整”
書寫的過程,非是指力、腕力,肘力各自為政,而是肩、臂、肘、腕、指乃至于全身每個(gè)部分的相互協(xié)調(diào),有機(jī)聯(lián)動(dòng),形成系統(tǒng)合力,得一身“整勁”“渾勁”,盡一身之力于毫端,缺一都會(huì)“力不從心”“力所不及”。書法是全身運(yùn)動(dòng),如同打太極拳之周身一體,其力根于腳,發(fā)于腿,主宰于腰,發(fā)于脊背,達(dá)于肩臂,行于手指,由腳而腿而腰,一直到指端,總須連貫成一身“整勁”,完整一氣,前后左右,乃能得機(jī)得勢(shì)。有不得機(jī)得勢(shì)處,身便散亂,力便分散。走極端地提出“死指活腕”(姚孟起《字學(xué)臆參》,強(qiáng)調(diào)某個(gè)部位而否定另一部位,就要誤導(dǎo)后學(xué)了。周星蓮《臨池管見》一針見血指出:“不知腕固宜活,指安得死?肘使腕,腕使指,血脈本是疏通,牽一發(fā)全身尚能皆動(dòng),何況臂指之近乎?”
用筆能“盡一身之力”,形成“整勁”,乃取得高質(zhì)量點(diǎn)畫的前提,在筆法技法體系中處于重要位置。《筆陣圖》云:“下筆點(diǎn)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包世臣《藝舟雙輯》強(qiáng)調(diào):“點(diǎn)畫細(xì)如絲發(fā),皆須全身力到。”這全身各個(gè)部位力量如何運(yùn)轉(zhuǎn)呢?清人程瑤田《九勢(shì)碎事》講得具體到位:“書成于筆,筆運(yùn)于指,指運(yùn)于腕,腕運(yùn)于肘,肘運(yùn)于肩。肩也、肘也、腕也、指也,皆運(yùn)于右體者也,而右體則運(yùn)于左體。左右體者,體之運(yùn)于上者也,而上體則運(yùn)于下體。下體者,兩足也;兩足著地,拇踵下鉤,如履之有齒以刻于地者,然此之謂下體之實(shí)地。下體實(shí)矣,而后能運(yùn)上體之虛。然而上體亦有其實(shí)焉,實(shí)其左體也。左體凝然據(jù)幾,與下貳相屬焉,由是以三體之實(shí)而運(yùn)其右一體之虛,而于是右一體者乃其至虛而至實(shí)者也。夫然后以肩運(yùn)肘,由肘而腕、而指,皆各以其至實(shí)而運(yùn)其至虛。”長(zhǎng)年潛心于書而筆力孱弱的原因多是不得“盡一身之力”,立志學(xué)書者不得不察。
用筆能“活”
用筆之難,就難在遒勁有力,而遒勁有力決非是肌肉和關(guān)節(jié)“怒筆木強(qiáng)”,用直逼逼之僵硬拙勁、生拉硬拽之呆滯之力,而是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所云“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之“巧力”“活勁”(如體操運(yùn)動(dòng)員般能倒能起),亦是倪蘇門《書法論》所云“搦筆極活極圓,四面八方,筆意俱到” 。可以說,筆力的關(guān)鍵在化僵滯為松活。
活的前提是松,包括意念放松和肢體放松。首先是意念松。“欲書之時(shí),當(dāng)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玄妙。”(唐太宗《筆法訣》)排除雜念,洗心滌慮,心無掛礙,以引導(dǎo)各部位關(guān)節(jié)肌肉節(jié)節(jié)放松,無一僵一滯。惟松方能感覺和反應(yīng)敏銳,即時(shí)感知“筆端消息”之大小、方向、作用點(diǎn)等等,從而有效控制并駕馭筆毫,“隨提隨按,亦提亦按,若離紙,若不離紙,處處有提按……能隨意轉(zhuǎn)換。”(劉遵三《歷代書法家述評(píng)輯要》)而“其行筆也,滾跳擲翻,勢(shì)不能已,每筆皆具起止,又轉(zhuǎn)令鋒正自然”(徐用錫《字學(xué)札記》)。松是拳之魂,亦是筆之靈。身心俱松,如太極拳般“周身柔軟僅無骨,忽然放開都是手”,以“極筋所能至,使之內(nèi)氣通而外勁出”(包世臣《藝舟雙輯》),處處相應(yīng),上下協(xié)調(diào),意在筆先,筆隨意走,隨勢(shì)賦形,翰逸神飛,讓筆力無所不在。
用筆能“逆”
用筆之“逆”,如同車下坡掛上檔,有齒輪咬合,車子向前的“順勁”中,還有向后的“逆勁”相對(duì)抗,不讓車子虛漂甚至失控。亦好像在水中打拳、又似空氣是粘稠的,有向后的“逆勁”阻力制約,拳打出去才有力。寫字也一樣,沒有紙咬住筆毫的“逆勁”,一掠而過,留不住筆,就會(huì)直率、飄浮和油滑。即使筆道粗如椽,蘸墨如水注,也難入紙,終究線條質(zhì)量不高。
《周易·系辭下》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一種昆蟲的幼蟲,把身體向上彎曲,以反向的逆勢(shì)求得前進(jìn)。《周易》智慧給了人們書法用筆無限思想啟迪。笪重光《書筏》云:“將欲伸之,必故屈之……將欲行之,必故停之。書亦逆數(shù)焉。”周星蓮《臨池管見》云“字有解數(shù),大旨在逆。縮者伸之勢(shì),郁者暢之機(jī)”。以縮求伸、因郁得暢,逆勢(shì)用筆無疑是古人對(duì)用筆規(guī)律的深刻揭示。
米芾《論書》把逆勢(shì)用筆內(nèi)容高度概括為“無垂不縮,無往不收”,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奉此為“八字真言,無等等咒也”。然而“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并非收筆處作一筆鋒回復(fù)動(dòng)作,而是在行筆的全部過程中,施“提按頓挫”之巧力,顯“遲速行留”節(jié)奏,時(shí)時(shí)具“收縮”之逆勢(shì),備“往”“垂”之順暢。具體說來,就是筆管朝筆畫反向傾斜,筆錐挺起來,行筆時(shí)前面如有物阻拒,筆毫在受擠壓并竭力與之抗?fàn)幹星靶校谏稀⑾路较騼煞N力的對(duì)抗和左、右方向兩種力的雙重對(duì)抗中,才會(huì)有“點(diǎn)如利鉆鏤金,畫似長(zhǎng)錐界石”(張懷瓘《玉堂禁經(jīng)·結(jié)裹法》)的感覺,才可寫出來古人所謂“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高質(zhì)量的線條來。
高質(zhì)量的線條是克服困難,頂住壓力,戰(zhàn)勝阻力,始終讓筆鋒不倒于天地之間寫出來的,這樣的線條才是最美。如今有誰(shuí)面對(duì)載于中國(guó)歷史的玄奘法師西行取經(jīng)走出來的“線條”,以及中國(guó)工農(nóng)紅軍萬里長(zhǎng)征走出來的“線條”不拍案驚絕?“師法造化”者,當(dāng)由此開悟。
“整”是筆力之前提,用筆未“盡一身之力”,則力怯;“活”是得筆力之關(guān)鍵,身心僵滯,則力死;“逆”是筆力的核心內(nèi)容,沒有逆勢(shì)阻力,則失力。筆力的形成是用筆“整”“活”“逆”三者的統(tǒng)一。學(xué)習(xí)太極拳入門須得三勁:整勁、活勁和逆勁,拳道與書道本出一轍,書中自有太極。自作詩(shī)《硯邊絕句》云:
悟得活松彈抖勁,
方能順勢(shì)撥千斤。
書中太極何人曉,
手滯心昏枉用勤。
也談 “意在筆先”之意的模糊性
書法創(chuàng)作歷來是講究“意在筆先”的。王羲之云:“夫欲書者,先干研墨,凝神靜思,預(yù)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dòng),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后作字。”(《題衛(wèi)夫人筆陣圖后》)韓方明在《授筆要說》亦云:“夫欲書先當(dāng)想,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yǔ)多少,及紙色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dāng)。然意在筆前,筆居心后,皆須存用筆法,想有難書之字,預(yù)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筆,自然從容徘徊,意態(tài)雄逸,不得臨時(shí)為法,任筆所成,則非謂能解也。”《板橋題畫三則》繼而云:“意在筆先者,定則也。”古賢們都強(qiáng)調(diào)下筆前須要有一個(gè)凝神、靜思,預(yù)想整幅作品寫什么,怎么寫的藝術(shù)構(gòu)思過程,須先形成一個(gè)創(chuàng)作意圖,做到意在筆先,胸有成竹。千百年來,后之學(xué)者無不將此奉為圭臬。
“意在筆先”構(gòu)思形成的意象、意圖其顯著特征是宏觀性、模糊性,而非越具體越清晰越好。陳望衡《藝術(shù)創(chuàng)作美學(xué)》云:“藝術(shù)構(gòu)思所構(gòu)造的意象是相當(dāng)寬泛的、模糊的,它只是在主要點(diǎn)比較清晰,比較明確,因而留有很大的伸縮余地。”陳望衡先生所云是符合認(rèn)識(shí)發(fā)展規(guī)律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實(shí)際上,模糊性是人類思維的一種品性,當(dāng)我們對(duì)孤立的相對(duì)靜止的事物觀察時(shí),容易得出事物樣態(tài)的清晰的精確的結(jié)論,然而當(dāng)我們對(duì)聯(lián)系的運(yùn)動(dòng)的事物觀察時(shí),又往往發(fā)現(xiàn)事物樣態(tài)的不確定性、模糊性。書法創(chuàng)作中的筆前意象的模糊性,源于構(gòu)成書法作品的點(diǎn)畫的連續(xù)運(yùn)動(dòng)性和普遍聯(lián)系性。
具體從兩個(gè)方面來說明:其一,從時(shí)間性的展開為線索來看,每一幅書法作品,都是在毛筆連續(xù)運(yùn)動(dòng)過程中生成的。由于運(yùn)筆力量、速度和方向等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點(diǎn)畫形態(tài),生成貫穿在點(diǎn)畫之間的筆勢(shì),生成一個(gè)個(gè)結(jié)體及其體勢(shì),生成字組及其組勢(shì),生成行及其行勢(shì),繼而生成一幅完整的書法作品。這個(gè)生成一幅完整書法作品的過程,具有連續(xù)運(yùn)動(dòng)的特征。從一幅書法作品的空間關(guān)系來看,一幅作品的點(diǎn)畫與點(diǎn)畫之間、結(jié)體與結(jié)體之間、字組與字組之間、行與行之間甚至是空白與空白之間的俯仰向背、敧側(cè)呼應(yīng)等等的對(duì)立而統(tǒng)一,在空間上具有普遍聯(lián)系的特征。書法創(chuàng)作中點(diǎn)畫在時(shí)間上的展開的連續(xù)運(yùn)動(dòng)性,以及點(diǎn)畫運(yùn)動(dòng)形成的各種造型元素在空間上分布的普遍聯(lián)系性決定了“意在筆先”意不可能做到精確和清晰化,只能做到大致的、籠統(tǒng)的、模糊的把握。
其二,書法作品中的一點(diǎn)一畫,都是從書法家心田里流淌出來的,是書法家的情感“心畫”在紙上的物化、可視化。書法家書寫中伴隨著大量的情感活動(dòng),這種情感活動(dòng),是一種流動(dòng)不息的,瞬息萬變的,而且又是豐富復(fù)雜的心理活動(dòng)。書法家在書寫過程中的情感活動(dòng)的豐富性、變化性及其復(fù)雜性,在一幅作品的書寫之前的構(gòu)思中,是不可能具體化的。意象是模糊的,下筆卻來不得一絲含糊。動(dòng)筆創(chuàng)作是對(duì)筆前構(gòu)思形成的籠統(tǒng)的模糊的意象、意圖的具體化、清晰化和實(shí)現(xiàn)。提筆濡墨入紙,積點(diǎn)畫成字、組、成行、成篇的過程中,就如同旅人上了路,各種難以預(yù)見的情況接踵而至,之前理性的“頂層設(shè)計(jì)”的意圖變成當(dāng)下的“摸著石頭過河”。這里“摸著石頭過河”,決非不諳事理的楞頭青情急之下的歪打誤撞,亦非江湖藝人的胡寫亂涂,更非伯樂兒子似的對(duì)古人經(jīng)典的按圖索驥、復(fù)制抄襲,而是書法家的人格、理想、目的、需要等等一切心理因素構(gòu)成的精神世界凝聚成一種情感力量,合于陰陽(yáng)對(duì)立統(tǒng)一規(guī)律以及此規(guī)律體現(xiàn)出來的規(guī)矩、法度的“合情調(diào)于紙上”。
具體到某個(gè)位置上的單字,其間架結(jié)構(gòu)到底如何寫、寫成什么樣才好?這是創(chuàng)作之先難以設(shè)定的。以王羲之《蘭亭序》中的“之”字為例,21個(gè)不同的位置上的“之”字,字字異勢(shì),各具美態(tài),神采照人,同自然之妙有,非筆前精于安排所能成,乃是書法家在21種具體書寫的形與勢(shì)、情與境面前的潛意識(shí)下的境由心造、道法自然、臨場(chǎng)決斷、隨勢(shì)賦形、因勢(shì)生形,無意于佳乃佳。預(yù)先安排,非但寫不好一個(gè)單字,更寫不好一幅完整的作品。王羲之后來又寫了幾遍《蘭亭序》,按說前面寫過了一遍,前后左右上下,所有字所有留白所有細(xì)節(jié)就像圖紙一樣擺在眼前,可是,總寫不出先前水平的作品,米芾題褚河南臨《蘭亭序》題跋感慨曰:“愛之重寫終不如,神助留為萬世法。”何哉?再次創(chuàng)作中不再是臨場(chǎng)決斷,不再是因勢(shì)生形,而是安排造型、照本復(fù)制。失去了模糊感,也失去了神秘感,戰(zhàn)場(chǎng)透明了,仗也就沒法打了。沒有了模糊和神秘,就沒有了變化,沒有了創(chuàng)造力,從而也就沒有了書法藝術(shù),而只能淪入“寫字”的江湖,這才是再也寫不出先前水平的根本原因。王澍《論書剩語(yǔ)》云:“作字不可預(yù)立間架,有意整齊與有意變化,皆是死法。”由此看來,那種作書之前預(yù)想字形、結(jié)構(gòu)的任何有違“意在筆先”模糊性規(guī)定的精于安排,都是違背書法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是徒勞而可笑的。
在實(shí)際書法創(chuàng)作活動(dòng)中,有經(jīng)驗(yàn)的書法家往往在下筆前只是對(duì)作品幅式、書寫內(nèi)容、字形大小、難書之字、書體、風(fēng)格等方面做“意在筆先”的預(yù)想,至于書寫過程中具體哪大哪小、哪重哪輕、哪快哪慢、哪收哪放、哪虛哪實(shí)等等變化及其變化后形成的對(duì)比和形勢(shì)關(guān)系的把握一任筆墨游走。這不是草率,而是因?yàn)樗麄兩钌畹亩茫瑒?chuàng)作是硬道理,只有進(jìn)入書法創(chuàng)作階段,才真正進(jìn)入書法家想要的藝術(shù)境界。正是意象的模糊性為書寫過程中的“窮變態(tài)于豪端,合情調(diào)于紙上”大開了綠燈。當(dāng)書法家全身心沉浸于創(chuàng)作時(shí),平時(shí)連想都想不到的精彩細(xì)節(jié)、造型、布局、章法等等奇妙地展現(xiàn)在眼前,“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面對(duì)意料之外的好作品自言自語(yǔ):“這是自己寫的嗎?”每每這個(gè)時(shí)候,我也像俄國(guó)作家果戈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時(shí)那樣,對(duì)忽然閃現(xiàn)在面前的美好靈感和題材“全身都感到一種甜蜜的戰(zhàn)栗”,情不自禁地說:“這是多么的快樂啊!”
自作詩(shī)《硯邊絕句》云:
筆前作意向來遵,
臨到揮毫半當(dāng)真。
算盡機(jī)關(guān)常被誤,
糊涂道是出奇新。
悟篆隸筆意,開草書新境
學(xué)習(xí)草書,強(qiáng)調(diào)直接取法“二王”,直追晉人筆墨的高妙,可謂“取法乎上”。但當(dāng)我們考察一下“二王”學(xué)書歷程發(fā)現(xiàn),“二王”取法篆隸,比我們更“取法乎上”。李世民《王羲之傳論》贊王羲之曰:“詳察古今,精研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草書是由篆隸演變而來,篆隸是草書的本原。正如姜夔《續(xù)書譜》所云:“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于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于蟲篆;點(diǎn)畫波發(fā),則出于八分;轉(zhuǎn)換、向背,則出于飛白;簡(jiǎn)便痛快,則出于章草。”從用筆、結(jié)字、篇章到形質(zhì)、神采等,篆隸對(duì)草書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傅山強(qiáng)調(diào)篆隸的重要性曾言:“不作篆隸,雖學(xué)書三萬六千日,終不到是處,昧所從來也。”清《書法正傳》亦云:“古人以書名者,必通篆籀,篆籀所以為諸體之本。”? 從“二王”,到顏真卿、懷素、鄧石如、吳昌碩、于右任等,留名青史的草書大家莫有不師法篆隸者。
誠(chéng)然,學(xué)草者師法“二王”沒錯(cuò),但不可止于“二王”,還須沿“二王”學(xué)書路徑向上逆推,師法更高古的篆隸。篆用筆的紆余婉曲、線質(zhì)的“力弇氣長(zhǎng)”,隸用筆的倔強(qiáng)激越、線質(zhì)的“勢(shì)險(xiǎn)氣短”,以及篆隸筆意表現(xiàn)出來的或雍容渾穆、或端莊典雅、或古樸淳厚、或率真天然的氣質(zhì)風(fēng)貌等等,是提升草書藝術(shù)審美,走出當(dāng)下書法展覽體千人一面窘境,開拓草書藝術(shù)新境界取之不竭的源頭活水。
《筆勢(shì)論》記載了王羲之告誡兒子的一句話:“勿播于外,緘之秘之。學(xué)篆籀,工省而易成。”原來書圣工省易成的不傳之秘在于篆隸,我等今天知之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