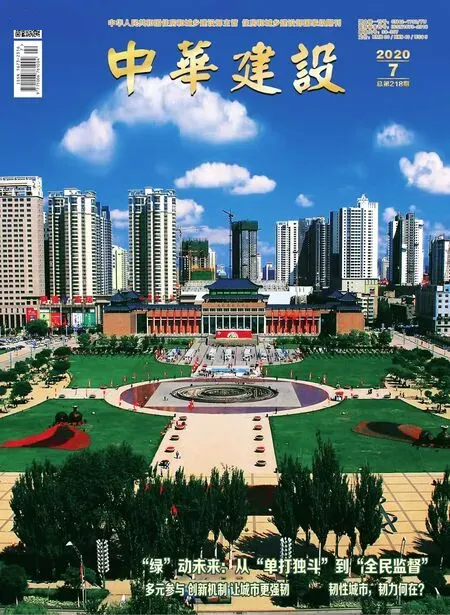多元參與 創新機制讓城市更強韌
本刊記者 李動
2020年,中國相繼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地震、洪澇災害等突發事件,尤其是疫情給中國乃至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突發事件沖擊下,作為區域資源要素聚集地的城市,顯露出其脆弱性。
為了應對不確定性風險,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城市除了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不斷進步外,還應加速城市韌性的建設和提升。
從城市規劃到城市防災
“韌性”一詞,源于物理學領域,主要用于描述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形變之后的復原能力。上世紀70年代,“韌性”這一概念首先被引入生態系統研究中。而后,韌性被引入城市規劃建設實踐中,尤其是在城市防災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就理論體系而言,韌性城市還是一個較新的領域,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概言之,韌性城市是指面對不確定風險時,能夠憑借其動態反饋、自我修復、冗余緩沖等自身特性,保持城市的主要功能和正常運行。這里所說的風險,既包括慢性壓力,如空氣污染;也包括突然沖擊,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指自然風險,如地震、臺風等;也指社會風險,如恐怖襲擊、社會動亂等。


韌性城市具備以下特性,一是多樣性,功能多樣化的城市更能抵抗不可預測的風險;二是冗余性,即具備應對風險的備份資源;三是穩健性,通俗的講整個城市系統是經得起“摔打”的;四是適應性和恢復能力,即城市系統能夠根據風險變化調整自身形態、功能或結構,同時在風險之后能夠自我恢復。
城市韌性描述的是城市應對發展過程中不可預測的沖擊,其范疇不僅僅指的是基礎設施,還應當包括經濟、技術、社會、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只有建立多維度的韌性體系,方能抵御多方面的風險沖擊。
上世紀90年代末,人們日益觀察到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滋生種種“城市病”,看似活力四射、動力澎湃的城市在應對不確定性風險時顯得尤為脆弱。因此,在城市規劃領域,人們試圖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組織系統、社會框架等調整來提升城市韌性。
而韌性城市較廣泛地為人們所認知則是在2002年,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ICLEI)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全球峰會上提出“韌性”概念。此后,國際性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跨國企業開始推動地區間的韌性城市建設,逐步形成實踐、交流、合作的網絡平臺。其中,聯合國減災戰略署、聯合國人居規劃署等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2年,聯合國減災戰略署提出了“讓城市更具韌性十大指標體系”,其中包括制定減輕災害風險預算、維護更新并向公眾公開城市抗災能力數據、維護應急基礎設施、評估校舍和醫療場所的安全性能、確保學校和社區開設減輕災害風險的教育培訓等指標。
2013年,洛克菲洛基金會啟動“全球100韌性城市”項目,除了巴黎、紐約等國際性大都會外,中國的黃石、德陽、海鹽、義烏四城也相繼入選。2015年,聯合國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減輕自然災害風險、實現社會災害韌性納入目標和指標體系。2016年,在第三屆聯合國住房與可持續城市發展大會上,“城市的生態與韌性”成為核心議題之一。
在相關理論推動下,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進行了韌性城市建設的探索,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提出了具體規劃方案并進行了實踐,取得了初步成效。
推動城市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韌性城市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尚處于摸索階段,其重點主要是應急救災領域,尤其是抗震方面。
1976年,河北唐山發生7.6級大地震,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遭受極大損失,在震后的恢復工作如供水、供電的應急搶修等,對我國城市應急救災體系提出了警示。此后,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樹地震,災后重建規劃工作中強調了基礎設施在抗震方面的韌性設計。
2018年,國家應急管理部成立,統籌管理全國應急救災工作,包括負責組織編制國家應急總體預案和規劃,指導各地區各部門應對突發事件工作,推動應急預案體系建設和預案演練;組織災害救助體系建設,指導安全生產類、自然災害類應急救援,承擔國家應對特別重大災害指揮部工作,等等。
在具體的政策措施方面,2017年6月中國地震局提出實施《國家地震科技創新工程》,包含“透明地殼、解剖地震、韌性城鄉、智慧服務”四大計劃。其中,“韌性城鄉”計劃旨在科學評估全國地震災害風險,研發并廣泛采用先進抗震技術,顯著提高城鄉可恢復能力,不斷促進我國地震安全發展。這是國家層面上首次明確提出韌性城市建設。
除了應急救災,住建領域近年來也對韌性城市建設提出要求。2016年11月,住建部印發《城鄉建設抗震防災“十三五”規劃》,特別提出探索抗震防災韌性城市建設,即開展抗震防災韌性城市建設體系研究,探索以提高承災體抗震能力為重點的韌性城市建設;研究建立韌性城市風險評估、生命線工程抗震安全保障、應急處置和恢復等技術體系。
2017年8月,住建部印發《住房城鄉建設科技創新“十三五”專項規劃》,提出根據不同城市規模、城市功能、自然地質條件、氣候風險,研究基于大數據分析的城市運行安全綜合風險識別、脆弱性評估技術,開展安全韌性城市構建與防災技術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后,韌性城市建設的重要性更為人們所認知認同。2020年4月,國務院印發《全國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計劃》,明確了2個專題實施方案、9個專項整治實施方案。其中,住建部牽頭制定了《城市建設安全專項整治三年行動實施方案》,該方案的一項重點任務就是加強對各地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指導,將城市安全韌性作為城市體檢評估的重要內容,將城市安全發展落實到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建立國家、省、市城市安全平臺體系,推動城市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另外,海綿城市、綜合管廊、老舊小區改造等行動,同樣也是提升城市韌性的措施;北京、成都、合肥等部分城市也進行韌性城市建設的探索。
多元參與強健城市機能
很顯然,我國傳統應急救災管理策略主要放在災后恢復、重建,而韌性城市則是注重城市通過規劃設計、制度調整等增強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相較于國際前沿理論體系,我國在韌性城市理論研究上尚處于追蹤、借鑒、引進階段,沒有形成符合我國城市特性的理論體系,在創新性、實用性上存在較大不足,這極大地制約了韌性城市在我國的落地實施。
如前所述,雖然韌性城市越來越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關注,但無論是政策措施、標準規范還是法律法規,都沒有形成清晰、明確且具有操作性的體系。同時,韌性城市建設需要多部門協同,目前條塊化的管理體系也阻礙了城市風險應對、應急管理的效能發揮。
從國外經驗來看,強韌的社會體系需要多元參與、多元共治,尤其是應對突發風險時,不僅需要政府層面強有力的行動,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等主體都要參與進來。而我國目前主要推行的是從上至下、層層推進的治理模式,其他社會主體缺乏參與度,雖然在整體上保障了強有力的行動力,但在社會組織末端缺乏靈活性,不僅降低了效能,也容易激化不必要的矛盾。同時,下情難以上達導致部分政策不接地氣、難以實施,而由于基層組織薄弱,一些好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容易荒腔走板。
在城市建設方面,重形象輕內涵、重硬件輕軟件的現象依然存在。我國超高層建筑建設規模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不少城市在雨季來臨時仍然面臨“城市看海”的窘境。雖然近年來國家不斷在海綿城市建設、地下綜合管廊上發力,但仍然有不少短板要補。
因此,推進我國韌性城市建設,必須加強理論創新和制度建設,建立健全長效機制;進一步優化管理流程,厘清權責關系,加強部門協同,促進資源共享,建立反應迅捷、高效靈活的風險應對體系。與此同時,應當充分發揮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作用,不斷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人民群眾防范風險的意識。另外,金融體系支撐也是韌性城市建設的重要一環。
經過此次疫情,我們應當看到,就風險防范而言,城市規模增長的收益有其上限,絕非規模越大越好。相較于不斷膨脹的超大型城市,城市圈、城市群或許是一個更優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