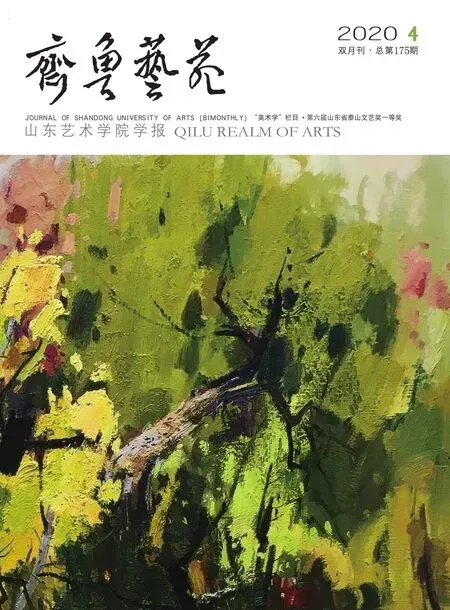圖文關系轉變中的“創作主體”身份探究
——以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為例
修太宇
(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6)
引言:從“總體藝術”談起
中國文人畫講求“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美學理念,“詩—書”和“畫—印”之間則構成一種圖文關系,它們共同形構了畫作的整體樣式。說到圖文關系,這離不開對“總體藝術”的回顧,只有把“圖文”放在“總體藝術”的語境中才能夠分析在歷史變遷過程中圖文關系張力的轉向,此點為本文的第一條行文脈絡。
“總體藝術”思想發端于德國浪漫主義美學,正如龍迪勇教授在探討德國浪漫主義美學“總體藝術”的觀念時所述:“在文體上,瓦肯羅德(Heinrich Wackenroder)已經創造出了一種真正的浪漫主義‘總體藝術’的典范形式。”“把各種體裁以及題材匯集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成為名副其實的綜合性的‘整體文學’。”[1](P128)由此可見,“總體藝術”思想首先發軔于文學領域,但展現“圖文關系”的具體實踐在德國并沒有得到廣泛傳播,德國主要起到先發性的理論指導作用。之后,德國歌劇作家瓦格納(Richard Wagner)在1849年的理論著作《藝術與變革》和《未來藝術》中首次對“總體藝術”進行了闡述:藝術創作已邁入“總體藝術品(Gesamtkunstwerk)”時代,只有將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歌曲、詩、寫作、編劇以及表演相結合,才能產生一種全面涵蓋人類感官系統的藝術經驗,也只有打破藝術領域間的界限,才有機會創作出最完整的藝術作品。能稱之為“整體藝術作品”的作品,應當是一個綜合的、全面的作品,在這種作品中,所有的藝術元素,再一次被結合在戲劇性的神話敘述中并展現給觀眾,其中每個元素都要屈從于整體。[2](P135)至此,我們從這些思想中可知“總體藝術”創作的基本條件——融合兩種或多種藝術形式或表現媒介的藝術作品可謂之“總體藝術”。文人畫的“總體藝術”特征由此可見一斑,這樣,我們便可以轉向對其圖文關系的探討。
龍迪勇教授在其論文《“總體藝術”與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圖文一體現象》中對圖文關系作了詳細論述:“當文字與圖像共同構成一個‘作品’的時候,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外乎以下三種:一、在文字性文本中插入圖像,這就是所謂文學作品的插圖……二、在圖像作品中添加文字,而所添加的文字往往成為圖像的組構成分……三、文字和圖像在整個作品中和諧共存……”[3](P125-126)當然,作者對三種圖文關系的劃分是立基于文學作品之上的,而且這三種關系表現在“單幅”的共時性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一種關系的獨立性。鑒于本文主要依托于作為視覺藝術作品的畫卷展開對圖文關系的探討,因此,把視覺藝術作品的圖文關系亦分為三種:即圖像主體;圖文一體;文字主體。然而,與前者對“單幅”的文學作品作共時性圖文關系探討不同的是,本文欲從歷時性的角度出發,探討視覺藝術作品中因“圖—文”所占畫面比例的差異而界定三種不同的圖文關系。
本文的第二條行文脈絡是:在圖文關系張力轉向的歷時性過程中生發出美國藝術社會學家貝克爾(Howard S. Becker)“藝術界(Art Worlds)”內社會性結構的差異化塑造,由此發現,圖文關系與“藝術界”之間存在一種“藝術社會敘事”的可能,這種“藝術社會敘事”跨越了藝術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延伸至藝術社會的結構。
貝克爾認為:“藝術不是一個特別有天賦的個體的作品。與之相反,藝術是一種集體活動的產物,是很多人一起行動的產物。這些人擁有不同的技能和才華,來自不同的背景,屬于不同的職業群體。盡管他們的訓練和背景有所不同,但他們卻找到一種合作方式,制作了他們那種藝術典型的最終成品:一幅畫、一場音樂或一出戲劇表演……”[4](中文版前言)其實,貝克爾的“藝術界”理論亦是建立在同一作品創作中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基礎之上,因此也體現出一種“單幅”藝術作品的共時性特征。作者“將一個藝術界看作一個在參與者之間建立起來的合作網絡”[5](P32),那么藝術創作就是“勞動分工”下的“制造和分配”活動。例如:創作一幅繪畫成品,在不同的環節需要不同的人員參與——制造繪畫顏料、畫布和畫筆的工人,創作繪畫作品的畫家,或許還包括畫家的助手——最終一幅完整的繪畫作品在這些處于不同“創作”過程中的人員的共同協作下才得以完成。
“藝術界”理論主張的最終藝術成品的創作主體不僅包括藝術家,還包括藝術媒介的制造者和服務者,這種“創作過程”涵蓋了——直接的和間接的——任何與此相關的人員,同時,藝術作品的成型是基于藝術家的“最后一筆”。那么,這個“創作過程”是否可以無限延伸呢?筆者與其觀點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本文的“藝術界”拋卻媒介材料的制造者,單專注于藝術家本人的身份,在歷時性過程中,視覺藝術作品上的藝術家“最后一筆”有可能被某位“藝術家”附上“新的最后一筆”,當然這種情形還有可能繼續發生轉變。由此,便可以對圖文關系轉變過程中藝術作品的“創作主體”的社會性關系進行探討。
基于對以上兩條行文脈絡的梳理,圖文關系中蘊含有社會關系的“藝術社會敘事”圖景清晰可見。如引言所提到的中國文人畫中“詩—書”與“畫—印”之間的圖文關系那樣,本文以此為研究對象,采取社會學的研究路徑,從歷時性的角度,以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后簡稱《子明卷》)(1)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卷構圖景物與《無用師卷》大致相同,起首保留了前段《剩山圖》,但卷末缺主山一段。因題款云:“子明隱君將歸錢塘,需畫山居景,此圖贈別,大癡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故簡稱此畫作為《子明卷》。經現代學者研究,比較兩卷筆墨造詣,確認此卷實系仿本。本文將拋開此卷的美學價值、歷史價值和真偽,主要采取社會學方法借此畫卷所展示的圖文關系來說明本文的研究問題:藝術社會敘事的圖景。(圖1)為例,對文人畫中“圖—文”所占畫卷畫面的比例差異化轉變的過程中所蘊含的社會關系轉變——即畫卷中圖文關系的轉變和“藝術界”中“創作主體”的身份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以解析這種藝術與社會結合的歷時性藝術社會敘事的藝術現象。

圖1 《富春山居圖》(子明卷)
一、圖像主體:作為原創的藝術家
與西方繪畫相比,中國文人畫存在一個有趣的藝術現象:題跋、落款。文人畫最初就追求一種“詩、書、畫、印”相結合的審美形式,畫家對圖像和文字進行空間布局和結構以傳達畫中所蘊含的情感和意境,它體現了藝術家的原創訴求和主體性特征。
在探究圖像主體與原創的關系之前,有必要對觀看圖文的“時空觀”先行分析。繪畫作為一種空間藝術,詩作為一種時間藝術,萊辛(Ephraim Lessing)對其有著精辟的論斷:“在空間中并列的符號就只宜于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空間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時間中先后承續的符號也就只宜于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時間中先后承續的事物。”[6](P82)因其創造媒介和材料的區別,繪畫和詩歌之間存在著一種“正義和友好”的界限。這里所論畫與詩的差異還在創作層面,主要探討藝術創作所用之符號或摹仿媒介與所描繪之物或題材之間的一種方便或適當的關系。從這點來說,所探討的仍是畫與詩作為藝術類別時相互獨立的藝術特征。
因此,從觀看的角度來說,很難對一幅成型的繪畫作品的時間性進行邏輯的把握,因為這種訴諸于“眼”的視覺藝術的整體性展示的是一種空間性的規范;值得一提的是,文字的時間性效果反而因處于繪畫語境中而被削弱了,對其可作空間性的觀照。本文所談及之“觀看”既不在圖文內容的時空特性,也不在創作過程中對時空的把握,而是聚焦于在跨越不同歷史時期的過程中,一段“新文字”附于畫卷畫面上所顯現的圖文關系之效果。這樣一來,當我們觀看《子明卷》的整體圖文時,就很難把握三種圖文關系轉變的過程性,因為畫面所呈現的是最終藝術成品的視覺效果。雖然這種局限性會阻礙對三種圖文關系的理解,但可以通過題跋時間和“文字空間化”使得文字與圖像之間形成歷史性的形式效果,這里,我們不是把文字作為文學去解讀,而是作為由一定字數組成的整體空間結構去觀照。其實,“一首詩既不是直義的時間形式,也不是比喻意義上的空間形式,而是一個時空構造”[7](P129),而一幅繪畫作品正是通過藝術處理手法,對詩、書、畫、印等不同媒介進行時空構造,最終展現出繪畫的整體效果。
“圖像主體”即指在畫卷中,圖像占據著更多的畫面,其中的題跋和落款僅僅作為圖像的補充,可稱為題詩的畫,這是創作主體對形式美的構造,以及對整體協調感的追求。當然,“畫卷”的本質就是一幅畫,而不是一首詩。這就決定了“詩—書”和“畫—印”共同形塑了繪畫的時空結構,聯結成為一幅畫的整體。這個時候,文字并不會影響觀賞圖像的效果,觀者在欣賞繪畫時,往往驚嘆于圖像創作的精湛技巧和視覺效果,文字僅是作圖像的輔助信息以更好欣賞圖像。《子明卷》在被乾隆帝題字之前是一幅未經任何信息介入的原創作品,它保持著一種原境;黃公望也處于原創藝術家的位置,在整個《子明卷》的時空結構中塑造著自我語境,這是對黃公望身份認同最直接的視覺證據,同時也作為黃公望的象征符號,是“作者性文本”的最佳呈現。《子明卷》和《無用師卷》局部(2)真跡《無用師卷》被乾隆定為贗品后束之高閣,而贗品《子明卷》卻為乾隆倍加珍愛,在畫卷之上寫滿了題跋。因兩卷構圖大致相同,本文以此作比,探討題字之前的“原創”圖景。(圖2)所展現出的圖文景觀非常鮮明地傳達了后者的原創特性,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其一為畫卷的獨立性;其二為黃公望的獨立性。

圖2 上圖《子明卷》(局部),下圖《無用師卷》(局部)
作為“圖像主體”的《子明卷》和作為“原創主體”的黃公望之間保持著一種對等的關系。黃公望即為文人畫家,他的身份決定了他的繪畫職責,而不是去作詩寫書法;繪畫的本質即為圖像的描繪,而不是用文字去描寫物象。以此可知,此時《子明卷》的最終成品是由“同一主體”在“同一時間”完成的,這就保證了黃公望的獨立身份。依照貝克爾的“藝術界”,與黃公望有所聯系的只有造紙、制筆的工匠和研墨的書童等,而創作主體即為畫家本人,同時,黃公望居于畫卷創作的核心位置。“圖像主體”的原創作品塑造了一種最為本真的原境,“藝術界”的復雜信息并沒有阻礙畫卷獨立性的展現,畫家和作品之間自始保持著一種最為純粹的、直接的關系。
綜括而言,《子明卷》最初的圖文關系展現出一種原創性質和社會關系的單純性和獨立性,藝術社會敘事的脈絡保持著一種單線、直接的構結,并通過“圖像主體”的畫卷視覺效果投射出來。
二、圖文一體:歷時性過程中的“創作主體”身份
《子明卷》作為繪畫藝術精品流傳至清乾隆帝手中,其畫卷魅力為乾隆倍加珍愛,題跋無數,猶如繪畫中的藝術日記。這樣一個藝術事件——題跋——成為繪畫中圖文關系轉變的轉折點:由“圖像主體”轉向“圖文一體”。此外,乾隆帝的介入亦引起了“藝術界”的變化,并引發出新的思考:《子明卷》的“創作主體”身份問題!
乾隆帝于《子明卷》(圖1)上題跋無數,據統計,從乾隆十年到嘉慶四年,畫卷上共有55處乾隆的題跋,其中畫卷之中有53處,另外兩則題跋寫在了畫卷的前后隔水之上,開卷第一則題跋也是乾隆最后一次在此畫卷作跋:“以后展玩亦不復題識焉。”[8]乾隆題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從原創的角度來看,此卷的美學價值很大程度上受到題字的破壞;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里卻呈現出一段乾隆與《子明卷》的藝術故事。
由于視覺觀照中畫卷只能展現最終藝術成品整體效果的局限性,這里,我們僅能依靠題跋時間和“文字空間化”來探討繪畫中圖文關系的“圖文一體”特征,但這種特征并非虛構,而是在乾隆題字的50多年的歷時性過程中真實存在過。“圖文一體”即指圖像和文字處在一種和諧整體的關系中,它們之間不僅具有一種內容相關性,而且展現出畫面空間的和諧感。研究發現,乾隆題跋的文字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有關《子明卷》的來歷敘述和真偽考證;二是就畫卷本身的藝術評價;三是乾隆攜畫出巡,引發聯想及印證自然與藝術相合的感性記錄。[9]以第三類題跋居多。從內容上來說,與圖像相關的題跋為第二類,其數量并不很多,但它們在傳達圖文信息方面有很強的相關性和一致性。然而,本文主要探討“圖—文”所占畫面空間比例的關系,也就是“圖文一體”關系的聯結需達到“圖-文”空間比例的和諧才能得以構建,這可被描述為巫鴻所謂的“空間文本”,同時,這些圖形符號和文字符號被安置在二維的平面空間之上,更加強了“圖—文”的視覺效果。
如《子明卷》局部(圖3)展示的那樣,圖像和文字所占的畫面比例處于相合氛圍之中,從觀者的角度來看,圖像和文字符號組成類似于兩個矩形的幾何形體,它們處在一種相伴而不相擾以及和諧整體的布局之中,這或許是乾隆在題跋過程中的某一階段而形成的“圖文一體”關系。從這一歷程可以發現:作為原創主體的黃公望是一位描繪者,他創造了畫卷本體,并形成《子明卷》的主要圖像和符號特征;乾隆帝的身份介入致使畫卷的“社會性”發生變化,由“圖像主體”轉為文字介入的“圖文一體”,這不僅改變了圖文關系,而且還引出了“創作主體”的身份問題。貝克爾認為:藝術家是藝術創作“核心活動”的人,藝術家與他人之間“存在一種合作關系”。[10](P23)但是這種“合作關系”中仍保留著藝術家的獨立性,是“單幅”藝術作品的合作關系,有了藝術家的介入,作品才得以完成。那么,乾隆在“藝術界”中的身份如何界定呢?乾隆和黃公望之間相隔數百年,從創作角度講,他們都是藝術家,前者是書法家,后者是畫家。然而針對《子明卷》的題跋,乾隆的書法家身份卻成了“破壞者”,這里表明了兩者最直接而又最曲折的關系:“介入與被介入”的關系。

圖3 《子明卷》(局部)
雖然圖像和文字在時間上發生錯位,但在空間上仍然并置在一起。黃公望構建了自己的繪畫語境,因某種機緣巧合,乾隆把文字書寫在了《子明卷》上。此外,《子明卷》作為已被承認的最終藝術成品,那么,乾隆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介入者”,而畫卷則成為“被介入者”,也就是說,畫卷語境被“乾隆化”了,增添了乾隆的主體意識。或者說,如若拋開畫卷的歷史不談,僅就呈現于眼前的畫面來說,可以明確的是:黃公望和乾隆屬于“合作關系”,他們共同形構了畫卷的整體,僅僅是“創作過程”較長罷了。就如同現在很受關注的“總體藝術”,同一藝術作品,參與的“創作主體”可以由多人組成,這就賦予了作品的組織性特征,其中必定包含一位核心組織者(創作主體)。然而,黃公望無法與乾隆“隔空對話”,乾隆也并未獲得被組織者的身份,因此,乾隆具有主動介入性,畫卷的“總體藝術”特征是由他們共同建構的,同時,賦予了《子明卷》以“社會性文本”特征。
綜括而言,乾隆在不同階段題跋時表現出不同的“習俗”符號,然而畫卷圖像的“自然”符號則不變。[11](P92)若除去“題跋”符號,依然是黃公望語境,這也是《子明卷》作為繪畫本質而存在的基礎;因為乾隆語境的介入,文字符號賦予繪畫以社會性,“圖文一體”便由此在歷時性過程中被初步構造出來。由此,從“藝術界”的角度看,畫卷的“創作主體”亦發生身份溝通,黃公望和乾隆共同形構了《子明卷》的畫卷圖景。
三、文字主體:藝術作品的“創作主體”變異
“圖文一體”是乾隆初次介入畫卷時所賦予《子明卷》以“圖文關系”的視覺形態特征,也是黃公望與乾隆建立“對話”關系的轉折點。然而,這種“對話”關系不斷持續發展,突出表現在題跋數量的不斷增加。此時,畫卷儼然成為帶有山水印花的筆記本,而乾隆題跋則成為記錄各種巡游、感慨、觀點的感性日記,而文字內容與所繪圖像之間的聯系則相差甚遠。畫卷(圖4)中圖像和文字所占畫面的比例發生顛倒,“文字主體”的圖文關系展現出來,拋開文字所描寫的內容不說,圖像已然成為文字的補充材料,猶如為了裝飾凌亂的便利貼,為其繪飾了山水背景以作陪襯。
至此,對《子明卷》圖文關系的探討就面臨一個重要的話題:《子明卷》還能被稱作為畫卷嗎?能不能稱為書卷呢?是否可以把這些文字視為書法展示呢?龍迪勇教授在論述“圖文關系”時稱:“文本中插入圖像……在文字和圖像共同擁有的作品中,圖像都是強行插入到文字性文本之中的,文字性文本實際上可以脫離圖像而存在。”[12](P126)也就是說,文字是主導而圖像是裝飾。依前所述,“圖—文”之間在內容上的聯系不大,完全可以剝離出圖像單獨欣賞文字之美。然而,在畫卷中,這是行不通的。從貝克爾的“藝術界”來看,《子明卷》的“創作主體”發生變異,但是,其作為繪畫的本質并沒有改變,因為,從始至終,乾隆都僅僅是一位介入者,“先入為主”在這里或許可以得到更好的體現:黃公望和乾隆面對著相同的媒介材料——畫紙,前者繪圖,后者書寫。但因為時代差異,畫紙的主人便是第一位使用者——黃公望,他率先把自己的繪畫意志傳達出來并物化圖像于畫紙之上,同時構建了自己的獨立繪畫語境;到乾隆時期,畫紙已不再具有最初的紙張特征,它不僅包含了視覺圖像,而且還被賦予了原創主體意志,那么,乾隆的書寫也不同于專業書法家式的書法創作,他強行介入了黃公望的繪畫語境,不僅破壞了原作的美學效果,而且其所書寫文字與原圖像之間產生一種圖文對抗,這種咄咄逼人的題跋的侵入,使得文字占據畫面的多數空間,逆反了圖像的視覺焦點。

圖4 《子明卷》(局部)
由此可見,乾隆沒有資格要求把黃公望的圖像剝離開去,同時,《子明卷》的歷史也無法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在筆者看來重要原因是:圖像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態,且在文人畫的語境中,“書—畫”本身就是相結合的關系,而不能相互融合為第三種藝術,而且“圖—文”之間的區別比較明晰,因此,《子明卷》的三種圖文關系才能夠通過視覺形態展現出來;同時,歷史觀警戒我們,畫卷的繪畫本質不可顛覆,無論文字占據畫面空間比例有多大,畫卷依然是繪畫作品,而不是書法作品。有一個反例可以說明:杜尚(Marcel Duchamp)使用鉛筆在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名畫《蒙娜麗莎》的印刷品上描畫出山羊胡子并命名為《L.H.O.O.Q》(“她的屁股熱烘烘”),他是在原創圖像的復制品上加入了自己的繪畫意志,但“山羊胡子”與原圖像之間是一種“圖—圖”關系,因此,兩者能夠較好地融合在一起,而成為新的藝術作品,而“杜尚”符號也成為此作品的象征。當然,“圖—文”和“圖—圖”兩種關系還可以作進一步探討。
再反觀《子明卷》,圖文關系僅僅是一種關系,并沒有上升到文字吞并圖像的結果。那么,在“文字主體”的關系下,“創作主體”有沒有被顛覆呢?從前文論述來看,無論從歷史觀出發,還是從“圖—文”關系出發,畫卷的繪畫本質沒有改變,因此“創作主體”也未改變。但是,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畫卷所最終呈現的整體視覺效果并非僅由黃公望一人為之,跨越空間結構來看畫卷,難道不能把乾隆作為主要的書法創作者嗎?而黃公望僅僅是在幾百年前為其書寫紙張作了裝飾性描繪而已。或許,在歷史的某一時期,這種“創作主體”的身份真的會發生變異吧!
綜括而言,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文字主體”的創造者乾隆已然成為《子明卷》的畫卷畫面空間的主體結構,使得“創作主體”的身份發生變異,“乾隆”符號亦成為畫卷的焦點,并形構了畫卷的“文字語境”。
結語
文人畫本身所具有的圖文關系構成了一種“總體藝術”,“詩、書、畫、印”共同形塑了繪畫的空間結構。“題跋”作為文人畫中存在的獨特藝術現象,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詩—書”與“畫—印”的圖文關系發生著轉變:“圖像主體”→“圖文一體”→“文字主體”。在這種圖文關系轉變的歷時性過程中,不可忽視對“創作主體”身份問題的討論,這不僅關系到藝術創造,還關系到社會性的結構。古典哲學比較關注對物象本質的探求,延伸至繪畫也是如此,繪畫的本質成為藝術研究的主題;歷史進入現代社會階段,西方圖像學的發展和傳播,以及藝術社會學的興起,對圖像與文本關系的研究受到學術各界的關注,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成為一條可行的藝術研究路徑,循著這條脈絡,中國文人畫的藝術社會敘事圖景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