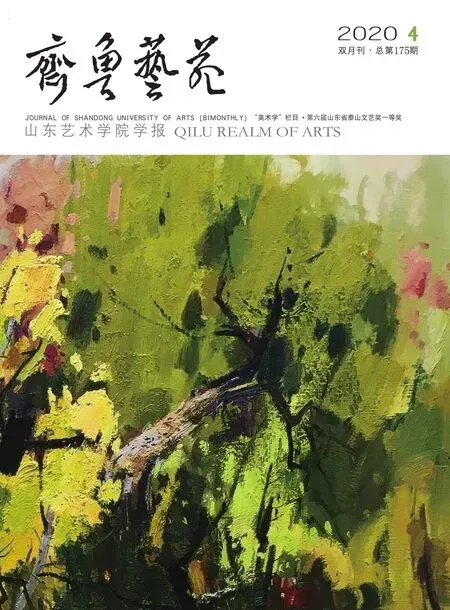藝術是一場規則的游戲
——伽達默爾游戲理論引發的思考
張天貽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游戲是動物學習如何在群體中生存的第一步,是人在基本物質需求滿足后,追求精神滿足的娛樂方式,也是人在某種特定時空范圍內遵守制定好的某種特定規則的社會行為。同時,游戲與人可以說是密不可分,人類成長中的每一段都有游戲的陪伴。游戲與藝術的關系可以追溯到柏拉圖時期,那時柏拉圖已經發覺游戲與藝術具有相似性。近代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游戲與美的特性很相似,認為游戲具有“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同時認為言語的藝術類似游戲。席勒認為“人與美應該只進行游戲,人應該只與美進行游戲。”[1](P220)人成為完全形態的人才能進行游戲,并且認為,人對愉快的、好的、完美的東西都會采取嚴肅態度,但對美的態度卻是游戲的態度。斯賓塞借鑒席勒理論發展出“剩余精力說”,將游戲對藝術的影響提高到一個較高的層面上。伽達默爾延續并發展了游戲理論,將節日、象征與游戲并列,提出游戲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
一、伽達默爾的游戲觀
伽達默爾是德國哲學家,同時也是闡釋學創立者之一。在其著作《真理與方法》中, 用了很大篇幅討論游戲,將游戲、節日、象征列為藝術作品的存在方式。事實上,伽達默爾受康德的影響,在康德的“藝術的本質即游戲”的基礎上將藝術與游戲列于同一層面上進行研究。在論著中,他認為,游戲與藝術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游戲的方式就是藝術存在的方式。他沒有從藝術的本質展開論及到游戲的本質,而是將游戲的事實進行分析解構,通過游戲看藝術。在他看來,游戲比藝術要提前發生,是“藝術的藍本”,同時游戲的結構符合藝術的結構,且本質特征相同。游戲能夠轉化為藝術,這種轉化叫“向構成物的轉化”。轉化后,游戲作為創造物具備了理想性,但游戲的本質沒有變,表現的是永遠真實的東西。其實這種轉化可以理解為用游戲與藝術的雙重視角去解釋藝術,游戲具備可轉化的條件就意味著游戲具備了藝術創造的某些特質,也間接證明了藝術起源論中游戲起源說的合理性。
1.游戲是種具有自己精神的往復運動
從游戲的本質內涵上看,游戲具有往復性。游戲是一種可以不斷開始,也可以重復結束的自身循環往返的運動。伽達默爾認為,閱讀、觀賞、玩游戲等活動發生時,人們就從日常生活的思想、行為方式中脫離。游戲空間是全新的領域,玩家參與其中,進入到一個新的游戲空間,為游戲而取消自身。這時,玩家積極地參與游戲,投入其中,達到所謂“忘我”的境界。這種境界很容易在游戲中達到,因為游戲的開啟到結束是依靠玩家的興趣。如果興趣消散,玩家們意興闌珊,結束一場游戲也是很容易的。在網絡游戲中很容易出現不喜歡某個隊友,或者游戲技能觸發錯誤而終止,繼而重啟一場新游戲的情況。藝術亦是同理,藝術家可以不斷嘗試創作新的作品,就像開始一場新的游戲那樣簡單。不斷重復、無限循環的運動是藝術與游戲共同的本質特征,這種具有生命本質特征的自由往復運動是藝術與游戲在結構上相同的原因之一。
其次,游戲具有獨立性。游戲具有自己的精神,有其獨立的意義。游戲在玩家心中有優先性,就是剛剛提及的,進入一個新的游戲后,玩家把自身擱置,而將游戲放在第一位上,自身的欲求變得沒有游戲重要了。與游戲相同的是,藝術作品的主體是藝術作品,創作者只是藝術作品的參與者。這或多或少抹殺了參與者的重要性,其理論直接影響了后來的結構主義。“零度寫作”“自動寫作”“作者之死”等口號的提出與伽達默爾的游戲理論也有很大的關系。
再次,游戲具有嚴肅性。游戲中,如果誰不嚴肅遵守游戲規則,誰就是游戲的破壞者。當然,這也是游戲的精神之一。游戲與藝術一樣散發著輕松的氣息,但需要參與者嚴肅地遵照規則。游戲的輕松性在參與者的主觀意圖中感受到的是對某種束縛的解脫,這種輕松性不是指操作中真的缺乏緊張性,相反游戲中的緊張感讓游戲者欲罷不能。散發嚴肅而輕松氣息的規則讓游戲者專注于自身,本能地想去重復這種行為,并擺脫現實中造成他感到壓力與焦慮的問題。所以游戲的吸引力在于遵照規則的行為使人擁有輕松感,讓參與者自愿參與進來并本能地重復這種行為,來暫時忘卻導致緊張的事物。
2.游戲是被表現出來的,并在觀賞者那里得到了圓滿
從游戲的外部呈現方式看,游戲具有被表現性。人游戲的意義在于自我表現,不存在任何單純自為的游戲。論述游戲時,伽達默爾認為,游戲是無法一個人進行的,與別人同戲是游戲的進行方式,場所、他者、觀眾是游戲必不可少的要素。游戲的特殊性在于,只能由他者與觀眾來組成自身,游戲沒有參與者便無法表現其自身,換句話說,游戲是被參與者表現出來的。雖然游戲無法自我表現,但對參與者們來說游戲具備優先性與權威性。藝術亦是同理,創作者展現自身來創作藝術作品,藝術便通過藝術作品展現自身,欣賞者通過欣賞藝術品獲得某些感受,再反饋到創作者和其他欣賞者那里,這種循環讓藝術實現了自身的表達。所以說,游戲的外部呈現特征亦具備欣賞性。藝術作品無法自我表現的特性,致使觀眾的欣賞成為藝術作品圓滿的標志。一部舞劇需要有觀眾的欣賞,欣賞者成全了作品的自我表現,讓舞劇的展現過程凝結為藝術。觀眾與藝術作品的關系,不僅是單向性地觀賞關系,還具有雙向性地交流關系。如果將欣賞者與藝術對話看作是解釋藝術作品的過程,那么藝術品的意義就不僅僅是藝術家所意想的意義,觀眾與藝術作品的交流是對作品本身意義的更深層次的挖掘。值得注意的是,欣賞者的審美經驗不同,會導致所看到的角度、問題、內容乃至真理都不同,“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問題在闡釋學中是個普遍的現象。這種理論指導下,我們理解藝術作品時,容易忽視審美通感的問題。而且,過于重視欣賞者的藝術行為是值得商榷的,把觀眾的賞析與解釋視為藝術作品圓滿的行為,容易忽視創作者或者說是游戲者的主觀行為的創造性。其實對作品樣態擁有大部分決定權的人是創作者,更多情況下藝術作品所表現的內容是與創作者意圖與潛意識有關。雖然來自欣賞者的反饋是極其重要的,但藝術作品的圓滿來自于欣賞者的前提是擁有一件具有藝術價值與闡釋價值的藝術品。如果一場游戲的前期鋪墊并沒有那么全面,參與者沒有那么嚴肅,眾人的配合沒有形成默契,這樣的藝術作品即使擁有文化積淀深厚的欣賞者去欣賞評論,也難以擁有真正的藝術價值。
總而言之,伽達默爾的游戲理論其實就是他的藝術觀。在他看來,以游戲方式存在的藝術作為主體,與把游戲放置于第一位的參與者一起進行的融合活動,這項活動中的參與者自愿且自發地參與并不斷重復類似的活動,并且游戲是藝術的開始。
二、藝術為何是規則的游戲
藝術其實就是一場規則的游戲。首先,藝術的游戲性在創作中十分常見。藝術的存在方式是游戲,相比較伽達默爾認為游戲是嚴肅而守規則的“藝術的藍本”,藝術對于規則上的游戲態度比游戲還要像游戲。很多藝術家、作家創作時態度沒有像遵守游戲規則一樣嚴肅,玩樂中碰撞出藝術是他們更傾向的創作方式。諾獎獲得者米蘭·昆德拉認為小說是游戲性的。昆德拉不僅有意從態度上指向游戲,比如在小說中加入有趣的玩笑等,從寫作技巧上,他也有意識地在小說的游戲性上下功夫。昆德拉在《不朽》、《慢》等小說中,以作者的身份與口吻介入小說,參與情節并與書中的人物直接對話,解構了小說的真實性。他的創作過程中具備隨意性、娛樂性與非功利性,這是作者與作品的游戲,也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游戲。昆德拉將藝術看成了一場游戲,以對待游戲的方式去對待藝術,以游戲的態度與口吻去質疑本身極其嚴肅的藝術規則,這是對藝術規則頂禮膜拜人的輕慢,也是對“藝術是游戲”觀念的踐行。
其次,藝術在規則的制定與遵守方面嚴肅認真。游戲看似自由自在,實際上擁有嚴肅的規則。游戲規則的制訂是權力體現,游戲者認為自己掌握了規則制訂或改變的權力。人自由自在的生存是每個人的本能追求,馬克思認為人“自由自覺活動”的特性是人的主體性活動的特性。就是說,如果權力的實施過程中忽略了這種“自由自覺活動”,那么人的主體性就會喪失,也許人會變成異化的狀態,成為一部機器。游戲就為人“自由自覺活動”提供了場所,也同時給人營造一種假象:游戲中的權力是由自己掌握的。玩家可以成為規則的制定者或更改者,抑或是成為最為適應規則的人。這樣一來,所謂游戲的“無目的性”在參與游戲的玩家身上就沒有那么純粹了。所以說游戲僅僅是無功利性目的,滿足的不是現實生活中的欲求。精神上的權力欲望是游戲。更多時候,看似在游戲中所向披靡的玩家,在現實世界中大多是適應不了規則的人。當自己對現實世界的規則甚至潛規則不滿時,當自己適應不了規則或者達不到標準時,當自己面對規則有深深的無力感,覺得無法改變甚至違背自身原則時,游戲滿足了發泄不滿情緒與逃避現實的愿望。而這也就是游戲的魅力,它讓人從現實中抽離,忘記自己與現實間的不適應,并且吸引游戲參與者自覺自愿地加入。游戲參與者一次又一次地體會運籌帷幄、主宰一切的成就感,深陷其中無法自拔。換個角度想想,游戲是否主宰了參與者。“游戲的魅力,游戲所表現的迷惑力,正在于游戲超越游戲者而成為主宰。”[2](P137)伽達默爾認為游戲具有極大的魅力,是這種魅力超越游戲主宰了游戲者。
再次,藝術規則可以打破并再次建立。藝術的創作者認為自己在作品的創作上掌控的是一種制訂規則的權力,游戲的參與者同樣這么認為。這點在兒童的游戲中十分明顯,游戲是可以隨時將自己制訂的規則改變,同樣,在藝術創作中規則也是如此。藝術作品不斷創新、藝術間跨門類融合、藝術與非藝術壁壘崩塌無一不在說明,藝術規則是可以像游戲規則一樣更改變化。在藝術創作中,藝術自身規則的更改由參與者協助完成。藝術規則的更改迎來的也許是藝術作品更容易受到歡迎,也是為進一步增強藝術作品傳達意義的層次感,豐富形式的多樣性而做出的改變。藝術的魅力在于不斷地吸引藝術家自覺自愿地參與,而藝術家作為作品的主宰,將自身消解于游戲,全情投入,忘卻自身,使藝術作為主體的被表現性增強。這是藝術的自我進化,藝術也在為自己有更強的表現力尋找出路。
最后,對待藝術“佯信”的態度,亦是藝術創作、欣賞的規則。游戲的參與者對于游戲規則的態度是認可的,因為游戲的參與者對游戲的態度是輕松的、開心的、自愿的,游戲無法逼迫一個人進入游戲。在欣賞者而言,了解游戲規則并以上帝視角觀察游戲過程,所有驚心動魄的過程他都看到了,但沒有親身參與。欣賞者沒有參與游戲,但仍然感受到了游戲參與者的游戲體驗,視野更加廣闊,感受也會更加全面,也就是說游戲參與者僅僅表現了一個游戲,欣賞者才能看清游戲的全貌,體會參與者遵守、打破或超越游戲規則時帶來的愉悅與刺激的感覺,完成了游戲的全過程。這也就是為什么說欣賞者適合充當評論者的角色,評判參與者和游戲的表現、效果,對規則的遵守等。欣賞者與參與者對待游戲不僅認可游戲規則,自覺自愿遵守規則,還愿意假裝相信這一切是確定發生,來保證游戲的正常運轉。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中認為游戲與藝術的共同點之一是對于臆造世界的態度都是“佯信”[3],并從兒童游戲的角度去證實他的觀點。他認為對待游戲與藝術應有的態度是一種假裝相信那是真的態度。觀眾欣賞米歇埃爾·莫爾格納的《地獄》,只會假裝相信,地獄的景物是畫中描繪的那樣,不會真的去問莫爾格納地獄的真偽。所以,對待游戲與對待藝術的態度只能是佯信,否則,便破壞了創作者的興致。跟藝術作品“較真”也違反了藝術的“講述美而不真實的故事”的原則。
總之,藝術的游戲性在創作過程中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藝術在規則的制定與遵守上的嚴肅性和超越規則的隨意性本身就像是一種游戲。在游戲中制定、打破、超越規則的過程也是藝術創作歷經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藝術就相當是一場規則的游戲。
三、挑戰既有游戲規則是藝術發展的走向
如今,藝術的創作走向在與后現代思潮的沖擊下,碰撞出不一樣的道路,藝術的游戲規則也在不斷被打破、重建。自從杜尚的《噴泉》在紐約獨立美術家協會美展廳展出之時,挑戰藝術的規則受到了藝術界的追捧。作為藝術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杜尚將生活中常見到的小便池,簽上了名字,送到了藝術品展覽會上。雖然未被展出,但是這個行為引起了學者們和藝術家們的熱烈討論。杜尚在藝術品展會上展現了對藝術的輕蔑與對創作的游戲態度,很顯然是在挑戰藝術規則,開啟了藝術創作風格轉向的浪潮。在《噴泉》這個藝術事件中,看似是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被對待藝術近乎于游戲的態度打破了,其實是杜尚用赤裸裸的現實生活用具來擊碎藝術品的光暈,借此逼迫人們正視藝術的規則是否必要合理。
19世紀之時,黑格爾提出“藝術終結”的觀點,他認為喜劇將終結一般的藝術形式,藝術將沿著哲學的道路發展,一般的藝術形式將終結。可縱觀藝術史,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下,21世紀的藝術沒有終結,而是被當代藝術家改頭換面,進入了一種泛藝術的游戲狀態。景區實景演出、沉浸式體驗話劇等藝術類型的出現,都在昭示著泛藝術時代的來臨。中國逐漸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藝術作品中日常生活審美化、嚴肅藝術游戲化等現象越來越普遍,消費與休閑的商品逐漸趨向藝術作品,而藝術作品逐漸被商業化、游戲化。此時的藝術不再具備深刻而嚴肅的模式,而是逐漸打破自身的規則,融入大眾文化。此時的藝術早已遠離存于高雅殿堂中的藝術光暈,超越自身原本的規則形式,結合眾多東西方藝術思潮,發展成為與生活越來越接近的、獨立于人類其他形式社會活動的價值領域。如今的藝術創作對前人制定的規則充滿質疑與輕蔑,不守規則成為藝術家們競相展現個性的武器。這些不守規則的藝術家們將藝術從神壇上拉下來,將原本與生活有距離感的藝術,無限貼近生活,從而消解了藝術與生活的對抗性。沃霍爾把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可樂瓶、罐頭、美鈔以及瑪麗蓮·夢露頭像通過重新組合排列和印刷,進行藝術創作。他將肥皂包裝盒印刷組合,創作出藝術品《布里洛盒子》。以丹托為代表的藝術批評家們認為沃霍爾與杜桑如游戲般荒誕的創作方式基本一致。這些藝術家不約而同地拋棄了原本嚴肅的藝術規則,用夸張而無意義的拼湊方式取代了含有深刻意義的藝術形式,他們企圖挑戰甚至推翻原有的藝術規則的行為引起了觀眾與評論家熱烈的討論。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類藝術品,并企圖給予其深刻的含義。不得不說,挑戰既有規則已經是現今藝術發展的走向。但值得注意的是,挑戰與反叛既有規則就會引起另一種規則的興起。早在20世紀初,現代舞的興起就是對古典芭蕾僵化體系的反叛。現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鄧肯之所以建立了自由抒發情感的舞蹈流派,是因為其經受不了古典芭蕾的基礎訓練,意圖擺脫芭蕾舞程式化的束縛,表現自己想表達的東西,現代舞應運而生。可經過多年的發展,所謂的反叛與自由形成了另一套全面完整的體系。以瑪莎·格雷姆提出的“收縮——伸展”為主要訓練手段的訓練體系成為練習現代舞的舞者必須接受的基礎訓練。看到現代舞基訓,就一定會看見舞者在地面上滾來滾去,如今現代舞的模式化訓練與當年芭蕾訓練僵化的把桿擦地訓練驚人的相似。現代舞追尋自由,擺脫芭蕾體系的同時,自身也設定了規則,這種規則也在發展中,逐漸固化為一套完整而僵化的體系,再次走上芭蕾發展的道路。所以說,對藝術現有游戲規則的反叛就意味著另一套新規則的建立。現在的藝術發展走向就像一場重新洗牌的游戲,不僅藝術品以游戲的態度創作,還打算推翻原有嚴肅自律的規則,將夸張與荒誕的藝術風格成為新的規則。這種規則下誕生了許多被現在年輕人追捧的作品。例如電影《大話西游》打破電影嚴肅敘事的手段,采用無厘頭式創作手法,用看似荒誕夸張的動作與情節,闡明了一些真實而深刻的道理。其無厘頭的語言風格與悲劇內核使其成為中國后現代的標本,雖然讓當時的票房遭遇“滑鐵盧”,但如今依舊成為人們心中的經典之作。電影《頭號玩家》以游戲作為藝術的表現對象,以電影的方式去展現了一場游戲。其中影片體現出的反宏大敘事、碎片化、無邏輯的藝術特征,以游戲化的方式挑戰傳統影片邏輯,也體現出當代藝術的新規則。
藝術作為一場可以不斷重復的游戲,從它現在的種種表現——不斷靠近生活、大眾文化,不斷延展自身范圍并將自身的意義消解來看,藝術的規則正在被改寫。現代藝術的發展正在挑戰原有藝術規律,重建審美標準,消解意義與規則,走向一個新的藝術時代。
總結
伽達默爾談及游戲與藝術經驗的關系時,認為游戲與藝術可以互相解釋,只要認真分析游戲的具體特征,就能將藝術的經驗和藝術的真理放置于網狀結構上,進行系統而深入的剖析。現在,有不少藝術工作者對藝術的游戲化、無意義化、商業化有著濃濃的失望之情。其實,大可不必以悲觀的態度來看這些現象。時代總有其更迭的時限,現今世界不管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都處于一個大調整時期,我們清楚的知道隨著世界不斷發展,以后的藝術一定不會與現在的情況相同,某些東西會被更迭掉,就如昆曲作為中華文明的文化瑰寶,已經不能作為大眾普遍接受的觀賞和消費的藝術形式一樣。藝術發展隨著20 世紀商品經濟的全球化發展而逐漸轉向。現在的人們正視被壓抑的欲望,更渴望將藝術與自身生活結合,這促使了藝術與非藝術的結合。藝術品作為社會景觀的模擬,表現出觀賞性的同時也具備消費特性。藝術商業化賦予了藝術品將人內心深處的隱秘不發的欲望引出的能力,用直白的方式直擊人們內心隱秘的期望,這樣的藝術品不僅能滿足人們對于自身的美好幻想,也能讓藝術品更能充滿商業價值。藝術的歷史感、距離感和神秘感在嚴肅規則喪失中消解,如今夸張與荒誕的藝術規則,讓藝術囿于孤立的截點,向前看找不到確定的方向,向后看厚重的歷史抓手早已消解于荒誕的藝術創作中。如今,對前一個社會思潮集體反叛的后現代主義在開啟自身的同時,也開啟了挑戰藝術規則之路。其實,無論藝術規則如何變化,其本身的游戲特性不會改變。藝術要想長遠發展,就要保證發展動能充足,動力持久。雖然觀眾與批評家的積極反饋與傳播也是增強藝術動力的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求藝術家能把握好藝術規律,秉承對待藝術嚴肅認真的原則,作為游戲參與者拋下自我,堅持融入藝術這場游戲,保證藝術發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