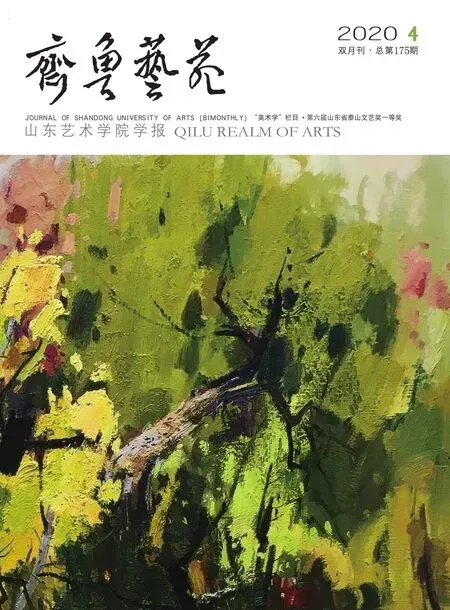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研究:維度、視角與方法
侯瞳瞳
(上海交通大學(xué)媒體與傳播學(xué)院,上海 200210)
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如今已經(jīng)成為了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股令人矚目的力量。根據(jù)艾瑞咨詢2019年最新發(fā)布的《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出海研究報告》,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跨文化傳播以東南亞地區(qū)為發(fā)端,在經(jīng)歷了2004—2011年的起步階段、2012—2017年的開創(chuàng)階段之后,正式步入發(fā)展階段,在全球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所占據(jù)的地位日益突出。具體來看,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跨文化傳播,有著三個層次的意義: 政治上,肩負(fù)著推動國家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實施、提升中國話語權(quán)的重任;經(jīng)濟上,有助于扭轉(zhuǎn)我國長期以來的文化貿(mào)易逆差局面;文化上,在彰顯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同時,有望促進人類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互動與交流。
當(dāng)下,國內(nèi)學(xué)界有關(guān)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研究和跨文化傳播的研究都比較豐富,但關(guān)于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則相對匱乏。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紛繁錯雜,因此需要我們通過對相關(guān)研究現(xiàn)狀的爬梳,來探尋其跨文化傳播的可能路徑。
一、文化源泉、技術(shù)叢林、他山之石: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三個維度
決定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效果的因素是很復(fù)雜的:市場因素、政策因素、媒介因素、文本因素,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要從這錯綜復(fù)雜的因素中理出一條清晰的線索來并非易事。這也是目前有關(guān)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系統(tǒng)研究相對匱乏的原因之一。在我看來,以文化因素作為研究的基礎(chǔ),以媒介機制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他國文化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成功經(jīng)驗作為研究借鑒,是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研究的三個重要維度。
其一,跨文化傳播被認(rèn)為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個體的交流,不同的文化決定了語言、行為等交流方式的不同,同時也決定了不同的信仰、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跨文化傳播的目的在于理解、包容、接受以及尊重彼此的文化方式,狀態(tài)、內(nèi)涵,構(gòu)建彼此可認(rèn)知、可相互區(qū)別和尊敬的共識文化,在此基礎(chǔ)上達(dá)到彼此交施、彼此尊重,彼此促進的目的。因此,跨文化傳播首先是“文化”的傳播。具體到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傳播來看,也離不開“文化”的因素:首先,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生成機緣來自于傳統(tǒng)文學(xué)的生存危機,它作為消費社會信息技術(shù)高度發(fā)展下傳統(tǒng)文學(xué)和互聯(lián)網(wǎng)碰撞的產(chǎn)物走進人們的生活,因此可以說,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根植于后現(xiàn)代消費文化和文化工業(yè)的土壤;其次,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審美機制是機械復(fù)制的“仿像”符號審美,以及游戲世界的“快樂”審美,這些都符合后現(xiàn)代主義為文化背景的審美范式——從深度時間模式轉(zhuǎn)向平面空間模式、從中心化的自我焦慮轉(zhuǎn)向非中心化的主體零散化、從個性風(fēng)格的表達(dá)向仿像的機械復(fù)制轉(zhuǎn)變、從自律的審美觀念向消費邏輯轉(zhuǎn)變[1];再者,隨著冷戰(zhàn)時代的結(jié)束和全球化大潮的奔涌而來,一種跨文化、跨國界、跨語言的“文化對話”成為當(dāng)代學(xué)界的核心問題,中國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中就蘊含了“文化對話”的精神,促進了異質(zhì)文化之間的共生與互動,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霍米·巴巴的“文化雜糅”理論、愛德華·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以及J·斯特勞哈爾的“文化接近性”理論等諸多文化理論中覓得蹤跡。文學(xué)評論家夏烈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首先是個文化問題”,它有著豐富的文化向度,它在今天的發(fā)生是復(fù)雜多元的力量和文化潮流的雜交。對它的認(rèn)識,其實也是對我們這個時代及其文化實質(zhì)的逼近。[2]以上種種可知,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本質(zhì),是文化的傳播。因此,文化維度的研究,是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基礎(chǔ)。
其二,以技術(shù)叢林的媒介機制作為切入點是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可行維度。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誕生之初,便是文學(xué)與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聯(lián)姻的產(chǎn)物。麥克盧漢曾言:“媒體會改變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會消滅一種文化,引進另一種文化。”[3]鮑德里亞亦道:“鐵路帶來的‘信息’并非它運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新的結(jié)合狀態(tài)……電視帶來的‘信息’,并非它傳送的畫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關(guān)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tǒng)結(jié)構(gòu)的改變。”[4]希利斯·米勒則直指:“媒體就是意識形態(tài)。”[5]由此可見,傳播媒介不僅是文化生產(chǎn)與文化傳播的工具,同時它還決定了文化的類型、風(fēng)格以及作用于社會現(xiàn)實的方式和范圍。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重要任務(wù)之一,就是通過技術(shù)叢林的媒介機制去呈現(xiàn)微妙而精神的文化價值體系,從而對外傳播中華文化的精神特質(zhì)。那么,媒介機制之于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跨文化傳播,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了,正如北京大學(xué)教授邵燕君所認(rèn)為的那樣,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蓬勃發(fā)展深受媒介革命的影響,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獨創(chuàng)的一套生產(chǎn)機制。艾瑞咨詢2017年發(fā)布的《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出海白皮書》中,這套生產(chǎn)機制得以一目了然地呈現(xiàn)于眾(見圖1),這引發(fā)了學(xué)者們關(guān)于這套機制內(nèi)各環(huán)節(jié)的細(xì)致研究和討論。綜合現(xiàn)有研究的觀點可以發(fā)現(xiàn),這套機制的成功之處主要在于:網(wǎng)絡(luò)傳播媒介激活了廣泛的民間力量,采取民間自發(fā)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文化宣傳,少了些刻意,反而增加了海外讀者的親切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抵觸心理。但同時,該機制目前尚不夠成熟,面臨著翻譯、版權(quán)、盈利等諸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尚有待探討。此外,隨著熱門作品的不斷涌現(xiàn),IP價值開始被挖掘,傳播渠道將變得更為多元化,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開始以影視劇、動畫等形式呈現(xiàn)給海外受眾。那么,在IP運營機制上,也有了更多值得深入思考的空間。總之,以媒介機制為切入口,一則是因為它是實現(xiàn)深層次文化傳播的必由之路,二則是因為該機制的具象化、可操作化而易于把握。

圖1 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出海行業(yè)產(chǎn)業(yè)鏈[6]
其三,以他山之石作為借鑒來進行研究,可以使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更具針對性。法國記者弗雷德里克·馬特爾曾在大量深入調(diào)查美、日、韓、印等國代表性文化產(chǎn)業(yè)的基礎(chǔ)上,整合編撰了《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zhàn)爭》一書,旨在探尋文化產(chǎn)業(yè)如何占據(jù)世界主流文化地位等問題。令人遺憾的是,全書幾乎沒有提到中國的文化產(chǎn)業(yè),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對中國電影略有提及,然而作者的訪問對象均為與審查職能有關(guān)的大陸官員,對于如何進入中國電影市場,受訪者給出的答案也是乏善可陳。如此看來,馬特爾所說的“主流”似乎并沒有中國文化的一席之地。而如今,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海外傳播剛剛起步便成績斐然,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我們在文化輸出上的自信力。因此,我們需要借鑒世界上文化產(chǎn)業(yè)強國和文化輸出大國的成功經(jīng)驗,來對自身的發(fā)展?fàn)顩r有一個自省式的照察,如此才能為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跨文化傳播乃至更長遠(yuǎn)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大計建言獻(xiàn)策、增添助益。
二、宏觀視野與微觀視點: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視角
跨文化傳播作為獨立的研究領(lǐng)域,始于二戰(zhàn)后的美國。1959年,愛德華·霍爾的著作《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問世,這部作品開創(chuàng)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新領(lǐng)域,他本人也因此被譽為跨文化傳播研究之父。中國學(xué)者對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始于20世紀(jì)90年代,在經(jīng)歷了初創(chuàng)期(1990-1995年)、提升期(1996-1999年)、高潮和深化期(2000年至今)之后,跨文化傳播的學(xué)科構(gòu)建意識逐漸形成。
至今近60余年的發(fā)展過程中,跨文化傳播研究有著豐碩的學(xué)術(shù)成果,與其他學(xué)科及研究方法亦有相互交融。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自近年來開始作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而走出國門,相關(guān)的研究亦是方興未艾:從2014年一些媒體報道的零散見刊,到2015年諸多學(xué)術(shù)論文的陸續(xù)發(fā)表,再到2018年相關(guān)碩士論文開始出現(xiàn),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跨文化傳播在當(dāng)下已然成為了一門顯學(xué)。綜觀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現(xiàn)狀,由于著眼點的不同,大體有宏觀和微觀兩種視角。
偏重宏觀視野的研究者,其邏輯往往是對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跨文化傳播的效果進行一個總體上的評估,找出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應(yīng)對策略。比如艾瑞咨詢(2017)對中國網(wǎng)絡(luò)小說在世界不同地域的受歡迎程度進行了宏觀調(diào)研,并對讀者規(guī)模進行了現(xiàn)狀統(tǒng)計和未來預(yù)估;吉云飛(2017)從讀者體驗出發(fā),指出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縮短了文學(xué)和大眾之間的距離,打破了文藝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界限;閆曉紅(2017)則從經(jīng)濟效益角度考量,認(rèn)為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成功輸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文化貿(mào)易逆差的現(xiàn)象。問題研究上,高純娟(2017)著重強調(diào)作品翻譯質(zhì)量問題,指出翻譯的速度和準(zhǔn)確度是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制約因素,并據(jù)此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提升翻譯人員整體素質(zhì)的策略;庹繼光(2017)從文化層面提出質(zhì)疑,認(rèn)為在海外走俏的大部分玄幻小說并未展現(xiàn)真正的中國文化和核心價值觀,有重數(shù)量輕質(zhì)量之嫌,提出在作品質(zhì)量和文化內(nèi)涵上下功夫是未來發(fā)展的重中之重;田小軍(2017)則從產(chǎn)業(yè)運營角度出發(fā),指出盜版問題層出不窮是制約我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海外傳播的重要瓶頸,同時提出一系列完善版權(quán)管理的運營策略。這些效果評估和策略提挈體現(xiàn)了研究者對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整體性的觀照,但由于研究視野過于宏闊,在策略的具體化和可操作性上似乎有所欠缺。
從微觀視點出發(fā)的研究多立足于某部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成功的經(jīng)驗,抑或是某個閱讀平臺的運營模式,通過作品的文本分析或平臺運作各環(huán)節(jié)的解讀,以期為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提供可行的操作技巧。比如馬換娜(2017)對武俠小說《七殺手》的英譯本展開語料庫研究,并分析了改文本受到英語讀者廣泛喜愛的原因;林玲(2018)依托譯介學(xué)理論,以玄幻小說《盤龍》為例,從主體、內(nèi)容、途徑、受眾、效果等五個方面探討該作品在譯介學(xué)上的技巧及其傳播成功的原因;萬金(2017)則以翻譯網(wǎng)站W(wǎng)uxiaworld為例,考察了該網(wǎng)站譯者對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的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相對前述的研究,這類研究更有針對性、更具體、更深入。但綜觀整體的研究狀況,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研究個案多集中于《盤龍》等屈指可數(shù)的幾部作品,且題材局限于玄幻小說,相對整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全球傳播,有些以偏概全、論據(jù)不足;二是研究多傾向于文學(xué)本體的研究,忽略了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語境方面的因素,使研究結(jié)論缺少了客觀性和科學(xué)性。
綜觀以上兩種視角的研究,與其它學(xué)科領(lǐng)域的跨文化傳播研究相比,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尚有許多不足:首先體現(xiàn)在理論積淀上。現(xiàn)有的研究中,含有明確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字眼的研究還比較少,而為數(shù)不多的幾篇還有該字眼的學(xué)術(shù)論文亦只是有名無實,對文化與傳播的關(guān)系缺乏梳理,更毋言理論上的深入闡釋與嚴(yán)謹(jǐn)建構(gòu)。究其原因,可能與研究緣起有關(guān),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研究始于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風(fēng)靡海外的現(xiàn)實,因此學(xué)者們的研究多囿于眼前景況,而忽視了對理論的追根溯源。其次,拋卻理論不談,在實踐研究方面,問題依舊明顯:第一,學(xué)科視角上,“文學(xué)性”有余而“文化性”不足,文化學(xué)視角的研究較為匱乏;第二,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較少,導(dǎo)致研究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強;第三,研究內(nèi)容上,大多局限于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本身尤其是玄幻小說的研究,缺乏產(chǎn)業(yè)視角的實踐研究。
從未來研究趨勢來看,我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著眼于若干問題的解決:其一,注重理論素養(yǎng)的積淀,建立和完善跨文化傳播的理論體系;其二,將宏觀視野與微觀視點相結(jié)合,在全面了解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實踐的基礎(chǔ)上,找出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的契合點,避免人云亦云和自說自話;其三,拓寬研究視野,將其他眾多人文學(xué)科的研究成果納入到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中來,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xué)術(shù)氛圍。
三、理論交融與實證研究: 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方法
理想的研究,應(yīng)當(dāng)基于某一理論,證實某一理論,進一步解釋某一理論,質(zhì)疑某一理論,或有利于提出某一理論。[7]關(guān)于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帶有學(xué)科跨越和理論交融的痕跡,比如Simanowski(2009)、Raley(2009)、Zuern(2010)、Noah(2010)等人就將符號學(xué)、敘事學(xué)、闡釋學(xué)、接受美學(xué)等傳統(tǒng)文學(xué)審美理論與計算機技術(shù)結(jié)合起來進行研究。這些理論為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研究提供了科學(xué)的邏輯、方法以及范式。因此,將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理論與跨文化傳播理論進行相互的交融研究,應(yīng)當(dāng)是可行且有必要的。
以愛德華·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為例,霍爾將文化語境分為高語境和低語境,高語境文化中的語言本身的所指并不能代表其全部的意義,而是需要到語境(即這個文化群體的習(xí)慣、思維、潛意識)中去尋找背景,解釋意義,因此處于高語境文化中的語言意義是相對模糊的;而低語境文化則是語言本身能夠指明其意義,這個意義與文化群體的整體思維、習(xí)慣、潛意識保持一定的距離,語言意義相對明確。霍爾將中國、日本等國含蓄的文化形態(tài)指稱為高語境文化,表明文化語境對語言的強大解釋作用;而將美國、歐洲等國直接的文化形態(tài)指稱為低語境文化,語言本身就能較清晰地表明其意義。[8]網(wǎng)絡(luò)玄幻小說中包含大量中國傳統(tǒng)儒釋道等文化元素,這些高語境的文化內(nèi)容通過低語境的表達(dá)方式在歐美等低語境文化國家成功傳播,就與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十分貼合。而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譯者的跨文化適應(yīng)、文本翻譯的跨文化策略、文本內(nèi)容的新奇與共鳴可都是約翰·貝利文化適應(yīng)理論的最好寫照。由此可見,對跨文化傳播理論的借鑒和交融,為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立足點和理論支撐。
鑒于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研究始于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出海熱這一現(xiàn)實景況,我們的研究應(yīng)當(dāng)以實證研究為重心。在實證研究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學(xué)界公認(rèn)的兩種主流范式。谷學(xué)強、汪中瑞的論文《從WuxiaWorld爆紅看我國網(wǎng)絡(luò)小說的跨文化傳播》是定性研究的典型之作:先分析中國玄幻小說跨文化傳播成功的原因,再歸納總結(jié)出相對應(yīng)的策略。這種先分析、后歸納的研究方法在目前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跨文化傳播的定性研究中較為普遍,譬如葉雨菁《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的跨文化傳播解讀》、郭競《也談中國文學(xué)翻譯出版“走出去”——以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歐美熱為例》等都屬于此類。這種研究范式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由于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既是參與者又是觀察者,因此,與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的主觀性更強、結(jié)構(gòu)性則相對較弱。
定量研究方法則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定性研究的不足。例如邱冬勝的碩士論文《網(wǎng)絡(luò)玄幻小說在北美的傳播研究》就采用了問卷調(diào)查的方法對中國網(wǎng)絡(luò)玄幻小說跨文化傳播的問題和對策進行了定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調(diào)查范圍僅限于玄幻小說,并未涉及言情、歷史等其他題材類型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調(diào)查問卷發(fā)放至網(wǎng)絡(luò)平臺,調(diào)查對象則相應(yīng)就是北美網(wǎng)絡(luò)小說翻譯平臺Wuxiaworld、Gravity Tales、Novel Updates及 Novel Translations 官方網(wǎng)站的網(wǎng)友,這不禁引發(fā)我們的疑問:這樣的研究結(jié)果是否足夠嚴(yán)謹(jǐn),以至于能夠推廣到其他類型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中乃至不同的語境和閱讀群體中嗎?竊以為,該研究的科學(xué)性、可靠性問題尚有待商榷。
總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在我國才剛剛起步,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體系。筆者以為,文化、媒介機制、他國經(jīng)驗是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三個維度;宏觀視野與微觀視點的結(jié)合是可行視角;理論交融,以及定性和定量相結(jié)合的實證研究是有效方法。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相信在眾賢的上下求索之中,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產(chǎn)業(y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范式一定會日臻完善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