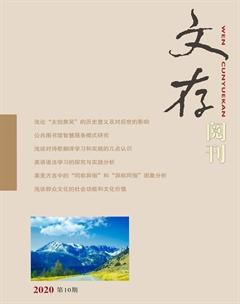福克納對余華小說敘事藝術的影響分析
梁冰雪
摘要: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余華,小說敘事藝術獨特,結構布局巧妙。其小說創作也深深得益于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寫作風格。全文旨在通過發掘兩位作家之間的關聯,從敘事結構與表現形式兩個角度來探討福克納對余華敘事藝術的影響。
關鍵詞:福克納;余華;敘事藝術
一、回環式的敘事結構
余華筆下的所有故事都有著相當嚴謹緊密的邏輯,滴水不漏,環環相扣。這讓讀者在一個循序漸進的狀態下跟隨情節發展律動,但又不過于忙亂。以《第七天》為例,主人公楊飛是主環,他連套著一些不同的次環,次環又連套次次環,從而形成連環式結構。于是,故事的講述者就由楊飛蟬蛻到“肖慶”,然后“肖慶”以第一人稱為大家講述“鼠妹”到“死無葬生之地”后大家所不知道的故事。《第七天》的邏輯相當嚴密完整,它實際上述說的并不是中國風俗里常提到的“頭七”,而是西方《創世紀》里上帝制造萬物的那一個星期。并不是寫所有人都離開了人世,而是將一切故事串聯成為了一個完整,美好的死者世界,并與殘酷的現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用以寄托作者強烈的批判和諷刺傾向。
回環式結構在《活著》《第七天》中都有一定的體現。福貴戰時患難與共,互相依賴卻最后失散的好朋友春生,回頭來竟然搖身一變,成了間接害死福貴兒子的縣長大人。福貴憤怒,悲傷得要死,但心中卻難以對春生下手,甚至無法對這個善良的同伴產生仇恨,只是讓他不要再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之中。而最終,被打倒了的春生滿懷著愧疚,將自己的全部家當交給了福貴,毅然決然地踏上了自己的道路。在《第七天》中,“我”和“父親”實際上都一直在尋找著彼此,從文章開頭一直到文章末尾,直到經歷了無數個他人的故事后,我才知曉,原來一開始在排號處等人的那位老人,就是我親愛的養父。這種回環式的寫法給文章帶來了別樣的韻味,如同文章中的前后呼應手法,先埋下深深的伏筆,最后再將其提出,叫人在某一瞬間頓時大悟,隨即回味無窮。
福克納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也有這種回環式的敘事結構。小說五個小節,從愛米麗的去世,到結局又回到她的死亡,首尾相接。在五個小節中,時序反復顛倒,故事懸念重重,福克納正是通過這種非傳統的敘述手法來使讀者注意故事的有關時間的主題。同時,在《押沙龍!押沙龍》中,福克納也通過大量的穿插敘述和將多個分崩離析的故事糅雜在一起的描寫(從亨利槍殺好友邦后逃逸,到最后解釋亨利因為無法接受邦是自己的兄弟,精神崩潰行兇的真正原因),彰顯了這種別具一格、同時具有相當大寫作難度的敘事結構。
二、冷漠低調的表現形式
表現形式一般是指敘述手法和語言的運用,余華對形式的偏愛和采用新形式的表現方法極大地引起了讀者的注意。為與死亡、暴力的敘事相呼應,余華還采取了冷漠低調的敘述態度,并常使用非常人的視角。例如《一九八六》《第七天》,前者通過精神病患者的經歷把暴力用原生態式展示,把歷史的殘酷性呈現出來,而后者卻用死者的視角來審視人類常有的感情,強調故事本身的殘酷荒誕。《活著》全書講述的故事慘烈至極,但語言卻平實無華,沒有運用什么辭藻,敘述也少見波瀾。小說中完整的故事,明晰的線索,樂觀的生活態度與冷靜平淡的寫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價值包容在從容的形式敘述之中。而《許三觀賣血記》中更是展示了一種全新的精神氣象,殘酷,冰冷的現實被人們不斷用豁達積極的態度應對,以層出不窮的幽默語言交流,家庭中的憐憫和溫情,取代了令人發指的殘酷場景和陰暗的環境氣氛,可以說,余華表現了讓人驚嘆的敘述手法和語言表現力。
同樣,我們也能夠從福克納的經典作品《喧嘩與騷動》中,看到相同的藝術表現形式。該小說講述的是南方沒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劇,與《活著》中因為時代黑暗與個人陋習逐漸衰敗的福貴的地主家庭,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小說的開頭是老康普生的三子—白癡班吉進行的敘述。盡管這個人物的現實年齡已經達到了三十三歲,然而,他的智力卻僅僅只停留在了三歲孩童的階段。除了哭嚎,他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情感。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個在腐朽衰敗、充滿了爭斗與猜疑的黑暗的大家庭中成長的人,他沒有沾染上半點不良的習氣。相比于父母與兄弟姐妹們表現出來的人性的丑惡面,班吉更像是一面鏡子,只是單純地反映這個家庭,以及故事的隱藏中心人物凱蒂的混亂與墮落的一生。
另外,與《喧嘩與騷動》略有不同的是,除了在正文部分偶然穿插著的“我”和福貴的對話外,《活著》的大多數描寫,都來自于福貴的第一人稱敘述,因此,讀者在閱讀時,會有著更加直觀的判斷與體驗,也更能站在主角的立場上思考問題,深沉地思考他波瀾壯闊的一生。而《喧囂與騷動》,則是使用了四個第一人稱視角,也就是將地主老康普生三個個性各異的兒子的心理活動描述與黑人女仆迪爾西的“補充性”描述,作為全文的基本敘述方式。盡管表現更為深刻全面,然而,也對讀者的閱讀能力與審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結語
余華的先鋒文學創作得益于對福克納小說創作的研究和學習。福克納對余華小說敘事藝術方面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回環式的敘事結構和冷靜低調的表現形式。這在他們的作品《喧嘩與騷動》和《活著》中都有所體現。
參考文獻:
[1]王曉梅.福克納對中國當代家族小說敘事藝術的影響[J].時代文學(下半月),2015,No.309,235-236.
[2]黎子瑩,苦難中蘊涵的美學力量——論余華作品的美學特征[D]2016-03-11
[3]耿菊萍;王震魁.美國文學滋養下余華先鋒精神的救贖[J].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v.38;No.182,37-39.
[4]馬雅楠.福克納和余華小說惡的主題比較研究[J].學理論,2013,No.647,174-175.
[5]羅伯特·W·罕布林;李萌羽;楊燕.國際化的福克納——兼與蘇童、沈從文、莫言、余華創作比較[J].東方論壇,2017,No.145,5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