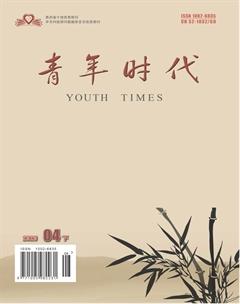宗澤鎮江事跡考
吳耀洋 江帆
摘 要:宗澤是抗金名將,曾有四年被貶鎮江,亡于東京后亦葬于鎮江。由于他在鎮江為官時間短暫,且在對宗澤現有的研究中多關注其抗金事跡和作品集分析,以致其鎮江事跡在《宋史》等史傳和地方史志的記載中,頗多遺誤。按現有之史料,對宗澤貶官原因、鎮江為官事跡、抱憾而死的結局等進行較為全面的考異、辨正和補遺,將有助于對這個歷史人物的進一步了解。
關鍵詞:鎮江;宗澤;事跡
關于宗澤的生平事跡,前人已有論及,大多研究宗澤抗金經歷和族譜考跡,對其于鎮江短暫的四年經歷僅有寥寥數筆,并未有所深入研究,導致宗澤在鎮江事跡多有失載、未詳之處。因此,本文擬蹈前輩人之足跡,以宋代官方政書、鎮江地方文獻為基礎,參考古今著述,進一步考察其鎮江事跡與價值傳承,并對一些尚待廓清的問題加以辨識,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一、知人論世:宗澤編管鎮江始末
宗澤,字汝霖,謚號忠簡,婺州義烏人,南宋抗金名將。“會倅登日,嘗穹治姦人,有司觀望,坐此褫秩,羈置鎮江府四年,就起為酒官。”這是位于鎮江京峴山宗澤墓上的墓志銘,寥寥數語,道出了宗澤與鎮江的淵源:宗澤被關押于鎮江,后遇大赦擔任鎮江監酒,逝世后又被葬回鎮江京峴山。
研究史料發現,宗澤被貶鎮江的原因與當時社會政治背景密切相關。“于官登州任內坐建神霄宮不虔,遭道士林靈素等攻訐。”由、此可知宗澤被貶至鎮江,源于道士林靈素的誣陷,這便不得不提當時盛行的道教文化。北宋政和以后,道教盛行。《宋史·林靈素傳》中記載,政和七年,道士林靈素以法術得幸徽宗,被封為“直通達靈元炒先生”。在他的影響下,宋徽宗對道教的崇尚在宋代歷史上達到極點,道教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幾乎成為國教。為了發展道教,宋徽宗下令各州縣廣建道教宮觀“神霄宮”,甚至將宮觀道士與各級地方官置于同等地位。道士由此仗勢豪奪,各地神霄宮也大量兼并田產,給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宋史·宗澤傳》寫到宗澤任登州通判時說:“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余緡,率橫取于民,澤奏免之。”而這便是宗澤于道士林靈素矛盾的根源。北宋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十四宗忠簡公傳》記載了登州道士高延昭“倚林靈素,凌滅郡邑”,“恃勢犯法,無復以州縣為意”,唯有宗澤敢于“窮治”。宗澤上任后,在查清了高延昭的種種不法行為之后,明知高延昭有政治背景,仍依法將他嚴加懲治。宗澤無畏權貴的為官精神由此便可看出。然而他造福了一方百姓,也因此事給自己帶來了貶官之禍。宣和元年初,宗澤乞請告老還鄉,獲準授予主管應天府鴻慶宮的掛名差使,不料高延昭通過林靈素向徽宗誣告宗澤蔑視道教,任登州通判時改建道觀“神霄宮”不當,于是徽宗下令將宗澤“褫職羈置”,發送鎮江府編管。《宗澤集》中也記錄了宗澤“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褫職”,證實了宗澤被貶鎮江的原因。經此一事,年至六十的宗澤再次踏上宦游之路,宦途走到最低點。
二、亂世堅守:宗澤為官鎮江史實考及政績評價
“削職羈置鎮江”短短六個字,道盡宗澤于鎮江的低沉仕途。而宗澤在鎮江的四年究竟是何經歷,可以在搜集史料的過程中得到解答。削職羈置的宗澤,在宣和四年得以被釋放。“壬戌,以復燕、云,大赦天下。”由于金歸還宋燕云十六州,徽宗舉行祭祀大典,實行大赦,宗澤才重獲自由,被差遣監理鎮江府酒稅。宗澤墓志銘上的“羈置鎮江府四年,就起為酒官”便能佐證。“四年差監鎮江府酒稅,敘宣教郎。公盡心,乃職課入倍加。”宣教郎為宋朝文官,從七品,監管鎮江府酒稅,是個微不足道的職務。可宗澤依舊克己奉公,盡心盡力,把小官職也干得有聲有色,使得當地酒稅的收入成倍增長。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松杉剝落精靈在,父老悲吟諫書傳。”(《憑吊宗澤》)百姓對宗澤的認可在清代詩人張九征的詩句中得到了體現。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羈置鎮江四年間,宗澤杜門卻掃,賦詩自娛,恬然自安。公元1121年,其兄宗沃意外去世,隨后一年,其妻陳氏撒手西歸,“公娶陳氏至是疾卒卜,葬京峴山之陽就、居丹徒經郊”。六十多歲的宗澤揮淚寫道:“一對龍湖青眼開,乾坤倚劍獨徘徊。白云是處堪埋骨,京峴山頭夢未回。”(《葬妻京峴山結廬龍目湖上》)詩雖是對亡妻的悼念,字里行間卻也能讀出他對國家的擔憂和對命運的抗爭。
三、魂歸舊地:宗澤葬于鎮江史實考
據《宗澤集》記載他死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這一年對宋王朝來說依舊是灰暗的一年,中山府、洺州、濮州相繼陷落。這一年對于宗澤來說依舊是壯志難酬的一年。建炎二年,宗澤先后向高宗上了24道《乞回鑾疏》,懇請趙構回鑾東京鼓舞士氣,并制定了詳細的渡河計劃,渴望成就中興大業。然而當時朝政已被黃潛善等人把持,他們一味屈膝投降,唆使宋高宗南逃揚州,國運日益衰微。
宗澤的壯志難酬從何而來?回首宗澤的為官生涯,他并非碌碌為無的庸官。調離鎮江后,他先后經歷了磁州備戰、抗金勤王、鎮守開封和保衛東京,戰果累累,其英勇名震敵國。然而宋王朝早已支離破碎了,強敵來襲,權奸當道,在政治極端腐敗的環境下,真正的忠臣——宗澤無法得到提拔和重用,最終只能空懷著對宋朝的忠心,憂憤成疾,郁郁而亡。
“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在彌留之際,他“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聽者無一哀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至死不忘渡河滅敵,宗澤的愛國精神令人動容。
關于宗澤所葬之地,諸多史書皆有記載。《宋史·宗澤傳》言宗澤去世后由兒子宗穎和愛將岳飛一起扶柩至鎮江,與夫人陳氏合葬于鎮江京峴山上。宗澤對岳飛的知遇之恩,在《宋史·宗澤傳》中有所記載:岳飛私自出兵違抗軍法將被處斬,宗澤見此甚為惋惜,便將五百騎兵交給岳飛,讓他立功贖罪。岳飛大敗金人而回,宗澤升岳飛為統制,岳飛由此知名,直至大將軍。因此,宗澤是岳飛名副其實的恩師。《宗澤集》中雖未提及岳飛扶柩一事,但也記載了“子宗穎扶柩掃鎮江,與夫人陳氏合葬與京峴山”。“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宗澤墓,在京峴山”,亦能證實宗澤的確葬于鎮江京峴山。
四、緬懷追思:文化遺產宗澤墓及當代繼承價值
宗澤墓位于江蘇省鎮江市東郊京峴山北麓,建于宋代,現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宗澤葬于鎮江京峴山后,岳飛為懷念恩師宗澤的知遇之隆,于塋旁花山灣云臺寺創設“宗忠簡公功德院”,以祠祀宗澤,即如今的紀念堂。到了嘉定年間,岳飛之孫岳珂以總餉駐節鎮江軍府,命重修功德院,并親撰《重修忠簡公功德院記》。宗澤墓前本還有享堂建筑,《嘉定鎮江志·卷十一》記載著:“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宗澤墓,在京峴山。顯謨閣學士曾懋銘,近守臣吏部侍郎俞烈重建享堂。”俞烈在鎮江任太守的時間是嘉定元年至三年,距岳飛及宗穎建墓時間達80余年之久,其時初建的享堂已歲久廢圮,故俞烈又重建享堂。而之后南宋鎮江太守趙善湘又專為新建享堂寫有《宗忠簡公享堂記》。1982年江蘇省人民政府公布宗澤墓為文物保護單位時享堂已不存在,直到2005年《中國文物報》報道了宗澤墓區發現宋代享堂遺跡,享堂面貌才得以展現。
八百多年來,宗澤墓經歷代多次修繕,大體保持原貌。墓前豎白云墓碑,上刻“宋宗忠簡公諱澤之墓”九個大字,墓前的石坊兩邊石柱上刻有一副對聯:“大宋瀕危撐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墓道兩旁密集綠樹,莊重肅穆,表達著對英雄的敬意。京峴山腳下還堆放刻著愛國詩詞和贊頌宗澤詩歌的卵石,如鄭成功的《謁京峴山宗澤墓》、宗臣的《登京峴山吊宗忠簡公墓》及張九征的《憑吊宗澤》等,無一不表達著對宗澤愛國精神的歌頌。當年悲憤激烈的呼聲,似乎與墓北側洶涌激越的江流之聲,相互呼應。在這青松翠柏的山麓,成了一代名將的長眠之處。
宗澤是愛國英雄,亦是吾輩之精神榜樣。作為歷史名人,他對后世的價值不可忽視的,他既體現了鎮江的文化底蘊,亦是鎮江展現魅力的一張名片。
2012年12月,響應國家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號召,以宗澤墓為本體的鎮江宗澤紀念公園正式建成。紀念公園的成立,為傳承發揚宗澤精神提供了物質載體。鎮江山水漢居漢文化研習社每年都會舉行宗澤祭祀大典,身穿漢服的市民們“復制”古代公祭大禮,演習射藝,射以觀德,修文習武,紀念這位抗金名將。這些活動不僅提升了鎮江人民對鎮江文化的認同感與自豪感,也能讓更多的人認識、了解宗澤,擴大其愛國精神的影響力,使宗澤憂國憂民、維護國家統一的優秀精神永流傳,從而推動著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建設。
除此之外,紀念公園共分為文物本體修繕、宗澤紀念館建設、生態停車場建設、綠化景觀設置和環境整治五部分,作為一個集愛國主義教育、休閑健身為一體的開放式森林公園,它的建成為市區東部新增了一座城市“綠肺”,對提升地域文化內涵、地域環境都有著極大的作用。
最后,宗澤作為展現鎮江魅力的一張名片,激起了無數國內外游客的好奇,這不僅使宗澤紀念公園重獲生機,讓宗澤精神浩氣永存,亦可促進鎮江旅游業的發展。同時,對宗澤的研究促進與其相關書籍的銷售及衍生品的產生,推動著鎮江的文化產業與經濟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宗澤.宗澤集[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
[2]脫脫.宋史卷二二 徽宗本紀[M].北京:中華書局,2000.
[3]脫脫.宋史·宗澤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0.
[4]盧憲.嘉定鎮江志[M].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