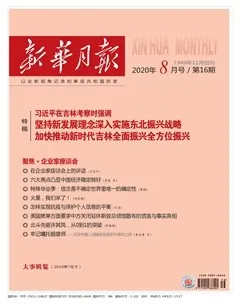“治本之法”嚴格規制醫鬧行為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
《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
法》(以下簡稱《醫療促進法》)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可以稱之為我國衛生與健康領域的“根本大法”。該法從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醫療衛生機構、醫療衛生人員,到醫療藥品供應保障、民眾健康促進,再到醫療資金保障、醫療監督管理等,均作出規定。如果能將其中所提出的院前急救體系、分級診療制度、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機制等各項制度都建立健全并切實落到實處,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少傷害醫務人員、擾亂醫療秩序現象的發生。
兩種違法類型
對于檢察機關而言,既要利用法律武器對違法犯罪行為準確實施打擊,用好法律規定,依法及時、從嚴懲治各類涉醫違法犯罪,有效保障醫務人員安全,維護良好的醫療秩序,也要認真落實“誰執法誰普法”的責任,深入細致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引導廣大群眾遵紀守法,為國家社會醫療服務工作順利開展營造良好的法治和社會環境。

侵犯醫務人員安全、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即通常所稱的“醫鬧”,其方式多樣,根據相關法律文件的規定,結合檢察機關的司法實踐,可以將之歸納為兩種類型:第一,對醫務人員的人身實施的侵犯行為,包括傷害、殺害醫務人員,以暴力、威脅等方法非法限制醫務人員的人身自由,或者公然侮辱、恐嚇、誹謗醫務人員。第二,對醫療場所正常秩序實施的擾亂行為,如非法攜帶槍支、彈藥、管制器具或者爆炸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蝕性物品進入醫療衛生機構,或者強拿硬要、故意損毀、占用醫療衛生機構的財物,造成秩序混亂,影響醫療工作正常進行的行為等。
對上述侵犯醫務人員安全、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應當視行為性質、情節嚴重程度分別予以治安管理處罰和刑事處罰。
引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那么,《醫療促進法》對于“醫鬧”是如何進一步從嚴規制的呢?在此要提醒醫療服務接受者:擾亂醫療場所的行為面臨更全面的制約——《醫療促進法》增加了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對這類行為的規制。在滿足行為人具有抗拒、阻礙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前提下,聚眾擾亂醫療場所秩序的行為可能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醫療促進法》首次明確將醫療衛生機構執業場所界定為公共場所,并要求“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擾亂其秩序”。也就是說,從今年6月1日起,將聚眾擾亂醫療場所秩序的行為定為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是名正言順的。而在此之前,對于“醫鬧”的行為規制一般只涉及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其行為人的目的是直接針對特定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行為人并不以擾亂特定單位工作秩序為目的。如果行為人主觀上過失,導致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無法工作,造成嚴重損失,那么雖然不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但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通俗地說,如果有人在醫療場所鬧事,即便他們針對的目標可能不是醫院和醫生,但只要破壞了醫療秩序,影響了醫院的工作,就可能觸犯法律。這實際上加強了對行為人在醫療場所活動的約束。
對“醫鬧”的法律規制越來越嚴格
《醫療促進法》將“醫鬧”納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的規制范圍,體現了相關立法、執法的不斷完善。
如前文所述,涉醫刑事犯罪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醫護人員個體的,另一類是針對醫療秩序的。對于針對醫護人員個體的侵犯人身權利類犯罪定性,司法實踐中爭議不大,偶有爭議,主要表現在尋釁滋事罪、故意傷害罪和侮辱罪等的適用。

爭議比較大的,是涉及醫療場所的犯罪行為。2015年之前,這類行為主要由尋釁滋事罪來加以規制。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將破壞醫療秩序行為納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規制范圍,進一步加大了對擾亂醫療秩序行為的打擊力度。
在同樣涉及擾亂醫療場所秩序的情形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與尋釁滋事罪的區分主要有三點:第一,犯罪形式上有一定差異。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表現為多人以上以聚眾形式出現,而尋釁滋事罪不要求聚眾。第二,追究刑事責任的主體范圍上有一定區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只追究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的刑事責任,尋釁滋事罪的所有參與者一般都要以本罪追究刑事責任。第三,犯罪客觀方面的要求有一定差異。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發生在醫療場所的多人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如果同時符合上述兩罪的犯罪構成,那么應當基于特別法優先于一般法的要求,優先適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單就合理性或者刑事政策的需要來看,更多情形下適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會更恰當一些。第一,這契合了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原本應有之義;第二,這不違背競合情形下“從一重處”的刑法基礎理論;第三,從犯罪起因方面考量,尋釁滋事罪往往是出于無事生非、逞強耍橫等動機,而實踐中擾亂醫療場所秩序的行為往往并非“無事生非”,而是“借故生非”“借題發揮”。
從相關的立法歷程可以看出,從尋釁滋事罪到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再到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對于“醫鬧”行為的法律規制是越來越嚴格的。
《醫療促進法》中針對“醫鬧”的新規定,還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明確了“醫療衛生機構執業場所是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共場所”,其中“公共場所”的界定將手術室、重癥監護室等無關人員禁入的區域排除在外,體現了法條的準確性。至于掛號區、候診區等區域,顯然屬于公共場所。在此提醒赴醫療機構的公眾,在這些區域應注意規范自己的行為。
其二,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同時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那么應遵循“從一重處”原則。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為單一刑檔,最高刑為五年有期徒刑。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對于首要分子處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行為人的行為更可能被定性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醫鬧人員黑名單”制度
《醫療促進法》正式實施后,檢察機關將有針對性地加強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依法從嚴打擊傷醫行為。眾所周知,醫生等特殊行業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理應受到更多的保護。因此,對于傷醫行為的從嚴規制,既能體現刑事政策導向,也有利于有效遏制暴力傷醫行為的發生。二是配合并支持衛健部門,建立醫療機構之間的“醫鬧人員黑名單”制度,提前預防把控風險。為配合“醫鬧人員懲戒機制”的建立,各部門會采取全方位、跨部門的聯合懲戒措施,建立懲戒效果通報機制,實現公安、衛生等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以確保各部門密切協作,積極落實相關信用懲戒機制。
(摘自《檢察風云》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