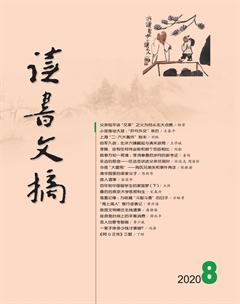箋墨記緣:為收藏“斗智斗勇”的日子

“書估”“足下”的錢穆
“書估”者,售書人也,另有美名曰“書友”。《蕘圃藏書題識》中兩名并用,但有辨別。得意時呼以美名,愛之也;失意之時,則以惡名稱之,賤之也。余對售書人,無尊之之意,亦無恨之之心,故而本篇通用“書估”者也。
“足下”者,稱謂也。“足下”戰國時已見,多用于稱君主,后來才用于平輩。另有同類稱謂“閣下”。古時作為尊稱并用,但有區別。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三說:“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于尊貴者。蓋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后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諸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本篇“書估”“足下”連用,非稱謂也,乃實指“書估”之“足”也。
兜了半天圈子,繞了一大彎兒,其實,本篇要敘述的是十幾年前,我在一個書估的腳下發現了一封錢穆先生寫給商務印書館的鋼筆信的故事。
那天,我正在上班,呼機上顯示了一個不熟悉的電話號碼。我馬上回電,原來是時常賣給我舊書的書估傳呼的。我問他又踅摸到什么好東西了。書估告訴我,幾天前他們從南城的一個回收站那里收到幾公斤某出版社丟出來的書稿,北大的程先生和許川都看過了,他們都給不上價。如果我感興趣,他和他的合伙人包租了一臺小面包車,可到我的單位來接我,到他們的住地去看貨。
那時我的身體好,有精力,經常下班后到那些書估住地看東西,幾天不去,心里還挺鬧騰的。一聽說有好東西自然很興奮,當即同意下班同往。
車行進到去往書估住地的窄小石子馬路,開始顛簸起來。坐在凳子上,低首翻弄車廂里的書,身體總往前躥,我干脆蹲下來翻看。這時,我發現對面打著瞌睡的書估腳下,結結實實踩著一份用曲別針別住的文稿,最上邊兒的是個發文單,仔細打量,原來是商務印書館出來的東西,受文者欄有“錢穆”字樣。我試圖從書估的腳下抻出這份文稿,但沒有成功。
那一年,我剛剛翻閱過一套叫《百年國士》的書,錢穆位列書中50名國士的第27位,在林語堂后,馮友蘭前。那時,我已集藏有書中所列的50名國士中大半的文人手跡。缺少的,而且最不容易搞到的就是林語堂、趙元任、梁實秋、錢穆等在海外定居的幾位的。今天能看到有關錢穆的東西,我怎能罷休。
看到這里,讀者會說,拍拍書估的腿,讓他抬腳,取出來看看,不就得了嗎。圈兒外的朋友有所不知,這一行素有“賣的沒有買的精”的說法,原因是這些流動的書估,大都來自于窮僻的山區,沒有上過幾天學,都是在做中學。而那些買家往往是做學問的,當然也有特別懂行的書商。這些書估進到一批貨,往往不急著出手,而是要通知許多買家來看,一圈兒下來,書估對自己的貨及價都弄明白了,才開始出手,自然誰出的價高就賣給誰。
既然東西被書估踩在腳下,說明書估并不清楚此物的價值。但是,你一拍他的腿,要看他腳下踩著的東西,你關注的東西,就被書估發現了,如果恰好這件東西,正是你渴求的,你越想買,書估就越不賣給你,不是干著急嗎?最好的辦法,就是你要繃得住勁兒,等到機會再出手。
我在這方面,是有過教訓的。因此,今天看見書估腳下有關錢穆的東西,依然不露聲色,繼續翻弄那些舊書爛畫一類的東西。
顛簸了幾公里后,到了書估的住處。書估和坐在司機旁的另一書估,開始撿拾車廂內的東西,那一沓文稿連同曾被書估踩在腳下的文稿,也被收拾到一個尼龍口袋里。
到了書估的屋里,他們把那口袋順手扔到一個破舊的沙發上,袋子里的東西順勢掉下來一些,落在了地上。我一瞥,掉下來的就有一沓文稿。我坐在另一只沙發上,趁著書估拿取書稿的工夫,探身伸手撿起落在地下的文稿翻了翻,見被書估踩過的那份里邊有一封錢穆的親筆信和信封,心里有數了,就又把它扔回到原處。
兩個書估提溜過來三四個紙袋子,放在我面前,我一袋子,一袋子地過了一遍。這批東西整體價值不高,書估開頭說的,某某、某某看過卻給不上價的話,是虛張聲勢。我不太喜歡,也就沒出價。看到書估很是掃興,我看機會來了。就說,在車上翻看那些舊書等物,有的還有點兒用,別白跑一趟,買一點兒吧。書估說,車上的那些東西,是星期天在潘家園賣剩下的,你如果要就“一槍打”,便宜賣給你。我問價,書估開了個我意想不到的低價,我又還了個價,皆大歡喜。書估住地離我家很遠,不可久留。我提溜著那個裝有錢穆先生信的尼龍口袋,出門就打了個“面的”往家趕。
在車上,我迫不及待地找出那份與錢穆有關的文稿。文稿被別在一起,共六頁,第一頁是商務印書館編審出版部收發文的批審單,因被書估踩在腳下,腳印深深地印在了上邊,后來經過裝裱師的處理才弄掉。批審單第一欄受文者寫:錢穆香港九龍嘉林邊道二十八號B地下。事由欄寫:《先秦諸子系年》版權退還作者。發文日期欄寫:1955年5月26日。擬辦欄后附給錢穆的回信草稿:
錢穆先生:
五月四日來信已經收到。大著《先秦諸子系年》由先生在港自印新版發行,我館可以同意。覆致
敬禮
商務印書館編審出版部 啟
第二頁是工具書組就錢穆來信寫給社長的報告:
錢穆(賓四)所作在我館出版,種數甚多:
《先秦諸子系年》(原列“大學叢書”)、《國學概論》、《論語要略》。此次來函要求收回第一種版權。
《先秦諸子系年》一書,過去曾擬重版,但以著者政治面目不明,所以未曾進行。是否可以退還,請批示。
此致
史經理轉社長工具書組
1955年5月19日
時任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史久蕓的批示意見:
《先秦諸子系年》是版稅書,我的意見,可以同意錢穆在香港自印新版發行。
1954年,商務印書館總管處遷京,實行公私合營,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劍西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他的批示是:可予同意。
錢穆先生的信和信封是附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收發文簽收單和登記單后邊的,信之原文如下:
敬啟者:
拙著《先秦諸子系年》一書,廿年前承貴館承印出版。惟此書十年以來久經絕版,而鄙人對此稿亦迭有增訂。茲擬在香港自印新版發行。特此函聞。敬希惠予同意并賜復為盼。
專此,順頌
公祺。
錢穆 啟
五月四日
復示請寫:香港九龍嘉林邊道28號B地下鄙人收。
信封為空郵,貼香港一角郵票。收信地址為: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此地址為原商館地址。
“面的”從現在的奧運村(那時還是朝陽區的村莊)到西城區百萬莊大街我家,大概行進了一個小時。到了大院,我在院子里一個乒乓球案子上,把那口袋舊書倒出來,挑出有用的,剩下的就都丟在了樓道放雜物的木箱里。
敘述完買得錢穆先生手札的過程,再來說說錢穆先生和他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
錢穆(1895年—1990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正如商務印書館編審出版部工具書組就錢穆來信寫給社長的報告中所說,“錢穆(賓四)所作在我館出版,種數甚多”:1925年,《論語要略》(又名《孔子研究》,列入“國學小叢書”);1930年,《墨子》(列入“萬有文庫”)和《王守仁》;1931年,《周公》《國學概論》和《惠施公孫龍》;1935年,《先秦諸子系年》;1937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即便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動蕩不已的歲月,錢穆與商務印書館的交往仍未中斷。1940年,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國史大綱》(當時被列為部定大學用書)由長沙商務印書館印行。1945年11月,《政學私言》(列入“人人叢書”)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同年,錢穆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中國學術思想史之分期》《選舉與考試》《神會與壇經》《學統與治統》《人治與法治》等文。可以說,錢穆前半生的幾乎所有重要著作都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1949年之后,由于各種原因,錢穆與20世紀50年代初從上海搬遷到北京的商務印書館總部斷了聯系,但與由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發展起來的臺灣商務印書館仍維持了非常密切的關系,在那里出版了一些著作。
《先秦諸子系年》一書可以說是錢穆的成名作,也是他著力最多的著作之一。錢穆一生著述甚豐,但其著作,包括那些最有影響的著作,大多是課堂講義或演講稿,如早年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學概論》等,晚年的《中國史學名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文化學大義》《中國歷史精神》和《中國歷史研究法》等,都是如此。《先秦諸子系年》一書則不然。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作者為撰寫此書下了很大功夫,考證也非常細致。全書包括考辨專文四卷,計160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張。
前人考證諸子年世,多依據《史記》中的《六國年表》,然《六國年表》頗多缺失。錢穆通過研究得而復失的汲冢之《竹書紀年》,厘訂其今傳世本的錯訛,然后以此來訂正《史記》中的偽誤和注釋的抵牾,同時又遍考諸子之書,參證諸子之行誼及六國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參伍以變,錯綜以驗,定世排年,疏證細密。
本書原名《先秦諸子系年考辨》。《考辨》四卷與《通表》四篇一一相應,第一卷考訂孔子行跡與相關人物,第二卷考墨子、子思、吳起等,并辨老子其人其書,第三卷考晉、楚、魏、齊列國諸子,第四卷考春申、平原二君和荀子,至韓非、呂不韋。作者依次將先秦學術思想發展分為“初萌”“醞釀”“磅礴”“歸宿”四期。
全書自孔子至呂氏,各家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對先秦諸子的生平事跡、學術淵源、各家思想流變轍跡一一加以考定,持論有據,資料翔實。
碎紙屑里找出的陳寅恪手稿——陳氏一門三代手跡奇遇記
周越然先生的《書的回憶》中有一段話說:“做官有幸運,就是連升;經商有幸運,就是賺錢。購古書者,也有幸運,就是:(一)我要什么書,馬上買到什么書,并且價錢不大。(二)或者在冷攤上偶然拾得一種毫不相干的破書,歸來審察,發現某名士的印記,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書賈拿了奇僻的古本來售,索價不高,故留之。后來細作考查,知是海內外孤本。”周先生談到的三個方面的幸運,我都經歷過。別的不必說了,就拿2003年年末我偶得陳寅恪先生手跡的故事來說吧,那簡直就是想要什么,就會有人送上門來。
那年歲末的一個下午,快到下班的時間了,我接到經營舊書的朋友杜先生的來電,他說帶來一包手稿,已經到了我辦公室的樓下,請我下樓看看,如果我喜歡,可以賣給我,因他準備回老家過春節了。我馬上下樓,鉆進他的小轎車里,打開包書稿的舊報紙一看,原來是幾年前與我擦肩而過的馮承鈞先生所譯《蒙古與教廷》手稿。
《蒙古與教廷》是馮承鈞先生20世紀30年代所譯,撰者是法國的伯希和先生。由于各種原因,這部譯著直到1990年才出版。馮承鈞先生生于1887年,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通英、法、梵及蒙古文和比利時文,曾任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對歷史地理學有深入研究,尤長于中西交通史和元史。壯歲即患風癱癥,1946年卒于北京。馮氏著譯甚豐,主要有《中國南洋交通史》《馬可·波羅行紀》《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鄭和下西洋考》《帖木兒帝國》《吐火羅語考》等,《蒙古與教廷》亦是他的重要譯著。
馮先生所譯的《蒙古與教廷》這部手稿,和我真是有緣分。還是20世紀90年代中,大概是1995年或1996年,我和幾個倒騰舊書的朋友在一位趙姓書販的家里小聚。趙先生聽說我開始積攢名家手稿,告訴我說,他認識一個安徽籍的舊書販,手里有一部馮承鈞先生用毛筆書寫的手稿,如果我感興趣,可以叫他把書稿帶過來談談。我說,好啊,價格合適,馮先生的手稿我肯定會留下的。當即,趙先生約那個書販馬上到他家來。大概二十分鐘后,那個安徽人背著一個大布袋子來到了趙家。寒暄之后,知道他姓劉,因身材高大,圈內人稱他“大劉”。大劉帶來的書稿正是馮先生所譯的《蒙古與教廷》手稿。這部書稿共三冊,非常完整,確為馮先生親筆,于是開始談價格。那個時候,名人書札、手稿的價位都不高,我依照當時舊書市場通行的手稿價格,給馮先生的這部手稿出了個價,每冊1000元,三冊3000元(人民幣)。結果這個家伙腦袋搖了好幾下,嫌太少。我讓他開價,他“獅子大開口”,每冊2000元,三冊6000元(人民幣),并說已經有人給過這個價了。還說少于他開出的價,就不談了。我又提高了1000元,總共4000元,他依然不賣。老趙出來打圓場兒,我出價到三冊5000元,可這小子就是不給面兒。我也惱了,告訴他,不賣算了。
這件事兒,我早就給忘了。誰曾想,事隔幾年之后,這部書稿居然輾轉到了杜先生的手里。書稿原樣沒動,價格卻翻了個跟斗,杜先生一口價:人民幣10000元,沒商量。我沒猶豫,上樓取錢,下樓付款,取貨。為什么我會這么痛快地接受了小杜開出的萬元價格呢?時過境遷,進入到21世紀以后,名家書札、手稿的價格已是今非昔比了。杜先生給我開的價,其實是個朋友價,假如書稿依然在安徽大劉的手里,現在他開出的價格絕對要比小杜的一萬塊高出很多。
除了馮先生所譯《蒙古與教廷》手稿,杜先生還把隨稿帶來的幾封書信、殘稿等送給了我。晚上,我整理那些書信、殘稿時,有一頁發舊并有水漬的文稿引起了我的注意,字跡很像陳寅恪先生的手跡。我小心地拿起這張陳舊泛黃的稿紙,輕輕地把它放在寫字臺上,并小心翼翼地用鎮紙壓住,然后一字一字地往下讀:
馮先生譯文正確(譯文時有刪節,但無害于大意),又間附注自己所發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讀者。惟外國字原文之有符號者,仍多未移寫正確,將來付印時,似必須悉照原文一點一畫皆不訛誤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冊府元龜》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實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頗奇(伯君原文自謂不解‘道王友之語)。”殊不知“王友”乃唐時之實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稱,如《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云:“王府官屬:友一人,從五品下”之類,若一一悉為考訂改正,則限于目力,想有所不能也。
再往下讀,緊靠紙邊有幾個并不起眼的字:“寅恪謹注。六月七日。”
果然不出所料,這頁文稿確為寅恪先生親筆所書!這真應了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老話。陳寅恪先生寫下的這段文字,是在伯希和的文章《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中,收入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該文注五十七,寫有,“此文不言王玄策的實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頗奇”云云。那時,陳寅恪先生是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的委員。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胡廷。由此推斷,這頁文稿是陳寅恪先生在審讀《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時記下的。
陳寅恪先生的手跡,連同他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和其兄陳衡恪,陳氏一門三代的手跡,可以說是我集藏中國近現代文化名人手跡的重中之重。自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開始了陳寅恪及其乃祖、乃父和其兄衡恪(即陳師曾先生)手跡的尋覓活動。之后,我曾在一次拍賣會上見到過陳寶箴先生的手跡,但拿捏不準真贗,沒敢舉牌;陳三立先生的書札、對聯我見過幾件,但都“不開門兒”。后來在琉璃廠一個舊書鋪里看到陳三立先生的一副尺幅很小的對聯,價格不高,便買下了。一個朋友到我家里玩兒,看了這副對聯后,說“不好”。我的收藏習慣是,家藏的書畫、信札及其雜項等,凡是圈內人不看好的,我也拿不準的,就一定會送人或轉讓。既然朋友不看好這副小對聯,我也不是十分喜歡,于是我便把它送到一家拍賣公司賣掉了。據說競拍到這副小對聯的是上海的一個書商,他放出的口風是:經專家鑒定,這副對聯是真跡。直到我準備寫《舊墨三記》了,才在北京一家拍賣公司舉辦的古籍拍賣會上買到了陳三立先生的兩頁詩稿。說起我能競拍到這兩頁詩稿,還真要感謝收藏大家和宏明先生。那天的拍賣會我和他挨著坐,我舉牌的幾通書札,和先生也都舉牌參拍。對于那些書札,我并不十分在意,當價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也就不舉了。結果和先生一連氣拍到了好幾通。到了陳三立先生的詩稿開拍的時候,場上舉牌者不下十幾個,當然和先生亦為之一。一般拍賣會我很少去現場,大多是辦委托。我這次來拍場,主要是為了請回陳三立先生的詩稿。開始拍的時候,我并沒有上手,直到競爭者僅剩二個人的時候,我才始舉第一牌。這剩下的二個人,其中的一個,就是和先生。他看我開始舉牌,便問我:這個你要啊?我說,我有用。于是他不再舉牌。和先生的實力,我是清楚的,他這是在成全我。一件拍品,最后只剩下兩個人時,也就是到了決戰的時候了,這時拍品的價格也自然超出了物品的實際價格。最終我競拍到了陳三立先生的兩頁詩稿,將之收錄到我的《舊墨三記》的開篇。
實際上,陳氏一門三代的手跡,我得到的第一件正是陳寅恪先生的手跡。那是21世紀初,與人合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墨跡》一書的時候,我和一個經營書畫的徐姓朋友聊天,他說家里藏有陳寅恪和吳宓兩位大師的詩稿,并提出我可以拿書畫和他交換。我并不怎么收藏書畫,可家里也還有幾張不錯的畫。于是約好時間,我帶上那位徐先生指名要的幾張畫,到他家進行交換。遺憾的是,他翻來找去僅找到了陳寅恪的詩稿,而吳宓先生的手跡則不知被他的夫人藏到哪里去了。雖然如此,我還是將帶去的書畫全部給了他。詩是陳寅恪先生執教于西南聯大時,于1940年年初赴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議之后所作,詩云:“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據說,陳氏與會時,見到了蔣介石,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后來,我把這件詩稿收錄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墨跡》中。書出版之后,滬上有個藏友提出拿一件我更加需要的藏品與我交換陳氏的詩稿,我同意了。我當時想,偌大的北京城,再找一件陳寅恪先生的手跡應不是件難事兒。誰曾想,之后的幾年,盡管我費了不少心思,也沒有再見到第二件陳寅恪先生的手跡。直到我得到了前文所述的陳寅恪先生在審讀《六朝同唐代的幾個藝術家》時記下的文稿,才了卻了我的心愿。
我得到陳師曾先生的畫作,是我與友人徐先生交換到陳寅恪先生的那件詩稿后不久的事兒。那是陳師曾先生所繪的一幅國畫,畫幅不大,但卻蘊含著漢高祖劉邦醉斬白蛇和劉邦創作《大風歌》的故事。畫面上的草澤之中,一條紅蛇昂首向前,有所向披靡之勢,筆簡意饒,形態逼真,頗有意境,耐人尋味,顯露出典型的陳氏水墨畫風格。畫面配詩一首,曰:“赤帝白帝誰英雄,同是盤旋草澤中。夜深提劍偶然行,氣蓋山河歌大風。”雖然落款書“師曾戲筆”,并鈐有一“游戲”之印,但我們可從其題材的選擇中看到他獨特的筆墨趣味以及他對現實的思考,并對其所謂“文人畫”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選自《箋墨記緣—— 方繼孝的收藏三十年》/方繼孝 著/文津出版社/ 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