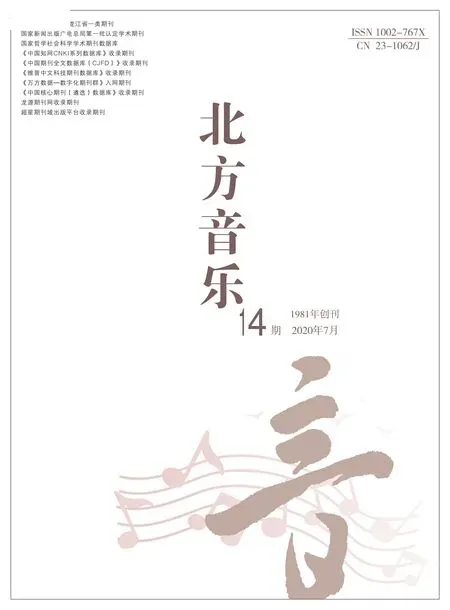淺談箏曲《西部主題暢想曲》的本體特征與藝術價值
王 穎
(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引言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古箏曲目根據一些特定的富含民族性的曲調進行創作。我們耳熟能詳的《西域隨想》《西部主題暢想曲》等便是這些樂曲中的一員。《西部主題暢想曲》(后文中我們將之簡稱為《西部》),這首箏曲問世后便迅速成為了古箏專業爭相學習的曲目。而當我們仔細研究黃忱宇、周望兩位創作者的創作傾向、專業方向后才真正了解到這樣一首極富民族風情又飽含傳統古箏樂器風格的曲目,其產生是兩位藝術家在其各自領域研究成果相結合的產物。
一、西部主題暢想曲的傳統性與民族性
在《西部》中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其存在的兩個特點:一方面是音樂創作中對于傳統的繼承,另一方面是全曲中新疆音樂元素的運用。
(一)《西部》所蘊含的傳統性分析
在《西部》中,我們能夠看到,在曲式結構中借鑒了木卡姆音樂的部分特點,就整體曲式結構而言,仍保留了大量的中國傳統音樂中變奏曲式的特點。如在一開始13小節的引子部分中(圖1)。

圖1
將前四小節理解為運用F(倍低音)作為旋律發展的“基點”,運用簡化的織體為主要形態,以左手單獨奏出,似層層疊加的前奏,為后續的展開起到奠基作用。
技法上依舊重視運指能力。同時,在指法設計上運用了撮、搖指、按滑音三種演奏技巧。故,創作者對于古箏的了解使其懂得如何使用這些專業技法在段落中進行發展,從而對音樂和情感進行細膩的刻畫和表達。另外,《西部》中大段采用雙手輪撮,在增強節奏感的同時將一種自由、廣闊的音樂展現給聽眾。
(二)《西部》民族性分析
《西部》通過人工定弦重新排列古箏音階。其定弦便是從典型的木卡姆音階而來,分為大乃額曼、達斯坦和麥西熱甫,每個部分又分為四個主旋律和部分變奏。正如前文所說,一開始的前四小節以F為基礎音進行發展。而在這首樂曲采用的典型木卡姆七聲音階中,也是以F為中心音進行排列的(圖2),同時能夠看到對稱性極高的排列結構,且富含民族性的增二度。

圖2
在新疆音樂中,我們也能夠看到一種在旋律上行時快速到達高音區,下行則是用相對緩慢的、同時進行三度以內的上升,形成一種下降中帶有上升傾向的級進音樂形式,如圖3。

圖3
二、西部主題暢想曲演奏技法安排與技法分析
在《西部》中,作曲家對演奏技法的安排和演奏者對技法的處理是兩個重要的部分。由于建立在箏的基礎體系之上,作曲家對演奏技法的安排更多突出了音樂本身的特點。而在演奏者對技法的處理上,是更多地結合了箏的演奏指法和技巧。
(一)作曲家對演奏技法的安排
前文中提到,《西部》具有新疆音樂中舞蹈性的特點。節奏方面主要表現在切分、附點等方面。在《西部》中左手聲部也采用了很多類似的、對手鼓進行模仿的伴奏,且這個伴奏往往采用切分音的形式;另一方面,附點節奏也是經常出現在維吾爾族音樂中的節奏類型,賦予舞蹈性的含義。這兩者在《西部》中的大量運用恰將新疆音樂作品的特點發揮了出來。
(二)演奏者對技法的處理
除了前文中提到過的撮,還有其他對整個音樂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的技巧。如點指,往往被運用在快速樂段中,所以需要演奏者保持相對的輕松的狀態和適當的力度,從而使音符的顆粒性在點指中得到體現。點指往往以雙手食指交替演奏,故作曲家在創作時多將其置于靈巧的小樂句中。
《西部》的引子部分采用自由演奏的方法,由弱到強,由慢到快進行演奏。慢板開始,古箏最先以右手搖指加左手低音區的大切分對位呈現,最終將歌唱性慢板的分句表現出來。在譜面上我們會看到很多強弱記號,音樂術語記號如抒情的、自由的等。但是在進行演奏時,完全按照譜面的要求進行處理會讓聽眾感覺到死板。故演奏者應該進行更加細膩的處理,如對樂曲進行劃分,增加樂句的獨立性和對比性,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理解進行二度創作。優秀的作品除音響效果外,其美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也值得探究。從音樂學習者的角度來說,美學價值的研究更利于演奏者的理解,而對于社會價值的思考,則會使作品本身的社會影響為人所知。下面我們便從《西部》的這兩方面進行討論。
三、西部主題暢想曲的藝術價值
喬治·迪基曾經以他的“慣例論”給藝術作品下了這樣一個定義:“人可以分作兩個向度:一是作為創作主體的人,一是作為接受主體的人。我們可以把對藝術品的界定或認定的客觀條件轉向人的主體的主觀條件。而某物之所以能稱之為藝術品是因為有人把這件東西命名為藝術作品。”
(一)西部主題暢想曲的美學價值
從作品本身出發,我們發現《西部》主題材料在不同音高上多次出現,這種主題的重復進行了修飾和擴展的不完全再現。作為本身就具備復調思維的一種樂器,古箏的復調思維也在樂曲中得到了展現。我們能夠看到在《西部》中對于小二度、增二度、增四度音程的強調,不只是單旋律的進行。這種復調思維在曲目中是不集中、片段化出現的,也正是這種對于復調的運用和處理,突出了音樂的特點。就音樂本身來說,這種將民族音樂與傳統器樂中本身蘊含的復調思維進行結合的創作手法,給予了聽眾極大的享受。
就作品的表演來說,當其問世時,這一作品就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傳播,并迅速成為了考試和比賽的熱門曲目。原因在于《西部》的音樂本身,單從演奏難度上完美地將音樂性與演奏難度達成了平衡,使這首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與演奏者在練習上的功夫進行了融合,深得演奏者的喜愛,便于音樂自身的流傳和推廣,這也就使其更容易作用于演奏群體進而影響音樂的傳播。
(二)西部主題暢想曲的社會意義
談到《西部》的社會意義,藝術家的職責是創作精神產品(藝術品)來滿足社會某一方面或某階層的特定需要,同時,這也是藝術家個人和社會進行情感交流的手段。在這里,我們單單將藝術價值中的社會價值這一部分作為一種必然存在,帶入《西部》中進行討論。
《西部》作為現代箏曲,其存在已經對古箏自身的發展進行了滿足。在滿足這種需求的同時,也滿足了人們當下對傳統音樂與各民族音樂相融合的需求。《西部》轉而將視野放在國內的各民族身上,將傳統古箏與民族音樂相結合,這種行為加深了民族自豪感。同時,站在國內的角度,關注到了民族音樂與傳統音樂的關系,并以傳統音樂為根基,抓住其他民族風格,從民間音樂中尋求發展。導致了古箏創作和發展形成了大致的三條道路,這三者都是建立在傳統音樂基礎上,分別以繼承傳統箏樂、結合歐洲音樂發展古箏和結合我國少數民族音樂發展古箏三種道路進行。
四、結語
箏三千年的歷史,逐漸到達如今的繁榮,各種風格的音樂也得以呈現在聽眾和演奏者面前。我們不得不意識到,當中國民族音樂向前發展,眾多音樂家面臨西方的沖擊時采用了各自不同的處理方法,從而產生了眾多時代造就的曲目。這些作品有著統一的特點,那就是立足于我國傳統音樂。這種對傳統音樂的繼承和發展,對于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有著怎樣的意義不言而喻。與此同時,應該怎樣在繼承中求發展,也是一個音樂學習者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