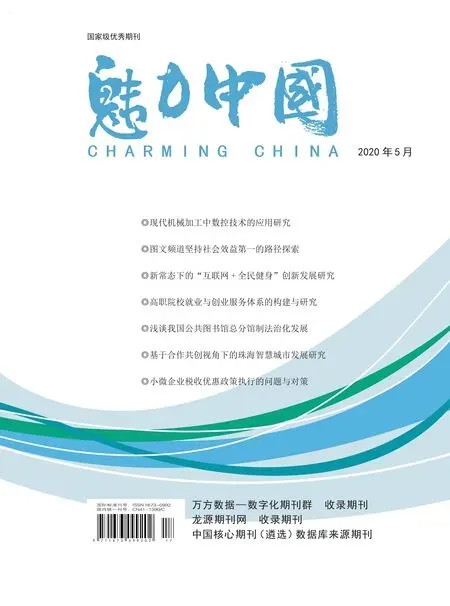在線協作學習中學習分析工具對教師干預的影響研究
(西華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中心,四川 南充 637000)
隨著現階段信息技術快速發展,“互聯網+教育”已成為一種較為常見的形式,在線教育應用越來越普遍。眾多學習者通過網絡平臺構成學習共同體,并通過網絡進行協作交流、接受教師指導干預,從而達到知識和能力增長的目的。但是在實際的在線協作學習過程中,常因為在線分組數量過多、討論信息過于多樣化等因素影響,使得教師難以及時有效的對學生做出指導和干預,進而影響到在線協作教學的效果[1]。而學習分析工具是基于大數據技術開發的輔助教學工具,對教師干預指導有著較強的輔助作用,教師通過收集數據信息能夠及時對學生普遍存在問題做出指導,從而提升在線協作學習的質量。現對學習分析工具的實際應用價值展開研究:
一、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主要選擇KBS-T 學習分析工具展開研究,該工具主要以大數據技術為基礎,深入挖掘在線協作學習人員知識加工、行為模式和社交關系三方面的數據信息,以此獲取在線協作學習人員的學習表現情況,為教師指導干預工作開展提供幫助。
研究選取50 名某師范高校教育專業職前教師作為研究對象,且所有研究對象對在線協作教學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對計算機教學技術應用有較為深入的認識。研究對象被平均分為對照組和試驗組,其中對照組人員未采用學習分析工具,有男生12 名,女生13 名;其中試驗組人員采用KBS-T 學習分析工具,有男生13 名,女生12 名。對照組和試驗組都在Moodle平臺上同時指導和教學6 組在線協作學習學生。在實驗過程中,以90 分鐘作為時間限制,教師發現在線協作學習學生需要干預時,及時向學生發出對應的干預信息。
二、研究方法
對所有教師全程干預在線協作學習學生的情況進行錄制,并記錄兩組教師干預的平均次數和教師干預的關注點,由此對比KBS-T 學習分析工具對教師干預產生的影響[3]。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數據信息都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19.0 進行處理分析。
三、研究結果
(一)對比兩組教師干預的平均次數
比較兩組教師干預的平均次數,其中對照組教師干預的平均次數為(38.35±2.34)次,試驗組教師干預的平均次數為(49.26±3.12)次,由此可見試驗組教師干預的平均次數明顯高于對照組教師,且二者之間差異明顯。
(二)對比兩組教師干預的關注點
從診斷、提示、解釋、指導、鼓勵、批評等方面比較兩組教師的干預關注點,具體如表1 所示。從表中實際數據可以看出,試驗組教師在干預關注點方面,提示、解釋、指導、鼓勵等方面的平均次數都明顯更高,而在診斷和批評掛這兩點上相對較少,且差異都較為明顯。
表1 兩組教師干預關注點平均次數(±s)(次)

表1 兩組教師干預關注點平均次數(±s)(次)
四、討論
教師在應用KBS-T 學習分析工具指導學生在線協作學習的過程中,其主要基于該工具對學生的學習行為做全面的分析,然后通過具體數據信息來進行呈現,從而便于教師采取科學的干預措施。從本次實際研究結果來看,KBS-T 學習分析工具對教師干預行為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
(一)高效診斷學生協作學習中存在的認知問題
學生在進行在線學習的過程中,在對各知識點的認知上必然會存在較多的問題,且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教師在傳統常規教學中,主要依據自身教學經驗,根據學生討論探討信息診斷學生在學習中存在的認知問題,在此過程中對教師的教學能力、教學經驗提出較高的要求[4]。而在應用KBS-T 學習分析工具之后,教師能夠通過觀察KBS-T 學習分析工具診斷的數據信息,然后采取對應的干預措施,不僅干預行為具有較高的準確性,而且干預頻率也能夠有效提升,及時對在線協作學習過程中的學生做出干預,從而有效提升教學的質量。
(二)促進教師掌握學生學習效果,改變干預行為
教師在對學生進行在線協作教學時,難以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并具有針對性的展開指導干預,是現階段網絡在線教學較為困難的一點。但是從當前KBS-T 學習分析工具應用來看,教師卻能夠通過該工具針對每組學生給予綜合性的評價,從而對各組學生學習中存在的不足之處采取針對性的干預措施[5]。例如:從本次研究結果來看,未采用學習分析工具的對照組教師,在對學生進行干預時,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診斷和批評上,形式相對較為單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干預的效果。而在應用KBS-T 學習分析工具后,教師提示、解釋、指導、鼓勵等行為明顯增多,而這些行為干預對在線學習學生帶來的幫助作用較大。
(三)促進教師對個體學生學習情況的掌握
學生在進行在線協作學習的過程中,以往教師干預往往更多的以小組作為單位,對各個小組學生做出整體性指導,很少針對小組內單個學生做出干預。這種現象主要受到診斷分析信息的影響,教師不能有效掌握各小組內學生學習情況,自然無法采取有效的干預行為[6]。而在應用KBS-T 學習分析工具之下,通過工具對學生整個學習過程中數據的采集,能夠有效獲知各小組內學生知識掌握情況,自然在干預行為上能夠更加準確,能夠基于學生情況做出對應的干預。
五、結語
綜上所述,在線協作學習中學習分析工具對教師干預行為有著較為積極的影響,在當前在線教學中,應當對此類輔助教學工具應用引起重視,以提升在線教學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