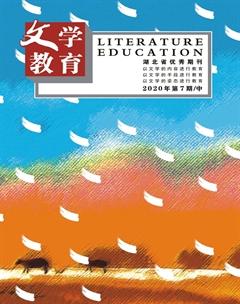詩與歷史真實性的比較研究

內容摘要:關于詩與歷史的真實性問題,亞里士多德于《詩學》中提出了和日常看法所不同觀點,即詩比歷史更真實。那么如何去闡釋這一觀點、比較二者關系離不開他提出的“摹仿說”。“摹仿”是西方美學史上關于藝術最早的定義,而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也回答了有關藝術起源的問題,所以文章將從其“摹仿說”入手,通過對對象塑造和情節編制兩方面的分析對詩與歷史的真實性進行比較研究。
關鍵詞:詩 歷史 真實性 摹仿說
詩與歷史之關系問題于歷代研究中當屬文學與歷史關系研究這一范疇,而文學與歷史也算是相愛相殺多年,諸多文論家對二者的地位問題爭論不止,但往往文學微居上峰。亞里士多德似乎也有重文輕史之意,在《詩學》第九章與第二十三章中,他談及了歷史,并將詩與歷史進行比較,論述了二者的諸多區別,在凸顯詩優越性的同時,他提出了一個極具思辨性的觀點“詩比歷史更具有真實性”。
何為詩?詩是詩人傳遞心中所想所感的藝術形式,它能夠通過語言去反映生活社會,建立起作者與讀者之間隱性的情感橋梁,以求得共鳴,這可以說是現實于文學中將其真實自身進行傳達的一種方式。何為史?梁啟超曾言:“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也。”這里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明確了歷史是對過去已發生事件、行為的記述與研究,這從內容上說明了歷史所載之事是有所依托的,這樣的一種依托性恰恰是其記述真實性的體現;二是提及了歷史對于后人的啟迪、反思功效,這是從意義上,以其影響的延續性反向說明了歷史及其價值的真實性。就從現代人普遍認可的詩與歷史的定義上來看,二者皆具真實性,只是這兩種真實性處于不同層面。
但對亞里士多德來說,詩始終高于歷史,他認為詩藝產生的原因之一是人的一種天性——摹仿的本能,通過摹仿人們獲得了最初的知識以及相應的快感。這種快感在人的精神上產生著積極的作用,也為所獲得的知識向更深層次的理念轉化提供契機。而相比之下,歷史所做的只是記述,這樣一種直白的記錄沒有闡釋的價值,人們通過歷史進行的知識獲取以“看”的形式便可直接達到目的,這阻礙了實踐經驗向形式理念的過渡。同樣都是以獲取知識作為最終目的,二者所采用方式的優劣便成為評判他們高下的重要依據。故而,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以歷史去抬高詩在整個古希臘文學與哲學上的地位。
對于詩與歷史的比較,亞里士多德主要從兩大方面來論述,一方面是對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是情節的編制。在對象塑造上,他提及了詩的兩大關鍵特征,“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和“表現帶普遍性的事”。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1]”因詩源于摹仿,朱光潛先生就在《西方美學史》中談到:“他(亞里士多德)的摹仿活動其實就是創造活動,他的摹仿自然就不是如柏拉圖所了解的,只抄襲自然的外形,而是摹仿自然那樣創造,那樣賦形于材料。[2]”因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四因說”,認為創造是制造者將形式賦予質料,使其成為具有規定性的存在。在這里,形式成為了摹仿創制的本質,它如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提到的,來源于藝術家的理性靈魂,是作為一種可能存在的,所以詩人將形式作用于質料體現出的“現實”超越了當下的時空限制,具有了隨著可然律和必然律發生變動的可能性與哲學性。相較而言,歷史則是質料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拘泥于對已經發生之事進行記述,處于一種“于事已然”狀態。這種狀態不需要多加修飾,融入諸多思索,相對于詩而言它只是具有個別意義、未經解構的物質材料,而詩要做的正是對原有歷史事件的解構與哲學層面認知的灌輸。
那么,詩可以描述已經發生之事嗎?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即使寫了已經發生之事,若這件事是合乎可然律,它就可轉化為可能發生之事,那么作家仍是作為詩人這一角色在進行創作。他在《形而上學》一書中曾提出過事物存在的方式無非現實與潛能兩種。已經發生之事顯然是以現實的方式存在,它是由質料在起著決定性作用,而質料作為構成實物的材料只能作為潛能存在,因為它和形式比起來并不具有具體的規定性。但他也認為現實是具有變化性的,它與潛能可以互相轉化,此時的潛能可能具備了成為可能發生之事的機制。由此可見,存在于現實事物中的潛能為事物的變動發展提供了可能性,而實現這種可能性需要的一定條件依然來源于“形式”。在之前的分析中我們知道形式是摹仿創制的本質,同時它也是事物的內在依據,規定了事物的本質,具有普遍性,那么在以形式為本質的摹仿作用下形成的詩也具有了普遍性。但詩的普遍性不是脫離個別一般獨立存在,詩人需要通過典型化的手法摹仿現實中的具體事物,然后通過具體事物的個性去反映出一般的普遍性,這便形成了與歷史“于事已然”所不同的“于理當然”的狀態。對此,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九章中談到:“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因為詩傾向于表現帶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于記載具體事件。所謂‘帶普遍性的事,指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某一類人可能會說的話或會做的事……[3]”這也就是說,歷史是對過去已發生的個別具體事物的忠實記錄,而詩人則致力于摹仿具有普遍意義的事,去揭示事物內在的本質和規律,這種摹仿中往往隱含了“虛構”的成分。與柏拉圖不同,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虛構具有積極的意義,它代表了藝術想象,也搭建了藝術想象與現實之間的橋梁。
就拿杜甫的《石壕吏》來說,詩歌描寫了安史之亂下石壕吏乘夜捉人征兵,連年老婦人都不放過的故事。這故事是否真實存在我們已不可知,但即使故事真實,詩人在對其進行描繪時增加了藝術渲染與細節強化,使得老婦的呼喊在虛構之下更顯得凄涼與無助,使得讀者去關注這呼喊聲背后安史之亂為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與封建統治者的殘暴。此時,虛構就起到了橋梁的連接作用,使讀者從詩歌藝術走入安史之亂這段真實的歷史,進而去體會戰爭所帶來的生命流逝與家破人亡,去流露對戰爭中人民苦難的悲痛與深切的同情。所以,這首詩描寫的早已超出了安史之亂本身,它找到了由其所輻射出去的人類苦難命運與憐憫通感的普遍性,而讀者也于其中找到了與作者、與歷史的共鳴。可見,在詩的創作中,特殊性與普遍性得到了統一,最后達到了人性的普遍性,詩的真實性由此體現了出來。與之相比,同樣是寫征兵,史學家僅僅只以“四處抽丁補充兵力”一句一筆帶過,將這一事件以客觀的形式進行敘寫,局限于已存在的事物,忽視了在其背后“于理當然”的事物。這種特殊真實的敘寫自然無法生發出具有普釋意義的結論,也就自然無法和詩普遍的真實性相提并論。
除了在摹仿對象上,亞里士多德將詩的真實性提升于歷史之上,在情節編制上,他對于詩的偏愛也是較為明顯的。亞里士多德認為詩的創作是一種情節的編制行為,情節所摹仿的對象是一個單一卻又完整的動作,它由起始、中段和結尾組成。它的開展要自然、合情合理,以達到內部的和諧整一性。但歷史卻不同,它需要涵蓋某一時期或是某個人物的全部事件。就拿中國史書最常見兩種體例來說,編年體史書是標準的以時間線索來記述的史書體例。它能照顧到整個歷史進程的方方面面,但其仍不具有整一性,原因即在于在一個完整事件或是人物早已被時間線切割地支離破碎。再來看紀傳體史書,一個人物一生的成長脈絡已相當清晰,但歷史時代的宏觀視角于其中漸漸磨滅,同一個人物于不同傳記中被反復提起,就像《高祖本紀》與《項羽本紀》中的劉邦與項羽,不同的敘寫側重,不同的性格塑造,歷史中的必然性也會有所蔭蔽。所以,在歷史求全的過程中,同一時間線上事件的繁雜與碎片化、同一人物身上的雙重性與其說是歷史的豐富性不如說是真實性的一種喪失。
再拿著名史詩《荷馬史詩》來看,在《伊利亞特》中,荷馬以一部劇作、一段完整的故事窺見十年戰爭的全貌,完成了起始、中段和結尾構建。這種高度的概括是生活的一種藝術再現,它無視了巨大的時間與空間跨度,展現了歷史的縮影,也對歷史進行了演繹。同時,完整的情節、典型的人物與深刻的思想也為讀者帶來了情感上的共鳴與道德上的教化,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二十三章中提及史詩時也說道:“史詩詩人也應編制戲劇化的情節……這樣,它就能像一個完整的動物個體一樣,給人一種應該由他引發的快感。[4]”這種快感源于人天性與詩作產生的碰撞,也是詩真實性的有力體現。所以在情節的編制上,歷史的真實性仍無法與詩的真實性相提并論。
所以,通過從對象塑造和情節編制這兩大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詩是詩人通過摹仿,把自己理性靈魂中的形式作用于質料,去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描述一個完整且合乎情理的可能發生的事,以此完成對事物本質與規律的普遍性的闡釋,這比僅僅記述經驗的個別事實的歷史要更具真實性。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一部分人認為亞里士多德對于歷史的看法完全基于日常的觀點,因而“詩比歷史更真實”這一觀點具有理論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無法否認在當時生產力較低的社會背景下,它的提出豐富了詩的內涵,將傳統的摹仿說上升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問題,為新的文藝美學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3][4][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1頁,第81頁,第163頁.
[2]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頁.
(作者介紹:鄒佳妮,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碩士在讀,學術方向為學科教學(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