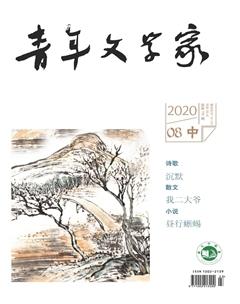從《胭脂》看張翎小說的結構、語言魅力
潘雨菲
摘? 要:《胭脂》是張翎的中短篇小說集,《胭脂》講述了三代女性的悲劇生活,而致使她們悲劇的原因大都來自于男人和社會。本文主要探究張翎的小說魅力在《胭脂》中的體現。
關鍵詞:張翎;《胭脂》;小說;藝術手法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3-0-02
《胭脂》分成了三個篇章——窮畫家和闊小姐、女孩和外婆、土豪和神推,小說的敘述視角也正是在這六個人物、六種身份、六個年齡段、兩種性別中來回切換。
這部中篇小說集給人的震撼不僅來自作者寫作時視角的靈活切換,也來自于其情節安排的巧妙。
小說的第一部分簡單交代了闊小姐吳若雅和窮畫家黃仁寬戲劇性的相識、相愛、相離。22歲的吳若雅由于拐錯了一個走廊而在病房里撞上了她命中的克星——一個憑著對色彩的敏感給她取名“胭脂”的人。命運在這部小說中是一個隱形的推手,他先是將吳若雅推進了黃仁寬的懷抱,又把她推進謊言的泥潭,最后使其一生吞食惡果,讓幾代人的命運陷入可怕的輪回之中。小說后兩部分著重交代了女主人公以及其后代的遭遇。
第二篇章先以孫女“扣扣”的視角描繪了祖孫二人悲慘的境地:孩子身份不明,撫養她的外婆靠手工業賺取生活費,同時單薄瘦弱的外婆還要和一些惡人作斗爭。以扣扣為視角的這部分敘述似乎讓讀者誤以為進入了新的故事,但很快作者便以外婆的口吻將我們拉回到先前她構建的故事圈中。原來外婆即是上文中的吳若雅,而扣扣則是其女兒抗抗的孩子。
命運弄人,抗抗出生時發出尖利的號角——“那聲音里帶著刀子”,有算命的婆子就說她命不好,所以若雅希望女兒能“抗一抗老天給她的命”。但抗抗并沒能抗住老天的捉弄,她悄悄地愛上了她的美術老師——一個有婦之夫,并與他發生了關系,最后因難產而死。像她的母親一樣,抗抗是被愛情的沼澤拖住了腳。
第二部分看似是在訴說兩個愛情悲劇帶來的后果,但給人感受到的還有惡劣的大環境給底層人民帶來的苦難。
貫穿第二部分的是“文革”這個大背景。作者在故事的敘述中時不時地提了“那些人”給周圍居民造成的恐慌——這是明線,那條暗線則是小女孩扣扣的病。扣扣幼兒時期,親眼目睹了“那些人”粗暴地闖進家門搜查以及外婆善意的提醒卻遭到了暴力逮捕的場景。上學后,扣扣怎么也長不高。外婆尋醫問診了多年,得出的結果卻只有“營養不良”。后來,外婆偶然發現扣扣發呆時作的詭異的畫——一個沒有五官的臉,喉嚨的地方腫了好大一個包。在一個學過兒童心理學的醫生的提示下,外婆似乎發現了扣扣的病根。
最后,在帶著扣扣親眼目睹了當年的“那些人”被打倒后,扣扣解開了心結。于是那個夜晚,她的骨頭開始生長。
小說中,張翎把那種有苦說不出、壓抑的痛抽象為孩子停滯的生長發育。于是小說在傳達控訴、憤怒的同時又多了一份揪心、殘忍,和一絲詭異。
同樣帶有奇幻色彩的筆法在小說的其他地方也能看到。比如第三部分中,外婆珍愛的寶盒丟失了,是外婆的夢引領她發現的;還有那詭異可怕的命運輪回——抗抗尖利的哭叫聲、扣扣頭頂的渦以及故事的最初,吳若雅和黃仁寬戲劇般的偶遇。這些情節雖然充滿著奇異、玄幻的色彩,但前后又都有著邏輯照應,讓人覺得即使不可思議,可是就得這么發展下去。
就拿吳黃二人的相戀來說。胭脂和那個窮畫家的感情真的只是由那個小小的錯誤促成的嗎?恐怕未必。
首先是胭脂的外貌。在黃仁寬的記憶中她的眼睛“眼白蕩漾著一抹淺藍,帶著一絲不諳世事的驚訝和好奇”。有著這樣一雙純粹的眼眸的人,她的內心也注定是純粹的。
胭脂說她決定留下來陪這個男人的原因純粹是出于憐憫,因為教會中學的一位嬤嬤告訴過她“世上最悲慘的境遇,莫過于一個人孤零零地死去。在世時的任何一種孤單,都無法和靈魂獨自上路相比”。一開始很難讓人信服,等到后來胭脂變成了母親,抱著女兒的遺孤準備去找那個作孽者時,她看到眼前幸福的一家三口,默默地放下了敲門的手;當胭脂變成了外婆,面對兇神惡煞的紅衛兵,她仍能關注到對方的傷口——即使因此被迫害,她也只是對著孫女嘆一口氣說“外婆傻,這輩子盡干傻事,總是為好心吃苦頭”。
這一切不得不讓人相信她的眼睛里至死都保存著那份純粹,同情她抱著救世的熱心和善良來到社會,得到的卻只是勞苦和拳腳;心疼她擁有一雙澄澈的眼睛,卻不得不飽受世間的污濁和不堪。
當然,善良和熱誠只是胭脂的一個面孔,促使兩人愛情悲劇的不僅僅是客觀環境的“明槍”,還有二人性格上的“暗箭”。
吳若雅和黃仁寬都是叛逆的,他們拒絕了父親給他們安排好的路,并喪失了家庭給予他們的幫助和關心。不僅如此,黃仁寬的家庭早年富裕時,父親是有許多妻妾的,母親還早早地將他與一起長大的鄰家姐姐定了親;同時吳若雅的父親也沒有給她合理的家庭教育,戀愛和婚姻都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他們身邊的愛情都是虛假而世俗的,而吳若雅的愛又來得太快太瘋狂。她出生于一個富足家庭,但并沒有富家子的紈绔,而是有著熱血和遠大的理想。在“生命猝不及防地撞到了一場意外”之前,若雅第一次忤逆父親是為了不在焦土上彈琴,可惜意志的脆弱占了上風——她享受著墮落,“體會到了墮落是一件多么容易又多么讓人心馳神往的事”,并且“在淑女和街婦的角色之間穿梭自如,毫無生手的無措和驚恐······”
而黃仁寬也并不完全是若雅眼里的那個“謙謙君子”,雖然一開始他總是拒絕著、推辭著,但一句浪漫的借口——“唯一能堵上胭脂心里那個缺口的辦法就是去害她”便麻痹了自己,讓自己心安理得地拖她下水。就像《傾城之戀》中范柳原月夜下那一個電話和一句“愛你”,浪漫的背后都是謊言。
再者,吳黃二人的身份差距過大,就像若雅說的“我每天帶進那個亭子里的大包小包,已經把他的自尊輾壓成一張稀薄的綿紙”,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么黃仁寬最終還是為了前程拋妻棄子了。這也正像四大古典愛情故事中演繹得那樣,如若沒有神助,存在巨大身份差距的男女主人公是無法于現實中在一起的。這樣看來,種種因素的共同作壞下,吳黃二人的“閃戀”實在是太容易被擊垮了。
然而小說中命運的可怕之處就在于,它不會輕易地放過每一個人:胭脂因為憐憫孤獨上路的病人而留下,最后自己卻是孤獨地離去;胭脂花了22年去愛一個男人,為了愛情與家庭決裂,最后還是被丟在了岸的另一邊;黃仁寬是因為那個“吻”的滋味愛上了胭脂,多年后,他們的孫女扣扣在五十三歲的年紀,因為一個吻而悸動。
第三篇章的開頭,作者以“土豪”的視角講了許多“不相關”的事,這些事多到像打開了另一個故事。后來“神推”扣扣出現了,把情節拉回到我們熟悉的地方,她生活的“平穩”似乎告訴我們命運的折磨終止了。可是結尾處,那一個“吻”留給扣扣的是悸動,那種心跳的感覺酷似她外公從她外婆的唇舌中感受到的;還有與“土豪”發生關系后的她在“羞恥”與“快活”中跳躍,扣扣是否也感受到了血液里流淌的外婆的沉溺于墮落的快感?這不是結束,這是命運開啟的新一輪游戲,扣扣終將卷進命運的齒輪中,她是朝熊熊烈火沖去的第三只飛蛾。
整部小說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每一階段的故事都由新轉舊地牽連前后的情節。像寫推理小說似的,作者會在前面先挖下一個個的坑,后面再用不同的技巧方法去填滿先前的“漏洞”。到最后,每一個人物都在兜兜轉轉中有了歸宿,他們的命運或在別人口中,或在作者筆下,或不經意從讀者眼中劃過地有了定數。這三代人的一生看似是從不同的起點出發,各自又在世界的軌道中留下了屬于自己獨特的痕跡,但最后卻是匯聚在一個終點上。這樣的情節安排讓小說在形式上構成了一個完整而又完美的“封套式”結構。
情節的跌宕以及“命運論”的設計讓這部小說的內容顯得豐富而充滿吸引力,同時作者的語言打磨也是小說的精彩之處。
在胭脂決定留下時,黃仁寬起初認為那是一種虛假的安慰——“惻隱是一根斷頭的線,甩出去很容易,收回來卻很難”;還有嬤嬤告訴胭脂的那句“世上最悲慘的境遇,莫過于一個人孤零零地死去。在世時的任何一種孤獨,都無法和靈魂獨自上路相比”;以及女兒抗抗向母親要錢時,作者總結“天底下所有的兒女在還沒學會說話時,就已經準確無誤地摸到了父母的軟肋”;包括扣扣讀完《紅樓夢》《西游記》后意識到的“賈寶玉不可能是石頭,孫悟空也不是。世上每一個人都有根,每一個拿石頭來說事的人,其實都在掩藏一個有關身世的可怕秘密”······
這些句子總是含蓄又細膩,并且把我們平時所感受到的用精準的話語表達出來。在這部小說集收錄的另外幾篇小說中也有同樣的體現:
“手機活著,他就活著。手機死了,他就成了個四面是水的孤島,連岸的影子都找不到。連著他和世界的那根線突然斷了,他便晃晃不知如何是好。”這一段說的是《都市貓語》中男主人公張茂盛獨居城市中的生活狀態,描繪的與我們現在的生活現狀也是及其相似。同時,作者張翎還在小說中使用了些許網絡化意義的詞語(如“小鮮肉”“土豪”),像是拿了一把時代的放大鏡,也拉近了與當下讀者的距離。
張翎的小說情節安排巧妙,語言精美準確,但在多個小說的對比下,還是讓人有一絲“重復”性的套用感。
比如《都市貓語》中寫到主人公的父親毫無預兆地死去,“頭天晚上還在跟人大呼小嚷地喝酒猜拳,第二天到了中午也不肯起床,一摸,已經渾身冰涼”;這一情節在《心想事成》中也有描寫,“你爺爺沒了······昨天晚上還跟你爸喝了半斤米酒,早上一摸,冰冷鐵硬了”;還有《胭脂》里外婆夢到盒子丟失,和孫女尋找后果然噩夢成真······這種“毫無預兆”“莫名其妙”式的情節不免讓小說的現實性中增添一絲奇幻詭異的色彩。尤其是在《心想事成》這篇短篇小說里,作者為了讓主人公“心想事成”,有些刻意地讓事情都像她說得那樣發展。如果是為了強調諷刺性,巧合的“合理性”“邏輯性”應該也要納入理性思考的范圍之中,否則便會讓讀者覺得有一種脫離現實的荒唐、詭怪。再說,《胭脂》的第三部分中“土豪”的回憶里出現了另一個“胭脂”,這個“胭脂”與吳若雅是沒什么關系的,包括“土豪”這個人物也是嶄新的。如果不是暗示著新的故事的開始,那么這幾個人物的出現是否也存在些許邏輯漏洞呢?
讀完《胭脂》,小說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五個關鍵詞:母親、眼睛、命運、孤獨、男人。小說中三位女性都經歷了母親這一角色,她們都是獨行的、孤獨的,她們的命運都與男人有關。將這一切串聯起來的是作者情節安排上的“天羅地網”以及精準細膩的語言。
張翎在人物的刻畫上,尤其是女性角色,非常的細膩獨到;在人性內涵的深刻性上,作者也在故事中進行了探索;除此之外,張翎的語言風格總是能讓讀者擁有穿越時空般的快感,她能把古典韻味與現代氣息、中西方文化完美融合,具有巨大的時空跨度和史詩般的追求。
參考文獻:
[1]胡德才《論張翎小說的結構藝術》,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