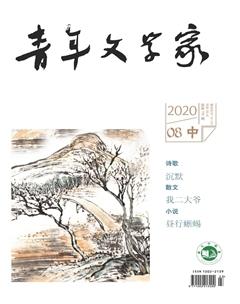千古文章未盡才
摘? 要:本文以仔細閱讀文本為主要研究方法,著眼聞一多先生已成的《紅燭》、《死水》兩部新詩實踐代表作,結合作者生平經歷、詩歌理論主張,從詩歌構思、修辭、語言三方面入手,試對聞一多先生詩集形式技巧進行不同方面的分析。
關鍵詞:《紅燭》;《死水》;聞一多;形式技巧
作者簡介:李明曦(1998.8-),女,漢族,遼寧朝陽人,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2017級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3-0-02
引言:
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聞一多是文藝研究者繞不開的學術重點。以學者、詩人、民主斗士三位一體的他,一生在詩的國度里大放異彩,不僅寫下大量膾炙人口的詩篇,提出許多富有見解的詩歌理論,更是數十年在“故紙堆里討生活”,開展古詩詞研究考證。其中,先生作詩的才學最為人稱贊,他的詩歌形式獨特、技巧多樣。前人對其詩歌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內容情感方面,較少涉及形式技巧。也有對詩歌藝術手法的相關研究,大多是對“三美”理論的研究和闡發,也有其他方面的論述,但不是特別突出。[1]筆者在仔細閱讀文本后,意圖從讀者接受角度,分三個層次具體表現聞一多詩歌獨特的形式技巧。
《紅燭》、《死水》是詩人青年時期相繼出版的新詩集,是我國現代新詩里璀璨的明珠,得益于詩人卓越天賦以及孜孜不倦地讀書進益,兩部詩集藝術特色突出,想象瑰奇,意象豐富,構思巧妙,將中西文學藝術精華薈萃其中,值得仔細探尋其中奧妙。
一、別具一格、新穎獨特的詩歌構思
詩歌的創作,在詩人真切地經歷現世或欣喜或悲慘的事件、詩歌素材積淀完成、內心因“物不得其平”情感亟待抒發后,就把一切都交給了構思。構思是文學活動的重要一環,好的構思能將詩人情感思想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從而使讀者接受更好的閱讀體驗。聞一多詩歌形式技巧的卓越離不開詩人獨具匠心的構思。
聞一多的構思不是逍遙于天地之間,隨心所欲、天馬行空般的任意起始接續,而是依據所寫內容特點進行嚴謹的連接。《紅燭》詩集的開篇《紅燭》就是一個典型例證。這首詩以蠟燭為歌詠對象,一開篇就突出紅燭意象紅色的特點,由顏色之后,又從紅燭所制材料—蠟和用途—照明寫起,最后依據紅燭燃燒時必然要“流淚”的情狀和最后燒蠟成灰的事實來表達主旨。詩人的構思由表及里,由始到終都是依據現實事物特點來寫,是將來源于生活的內容有邏輯地層層描寫和揭示。
這種獨特的構思方法,除了嚴謹的連接式描寫之外,更重要的是所選取的對象本身完全地與要表達的思想主旨相一致,這非常難以做到。讀者讀后往往驚嘆聞一多詩歌意象選取的巧妙和意象與主題的貼切。還是以《紅燭》為例,這首詩主要是對像紅燭一樣自我犧牲以拯救同胞,努力奮斗以創造光明的理想人格的塑造歌詠和欽佩贊嘆,表達了詩人熱愛祖國和人民,毫不顧惜個人榮辱得失,不懼奉獻和犧牲的精神。而紅燭這一意象就是這一精神最貼切的生動說明:紅燭的“紅”象征著此類人格的赤子之心;蠟燭燒蠟成灰以放出光明,就是其自我犧牲和努力追求光明的表征;而在放出光明過程中,蠟燭的“流淚”也象征著追求前行過程中此類人格必然要經歷種種痛苦與磨難,絕不是一帆風順的過程。
聞一多高超的構思能力還體現在詩歌中運用強烈反差以取得更好的表達效果。一類是化丑為美,在聞一多的詩篇中,《死水》正可作為化丑為美的藝術創造的例證。[2]《死水》中詩人集中筆力描繪出“一溝絕望的死水”:其本來面貌必是骯臟的、腐敗的、雜亂的、惡臭的,不堪入目,人皆掩鼻而過,但是詩人卻將銅綠形容為“翡翠”,銹斑說成“桃花”,油膩化為“羅綺”,霉菌生出的是“云霞”,臭水升華為“綠酒”,灑滿“珍珠”似的白沫,有花蚊偷酒,有青蛙唱歌……①“死水”被詩人竭盡美化之能事,給丑惡披上了美麗的外衣。強烈的比對既突出丑惡的可惡,又成功地給予詩歌藝術美。一類是以美襯丑,在《口供》中,詩歌后兩節與前面內容的截然相反,突出詩人人性矛盾復雜的好壞兩面,體現出詩人自我反省、自我解剖意圖。
二、想象豐富巧妙 意象充斥其中
想象為詩插上強有力的翅膀,是詩歌不可或缺的詩歌要素。聞一多的詩歌就充分體現了詩人想象豐富奇妙的特點。想象的豐富就必然伴隨著意象的運用,而運用意象則是為象征做準備。兩部詩集中幾乎每一首詩都有重幻象、意象、暗示、象征的痕跡。
要探究這一特點,不能不提及《紅燭》中的《劍匣》這篇詩歌。通篇都是奇妙的想象,是一個虛構的故事,是詩人“夢的原稿的影本”,是“閑惰蕪蔓的花兒開出來的”。詩人幻想著“生命大激戰”后,將暫時安身修養之所想象成一個“絕島”。既然是孤島,四周被大海環繞,杳無人煙就是潛在的環境,營造出一個孤寂的氛圍。詩人想象用“象牙”“墨玉”“金絲”“瑪瑙”“魚子石”“珊瑚”“翡翠”“藍珰玉”“紫石瑛”“螺鈿”等材料制作劍匣,制成了一件鏤金錯彩、工藝復雜、圖案精美的作品,上面有著白面美髯的太乙臥在粉紅色的荷花瓣里,駐著裊裊的篆煙的雷紋鑲嵌的香爐,肉袒的維納斯,三首六臂的梵像,在竹筏上彈著單弦的古琴的瞎人。②種種意象的堆積羅列,體現出詩人想象的豐富離奇。給讀者營造出一個神秘奇異的世界,讓讀者不知不覺跟隨詩人的詩歌節奏,一步一步見證著美妙精致、富有魔力的劍匣制成,而詩中人嘔心所做的藝術品竟然是長眠其寶劍、用以自殺的所在。詩人在這里建構美與美的極致,最后竟是為自我精神的消解尋找墓地,前后反差巨大,是作者運用大篇幅想象的結果,給詩歌增加了奇妙的藝術魅力。
聞一多在詩歌創作中亦多用象征和暗示,有在詩的局部運用,也有整體象征,如《淚雨》、《黃昏》、《末日》、《夜歌》、《死水》、《聞一多先生的書桌》等。故詩歌含蓄蘊藉,富有特殊的藝術吸引力。《淚雨》里以不同年齡層次所流的淚,象征了人生步履之艱辛和悲苦。《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以諧謔的筆調,寫出那些墨盒、信箋、香護、筆洗等等靜物的抱怨和牢騷,它們自認為得不到自己應有待遇,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在混亂和顛倒的現實中受盡委屈。此詩表面上可以解釋為反襯聞一多潛心于文化學術研究工作,專心致志,廢寢忘食的精神,但是包含著更深層次的象征義。那些用具們最終是同聲罵道:“什么主人? 誰是我們的主人? ”“生活若果是這般的狼狽,倒還不如沒有生活得好。”③這里不就已經升華成一個社會了嗎?一個社會的人事如果不能各得其位,多么糟糕和可怕?詩人已意識到這一現狀,但是他無能為力,他明明白白地說明“秩序并不在他的能力之內。”④象征的運用,不僅讓詩人淋漓盡致地抒寫心中五味雜陳的情感,也增加了詩歌含蓄蘊藉的表達效果。
三、用詞豐富生動貼切? 用語中西結合
聞一多先生家傳淵博,自幼愛好古典詩詞,13歲便考入北京清華學校深造。后又赴美國留學,廣泛領略異國文化。他曾學古詩并寫古詩,后來轉而創作新詩。可以說聞一多先生受到中西文化濃厚的熏陶。
這種獨特的經歷,使聞一多先生詩歌用詞豐富生動,能夠貼切地表現詩歌意蘊,并使意蘊或更含蓄雋永,耐人尋味;或更直切辛辣,直指人心。在詩中用語造句細心打磨雕琢,用語新奇,多有詞語運用的創新之舉,故增添了詩歌的藝術魅力。在《紅燭·記憶》中,詩人第一句這樣寫道“記憶漬起苦惱的淚”⑤,一個動詞“漬”用得新奇,用得貼切。“漬”意思是浸泡、漚意,生動地寫出詩人一開始回憶就會苦惱痛苦地落淚。回憶中浸滿苦淚,流淚是記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在《紅燭·我要回來》里寫“你”的心靈像“癡蠅打窗”,此短語的運用富有新意,不用以往形容幼童諸如天真爛漫等形容詞,用蒼蠅打窗鍥而不舍的事實展現出兒童內心的純真質樸和天真無邪,塑造出一個美的圣潔形象,使詩人不顧一切地投入到愛的追尋當中。詩人佳句好詞不斷,《死水·發現》中,詩人“迸著血淚”,在發現是“一場空歡喜”后,“追問青天,逼迫八面的風,拳頭捶著大地的赤胸”一系列詞語的運用鏗鏘有力,將詩人對祖國現狀失望與悲憤這一難以言說的痛苦展現得淋漓盡致。
聞一多先生詩歌語言體現出明顯的中西結合的特點。他說: “我們主張以美為藝術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東方之義山,西方之濟慈了。”⑤兩部詩集采用的都是西方傳入的句式和語法,是典型的中國現代新詩。聞一多主張在“新詩中用舊典”,他這個主張是出于熱愛祖國傳統文化,不忘歷數家珍以夸耀于世。[3]諸如《紅燭·春之首章》中“像一頁淡藍的朵云箋,上面涂了些僧懷素底鐵畫良鉤的草書”;《紅燭·紅荷之魂》中“是千葉寶座上的如來,還是丈余紅瓣中的太乙呢?《紅燭·億菊》中“啊!東方的花,騷人逸士底花呀,那東方底詩魂陶無亮,不是你的靈魂的化身罷?”都有典故的引用,這種運用將典故內蘊與詩的主題和詩意渾然無間地結合在一起。他的用典意義清晰,典與詩意不僅溶化且起著襯托的作用,使詩意更為明朗豐滿。在《死水》中也有受古典文化影響后形成的特點,如附錄《奇跡》里“婉孌”“藜藿”“閶闔”“綷綵”等古典用語。
結論:
綜合分析后,我認為《紅燭》、《死水》形式技巧主要有三個層次:一是詩歌新穎獨特的構思;二是豐富巧妙的想象,象征的大量運用;三是用詞豐富生動貼切,語言中西結合。聞一多先生作為近代中國文學史上較早學寫新詩、闡明新詩創作理論的文學家,其對中國新詩發展的貢獻不可小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注釋:
①聞一多:死水[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頁.
②聞一多:聞一多大全集·詩歌卷[M].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③聞一多:死水[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頁.
④聞一多:死水[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頁.
⑤轉引自鄺維垣:論聞一多新詩的藝術風格[J].暨南學報,1983年(8).
參考文獻:
[1]吳滿珍 李秋蕓. 最近30年聞一多詩歌研究綜論[J].江漢論壇,2009年(8).
[2]何佩剛. 聞一多詩歌創作對現代派技巧的汲取[J].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5).
[3]鄺維垣:論聞一多新詩的藝術風格[J].暨南學報(哲學杜會科學版),1983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