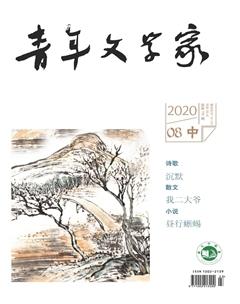論葉多多文學創作的意象呈現與美學追求
摘? 要:在葉多多的作品中,意象的表達承載了作者對表現邊地之美的追求。意象是主觀抽象的“意”與客觀具體的“象”的統一體。根據作品中作者對“象”的感受以及“象”的特征,可將主要意象概括為地域意象、民族意象兩種類型,代表意象為雪山、峽谷、森林以及火塘。意象與意象之間的內涵沒有絕對的界限,作者表達自然美、人情美的創作價值取向在意象與意象的融會貫通中得到凸顯,給予讀者“視覺”與精神上的雙重美感享受。
關鍵詞:葉多多;意象;文學創作;美學追求
作者簡介:張一鳴(1998-),女,湖北省襄陽人,云南省大理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3-0-02
葉多多,昆明回族作家,當代云南少數民族代表作家之一。歷任宣傳干部、記者、編輯。出版《我的心在高原》《瀾滄拉祜女子的日常生活》《美麗不需要結尾》《邊地書》等多部散文集、小說集。獲第十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眾多獎項。她的作品多數以非虛構散文的形式,生動地呈現出云南少數民族生活圖景和游歷過程中非凡的見聞,作品中意象的刻畫體現出紀實性與文學修飾相結合、情感與想象相交織的特點,成就了作品深厚的意蘊與視野的廣闊性。
一、“雪山”意象,圣潔崇高
在葉多多的文學創作中對標志性地域景觀的描述表現了云南山地的人文景觀、地方特色,承載了地方經驗、歷史記憶同時展現了自然生態之美與當地人民面對自然與生活的態度。
雪山意象是作家作品中典型的包含著矛盾的意象,它一方面圣潔而富有光輝,另一方面充斥著未知與災難從而襯托出人精神的崇高性。短片《遙遠的雪山》——與牧人仁青合作拍攝的劇情短片,主角碧落雪山在作者心里是沒有渣滓的純凈的光,在這種光的沐浴中童真得到顯現,表達了人的真誠和對原始的依戀。碧落雪山若是單單立在那里,也只是簡單的一座雪山而已,因為有了翻越它的決定,才有了后來筆下與它相關的人、事、物的模樣,也即有了“改造”,地域景觀變得更生動,更有人文色彩,也為作者的創作提供生成的空間,滿足了“情景交融”這一中國傳統美學給予意象最一般的規定。
碧落雪山的另一面:難以攀登,神秘,陰森,像一面鏡子,讓人看到自己的渺小與生命的脆弱。攀登雪山的路途中,作者目睹載著四個男孩的越野車滑下懸崖后,產生了對人生的疑惑,意識到了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無意義。災難對于山地人民來說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災難的旅程上,理性思維與習慣已經無法判斷和衡量,生命似乎隨時可以消失。在翻越碧落雪山見到路上的森森白骨時,她感嘆這是宿命和前定。這其實正是在認識到人的力量的微弱后,依然不懼與時間里的一切和諧共處的決心,是精神之崇高。美的效果,不依賴于愉悅與快感的產生。大自然的氣勢磅礴如詩如畫帶來的自然美、山地人民溫暖美好的人情人性和命運的困頓中不屈服的精神帶來的人情之美,都昭示著作者對作品審美價值取向的明確表達,也成就了碧落雪山這一意象帶給讀者的豐富的審美感受。
二、“峽谷”意象,雄奇險峻
葉多多的散文中多次出現“峽谷”意象,表達了自然美與人情美相交織的精神內涵,雄奇險峻的峽谷成就了人們正視苦難的勇氣。
如果說翻越雪山或在阿佤山生存是對自然景觀物質上的“改造”,那么文人意識的附加則是精神上的“改造”。“移情”是這一過程里最重要的心理基礎。希臘建筑的多立克石柱本是無生命的大理石,然而在觀者眼中它們卻顯得“有生氣、有力量,仿佛從地面上聳立上騰,這就是移情作用”[1]多立克石柱的姿態喚起了人們毫不屈服的人生記憶,正如回憶里的怒江峽谷,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意義而不是簡單的物理存在。它向世人訴說真理,像一個童心未泯的人。怒江峽谷在審美活動中與人性的東西、生命的東西相關聯,這正是作家對怒江峽谷的自我意識的投射,也可以說怒江峽谷內在的審美屬性被審美主體所喚醒。
怒江峽谷風景描述部分相當經典,作者著重描寫了多種色彩交織造成的視覺沖擊。山、天空、大地都融合成“肆無忌憚”的青黛,大地上一種顏色壓住另一種顏色,重重疊疊,視覺上的不和諧反而制造出令人愉快的效果。自然美的呈現,不一定依賴于鏡頭的記錄,甚至不需要感受者親身接觸美的對象。作者致力于營造一種讓讀者“親身感受”大自然之美的氛圍。就像葉多多筆下的怒江峽谷,無疑為讀者提供了再造想象的基礎,靜心感受,高原的險峰奇石、花草樹木、活潑生靈就躍然紙上。作家對高原的景色有著自己獨特的認識與表現方法,所以當景致被抽象化成為文字時,它的美也絲毫不會被剝奪,反而添上了縷縷精神芳香。作家通過語言技巧“將由意象組成的畫面直接訴諸人的視覺,從而使得意象得以具象化呈現出來。”[2]
峽谷意象同樣有展現人情之美的一面。瀾滄江大峽谷極目所至,一片荒涼,高原上的一切都是兇猛的,雷霆暴雨會在大地上肆虐,遷徙的路途充滿未知和變數。不易的高山峽谷生活造就了各民族獨特的審美意識,殘酷的生存環境沒有剝奪人們生活的勇氣,他們在單調的生活中發現美好,繁衍出生命的歡歌。這即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顯現,是關于崇高的精神美表達。
三、“森林”意象,幽深茂密
“森林”意象多次出現在作品中,表達了作家的堅定的生態理念。冷杉和硬闊葉林,是高海拔地區的名片,它們像那里高大、威猛、強悍的民族一樣,給人“披麾掛劍、刀槍林立”的威嚴感。兩千八百米海拔以下的云南松,在葉多多眼里則像秀麗、優雅、不失風度的思茅人,可見云南高原森林的地域特色。糯福的森林冒著油的綠色給人一種無法言喻的快感。它有著與世無爭的美麗,給人幸福、懶散的感覺,同時它又十分神秘,懵懵懂懂的才能轉出來,可見云南森林幽深茂密的特點。
此外,在《我的心在高原·陽光下》這一章,描寫了一位在森林中生活的老人——老扎俄。他對森林了如指掌,與森林相依為命。扎俄打獵生涯結束于誤把妻子娜蕾當作獵物麂子射死。這部分的寫作手法很有玄幻意味,凡是讀者定會好奇扎俄認定要捕到的獵物如何突然變成了娜蕾。這里給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這發生在森林中的故事,讓從前身為獵手的扎俄和來自森林外的作者都開始反思,干預動物的生活是否是正確的決定。
這些地域意象中的“地域”不單指某一高原或山川峽谷,也包含著“從現實繼承的、理解與想象的空間”[3],蘊含著作者在觀察這一空間時的感受、情緒、主觀的情境認識與價值判斷。它們作為地域景觀的自然存在狀態既因為自身的地理位置容易引起關注,又能作為審美客體給審美主體帶來心理愉悅。這些意象呈現的核心可歸納為“生態性”。葉多多曾表示自己的文字讓生命“蓬勃而豐沛,輕盈而美麗”[4],這得益于創作時一字一句所傳達出的“生態性”,不只是傳統意義上文學創作對環境保護表現出的重視,而是一種作者作為高原生活的親歷者表達出的對高原生命由衷的敬畏與贊嘆、一種從自然汲取力量的感恩之情。這種生態性具體表現為對自然生態的欣賞和保護意識,通過挖掘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資源,增強人們對自然的敬畏感。其作品中鮮有對人們生態倫理觀上的說教,卻潛移默化地促使讀者思考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失衡導致的現代性危機,以及如何面對這些危機。
四、“火塘”意象,熱鬧歡樂
以火塘為代表的民族意象為葉多多在游歷過程中進行審美活動感受到的蘊含民族精神的物象審美,它們與山地少數民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展示了少數民族人民在生活中關懷自身、關懷命運與自然的獨特生存美學。
火塘是作為作品中民族符號而存在的意象,它們代表了民族的信念與希望。
在拉祜族漫長的遷徙和生活中,火是永遠不會熄滅的。生活在深山里的游獵民族拉祜族的大部分勞作是在與自然作斗爭,他們仰仗刀耕火種技術。火塘承載了拉祜族人民一代又一代的共同記憶,拉祜人的歡樂很大程度來自于它,一方面火的溫暖驅走孤獨,另一方面相關習俗塑造了拉祜人的歷史。即使隨著現代化生活的到來正在消失,但它作為拉祜族民族意象是永不寂滅的,永恒燃燒于見證者的回憶中。拉祜族人民熱衷于在火塘邊載歌載舞,在豐收以及闔家團圓的日子里,他們在圍繞著火光唱起古歌,跳起民族舞蹈。與之息息相關的古歌是拉祜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家認為古歌是拉祜人永生不滅的靈魂,是文字不發達時歷史相傳的重要途徑,印證著時間和空間的無限延伸性。此外與之相伴的拉祜族舞蹈和蘆笙,都是拉祜人獨有的精神寶藏,隨著火塘的光芒也溫暖著作者與讀者的心。
從以此為例的民族意象可以看出作家鐘情于少數民族的生命氣象,著眼于云南少數民族聚居的山地,“她以一顆深深憂民的心將少數民族群眾的貧窮與落后面貌展現在了讀者面前”[5]。表達了作者對關于人們在現代文明面前該何去何從的問題的思考。
綜上所述,葉多多在散文中書寫邊地云南時使用了豐富的地域意象、民族意象,其中不乏對各類標志性自然地理風貌的直觀感受、對少數民族特有習俗的轉述,顯示出作者獨到的審美經驗以及文化與文化、價值觀與價值觀之間的交流與碰撞,表達出對自然美、人情美、生命美的追求和對現代文明的思考。她是少數民族窮苦人民的幫扶者,也是云南邊地的記錄者、歌頌者,為讀者打開了一個觀察邊地高原人民、景觀甚至苦難的新視野。我們從中看出了葉多多對少數民族文學要表達生態性以及健康美學導向的執著以及最佳實踐。
參考文獻:
[1]立普斯.論移情作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3.
[2]于興財.《生命之樹》的意象呈現與美學效果[J].電影文學,2016(17):133.
[3]潘泠.漢唐間南北詩人對地域意象的不同形塑——以《樂府詩集》為中心[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5:18.
[4]葉多多.時代呼喚生態的民族文學[N].中國藝術報,2013-12-13(003).
[5]高傳峰.新時期以來云南回族文學發展概述[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0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