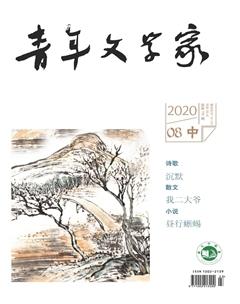《比目魚》奇幻原則視域下的啟蒙思想透視
摘? 要:君特·格拉斯是在世界文壇上都頗有名氣的作家。他早期創作的“但澤三部曲”成為人們家喻戶曉的名篇。作為“德國的良心”,他看到了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并努力在自己的創作中貫徹這一原則:“針對流逝的時間寫作”。在其創作生涯的中期,他開始將目光聚焦在全球的熱點問題上,比如:暴力,貧困,環境的污染。縱觀格拉斯的整個文學創作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啟蒙性一直都是作者在作品中想要表達的主題。可以說,它成了解讀格拉斯文學作品的一條重要的“紅線”,《比目魚》這部作品自然也不例外。本文就試圖從其外部結構和內在的內容入手探討小說的奇幻性原則,接著以此為框架來討論小說的感性啟蒙的形式和特點。最后結合德國浪漫派小說家的相關文學理論來探究格拉斯的感性啟蒙的目的:重歸母性神話。
關鍵詞:《比目魚》;奇幻原則;啟蒙性;母性神話
作者簡介:張弛(1995.8-),男,安徽池州人,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3--02
1、小說中體現的奇幻性
如果我們仔細品讀《比目魚》這部小說的話可以發現,這部鴻篇巨制處處充滿了奇幻性的色彩:那條象征著世界精神,具有淵博學識的比目魚,它會說人話,既通曉歷史又能預知未來;在小說虛構出來的歷史中,“我”作為歷史的敘述者和直接見證人,具有長生不老的特殊功能,能根據小說情節發展的需要沿著時間的階梯悄悄“溜走”,與各位廚娘上演著一幕幕的兩性關系史。
格拉斯在其一生的文學創作中非常重視童話,神話等因素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他認為,這些文學體裁屬于人類童年時期最樸素的文學形式,通過擬人,象征和隱喻的藝術手法,線性時間的共時性的排列,對人物形象進行特定的藝術加工,使讀者能進入到那種特定的故事情境中,讓一種超驗性的因素進入到平常的文學闡釋中,這逐漸消解了想象和現實的距離,使二者渾然一體,在主觀想象中包含了現實的因素,甚至在這種審美的想象中包含著比現實更為真實的“真實”。對于這種文學手法的運用主要是源于其荒謬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世界是荒謬的,因此不存在一個絕對的真理性的認識來解釋世間一切現象,而只能通過像神話和童話這種感性的文學形式來進行思想上的啟蒙。從小說的外在情節的組織特點上來看,這部小說也有著區別其他小說的特點:小說《比目魚》沒有按照一條完整的時間線索來組織情節的發展和人物的活動,出現在小說中的各種形象也不是靜態的,只是單純受制于作者情節展開的需要而在一定的范圍內活動,他們有著自己獨立的思想和心理,并積極通過自己的言行來影響著歷史的進程。整部小說就是在眾多的情節線索交織下由多重敘述聲音組成的“復調小說”:小說中出現了眾多獨立的聲音和意識,它們之間彼此進行著平等的交流,通過這種相互聯結和相互作用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比目魚”這一形象成為了小說的內在視角:它成為了眾多意識生成,交匯和聯結的關鍵點。
從文本的內容出發,我們可以發現,比目魚在女性法庭審判它的時候所做的抗辯,“我”通過自己在歷史上重要階段的親身經歷給自己的妻子伊瑟貝爾所講的故事和歷史上的各位廚娘在做飯的同時口述的歷史成為我們更好地解讀這些歷史故事的重要資源。從格拉斯的視角來看,我們可以通過努力,在新的條件下努力創造新的平衡,以漸進式的努力來靠近我們的最終目標:實現烏托邦式的理想。格拉斯對于物的描寫比較細致,非常注重以其藝術家的身份從各種不同的側面對事物進行“還原”,觀察它的具體特征。加繆認為,世界是陌生的,而且無法看透,所有認識和闡釋都是無意義的。格拉斯深受加繆哲學的影響,并由此發展出一種懷疑的精神:他懷疑一切現存的意識形態,并積極和非理性的現實力量抗爭。
2、隱喻的啟蒙
《比目魚》這部著作不僅反映了基于飲食史意義上的男女兩性的權力關系史,而且從深層次的角度來看,它更是一部反映作者對于啟蒙理性的可能性和限度進行反思的作品。“比目魚”這一形象成為了小說情節發展和轉折的關鍵因素。格拉斯深受蒙田的哲學思想的影響,認為在人的主觀意識中,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同等重要,都是不可忽略的,而且感性因素是純理性因素的重要補充。比如格拉斯的《鐵皮鼓》用荒誕的手法塑造了一個永遠無法長大的侏儒,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先天條件使得他常常可以從“另一種視角”和“另一種可能性”出發,看到成人世界中所隱藏的種種荒誕可笑的地方,進而諷刺當時成人世界的虛偽。他非常重視下意識,想象和夢幻這些奇幻性的因素,并把它們也加入了對于啟蒙現代性的思考當中。也就是說,他使得這些奇幻性的原則和啟蒙的話語形成了文本上的互涉性關系。一方面,這部小說對于《漁夫和他的妻子》這則童話的改編和小說開放性的結局暗示了以童話為其藝術特色的感性啟蒙的方式會一直延續下去,這是格拉斯應對受損的啟蒙理性和啟蒙現代性的一劑良藥;另一方面,夢幻象征著“集體無意識”的狀態,象征著隱藏在人們心靈深處的最原始,最純潔的愿望。那些被作者寄予了感性啟蒙希望的廚娘們,借助餐桌語言和勞動時口述的歷史的形式,發揮了她們的想象和主觀能動性,將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聯系在一起,這無形中消解了“自我”與“他者”的距離,使得“自我”與“他者”在感性啟蒙的召喚下實現更高層級的和諧。
3、重歸“母性神話”
格拉斯對于啟蒙的前景一直保持著樂觀積極的態度,他希望人類通過這條感性和理性辯證發展的啟蒙之路“走向內心”,尋求心靈神性的和諧與平衡,最終重歸“母性神話”。這種“母性神話”就是指在廚娘那種純潔和善良的內心力量感召下,消解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矛盾與分歧,重構“自我”與“他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之境。作者在小說的結尾也隱晦地表現了這一思想:在將比目魚重新放歸大海之后,“我”的眼前出現了多重幻影,仿佛歷史上的多位廚娘又重新朝我這邊走來。最終我認識到,是伊瑟貝爾逐漸走到了我的身邊,我追隨著她的背影而去。這里作者再一次運用了象征的手法,喻指我追隨著以伊瑟貝爾所代表的“母性神話”。
格拉斯的創作深受德國浪漫派的影響,他想借助文學感性啟蒙的力量來探討人類社會的前途與發展的問題。在《比目魚》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創作理念來源于德國浪漫派文學的“新神話觀”的設想。早期德國浪漫派的思想家們認為,神話是一種反映了原初人類社會樸素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文學體裁,詩與神話具有同構性。因此,詩性的精神可以超越純粹的理性存在,用美好的理想來代替黑暗的現實,這造成了生活的普遍“詩化”,提供了一種更高層級的自由。基于這個理論,他們又提出了“總匯的詩”這個概念:這是一種運用精神力進行的改變現狀的能動創造活動,并通過動態的詩來認識不斷變化的社會現象,最終實現理想和現實在最高精神層面上的“自由”。然而,格拉斯反對這種絕對精神,他認為,真正的啟蒙應該是在感性原則的指引下,借助于理性的,能動的力量來加以實現。只有這樣才能形成改造荒謬現實的巨大力量。這也反映了格拉斯的啟蒙思想和傳統的德國浪漫派“新神話學”思想的差異與不同之處。
4、結束語
在《比目魚》中,作者格拉斯用外在的童話框架和內在內容上富有感性精神和懷疑意識的廚娘形象,口述歷史的想象性和“陌生化”藝術效果形成層次上的呼應。它們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文本的奇幻性效果。在這種奇幻性的效果影響之下,他賦予自己的啟蒙理想以新的形式,即促進啟蒙理性和感性的有機結合,走上良性辯證發展之路。最后在最高精神原則——“母性原則”的感召下實現二者的詩性的統一。
參考文獻:
[1][德]君特·格拉斯,馮亞琳 豐衛平譯.比目魚[M].漓江出版社,2003.
[2]張辛儀.君特·格拉斯研究[M].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張麗.巴赫金復調理論對小說敘事理論的影響[J].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12期.
[4]余楊.文本的滋味——論君特·格拉斯的飲食詩學[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