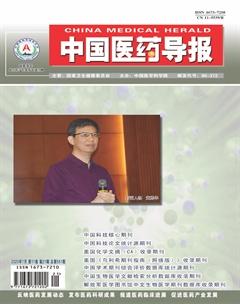精神康復開展和軍人康復思考
趙春海 蘇曉光 王曉慧 蔡紅霞 趙弘軼 孟文峰
[摘要] 精神疾病有著治療周期較長、復發率較高、致殘率較高的特點。精神康復的目的是,幫助精神障礙患者保存或提升生活自理、家庭勞動、職業工作能力,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降低致殘,適應醫院、家庭、社會之間的角色轉變,實現病后康復重新回歸家庭和社會,進而保持生活質量,體現個人價值,為家庭、社會作出積極貢獻。軍人群體的特殊性,決定了軍人精神障礙的康復需要考慮部隊建制體制獨立、訓練管理統一、崗位職責重要等因素,建立有別于現有精神康復形式的“軍人精神康復模式”,以減少對部隊日常建設和訓練的影響。
[關鍵詞] 軍隊;精神障礙;康復;模式
[中圖分類號] R749?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1673-7210(2020)07(c)-0181-04
Development of mental rehabilitation and thinking of mental rehabilitation of soldiers
ZHAO Chunhai? ?SU Xiaoguang? ?WANG Xiaohui? ?CAI Hongxia? ?ZHAO Hongyi? ?MENG Wenfeng▲
Psychiatr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er of PLA, the 984th Hospital of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Mental illnes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er treatment cycle, higher recurrence rate and higher disability rate. The purpose of mental rehabilitation is to help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to preserve or improve independent living, family labor, professional work ability,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society, reduce disability, adapt to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hospital, family and society, and realize the rehabilitation after illness return to the family and society, and then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life, reflect personal values,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family and society.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ilitary group determines that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mental disorders of the soldiers needs to consider factors such a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army′s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e unity of training manag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post responsibilities, and establish a “mental rehabilitation model of the soldier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form of mental rehabilitation, so as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daily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troops.
[Key words] Army; Mental disorders; Rehabilitation; Model
精神康復旨在幫助精神障礙患者恢復、保存(和/或減緩喪失)生活自理、獨立生活、社會交往能力,勞動技能和職業功能;進而減少復發、促進回歸社會,降低照護和管理成本。軍人作為一個特殊群體,要經常面對各種軍事行動的挑戰;軍隊的特殊環境決定著軍人是心理疾病的高發人群。降低精神和心理障礙對軍隊戰斗力的影響,需要預防、治療和康復三者相互促進、缺一不可。目前國內研究顯示[1],精神康復與臨床醫療的差異化開展是現代精神康復的趨勢,建立與住院治療相區別的社區康復服務、開展特色的技能訓練以及醫院到家庭的平穩過渡是其共同特征。因為軍人身份的特殊、崗位職責的重要和部隊管理的高度集中統一,具體到軍人精神康復開展上,無法完全復制目前在普通患者中已經開展的日間病房、會所制、庇護就業等形式。軍人精神康復的開展,要立足軍隊精神障礙診治專科建設的現狀,結合基層部隊和軍人精神障礙患者的需求,分析并借鑒已經日趨成熟的社會精神康復模式,即軍人精神康復要服務回歸部隊、社會,以個性化康復方案為基礎,充分應用現代醫學發展成果,通過全程康復保證康復效果的持續性。
1 增強軍人精神康復研究具有必要性
1.1 精神障礙對軍隊戰斗力的影響
各國公開資料顯示,精神障礙在現代戰爭中越來越常見,1992—1994年索馬里戰爭中,美軍創傷后應急障礙綜合征(PTSD)發生率約為8%[2];伊拉克戰爭中,需要心理救助的英軍人員比例為11.0%[3]。不僅如此,精神障礙會嚴重影響其他疾病的治療[4-5];并可能誘發其他疾病,有學者報告,海灣戰爭老兵中罹患PTSD者95%出現肌肉酸痛而非PTSD者只有50%[6]。
1.2 精神障礙對軍隊建設的影響
有資料顯示,140萬美軍現役軍人中需要門診治療精神障礙的官兵占6.0%,他們中因為精神障礙退役者達25.0%[7];在對現役軍人的流行病學調查中發現,英軍官兵存在精神問題者占20.0%,他們中PTSD占2.4%[8]。
1.3 加強精神障礙診治和康復研究的必要性
關于我國軍隊(簡稱“我軍”)的現有資料顯示,軍事沖突的精神障礙發病中精神分裂癥占較大比例[9];而在20世紀80年代后的局部調查結果提示,我軍官兵精神障礙患病情況與我國普通人群接近[10-11];但1998年的報告顯示,部隊精神疾病的總患病率達25.59‰[12]。
精神障礙在國內國外軍隊的發病情況均提示,做好相關防治和康復工作是保存和提高戰斗力的重要保證。
2 開展軍人精神康復研究具有可行性
2.1 國外精神康復發展
在美國,精神康復以社區康復為基礎追求回歸社會[13];在比利時,精神患者康復目標在于協助患者獲取適應自己和他人的自理權,提高患者自我照料能力,重塑社會尊嚴[14];在澳大利亞,要求對所有精神障礙患者實施全面綜合性服務,將以往住院服務為主的模式轉移到以社區服務為主的模式,并將后者作為精神康復服務的主體[15];在法國,一般在精神病院和社區都設有相應的治療和康復機構[13];在日本,精神康復政策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醫療、社會回歸、社區[13]。
2.2 國內精神康復現狀
在香港,精神康復服務形式多樣、體系完善,整個精神康復服務分為住院治療、醫院康復和社區康復3個階段;從居住形式、職業康復、精神支持和維權等環節保證精神病患者病情穩定后,其出院后有多種選擇,保證無縫對接[13,16]。
在臺灣,以慢性康復醫院、社區康復會所為代表,強調家屬的陪伴康復和主動參與,做好患者的自我接納、家庭回歸、工作適應、融入社區[17]。
在澳門,針對精神障礙患者設置日間康復中心幫助其在康復期學習技能和重建人際網絡,成為從醫院重返社會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支持[18]。
除以上地區外,我國比較發達的地區正在進行著“機構”向“社區”康復模式的轉向[1,13];例如深圳、上海、北京、蘇州等地,開始建立整套的精神健康服務體系,它們形式各異,如日間照料中心、會所模式、中途宿舍、個案管理等,把越來越多康復工作轉移到社區。但欠發達地區,特別是多數的大中小城市里的精神健康工作,這樣的轉變還沒有全面開始。
3 軍隊特色精神康復模式有待完善
3.1 國外軍隊精神康復資料有限
國外關于軍隊精神康復的信息所知有限,從公開資料可知美軍越來越重視心理衛生工作,其工作人員種類繁多,包括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軍官、精神衛生護士、牧師、全科醫生、軍醫等,各司其職,共同承擔心理衛生工作[19]。
3.2 軍人精神障礙診治日益重視
有學者[20-26]分別從人性化服務、綜合訓練、全病程醫療、集中收治、跟蹤隨訪、準軍事化管理等方面進行研究,報道了在臨床分階段診療、心理與勞動和社交訓練、預防與治療和康復結合、分區域管理、綜合治療和系統康復、延伸醫院服務、病房軍營化家庭化建設等方面的探索,收到較好效果。
4 我軍精神康復管理的研究思考
借鑒現有精神康復成果,結合軍隊體制要求和部隊管理實際建立具有我軍特色的、符合基層部隊實際和軍人需求的精神康復模式,至少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4.1 為回歸部隊做準備
運動對精神康復的積極作用已經取得共識[27],結合患者具體情況開展軍事體育運動,對于軍人身體機能恢復、體能儲備和社會功能恢復具有積極意義[28]。精神康復中實施軍營化管理,建立班排組織,實施“自我”管理;落實“內務”條例,堅持“一日生活制度”;結合康復管理,落實“值班”制度;在思想、身體、操課訓練和制度執行上為回歸部隊做準備,促進患者能夠快速適應從住院生活到回歸部隊后的緊張訓練節奏。
4.2 以回歸社會為宗旨
精神康復意義在于“回歸社會”[13];科學的職業能力訓練,如勞動技能、社會交往能力可以保存、提高,從而促進回歸社會[29];系統的個人技能訓練,如自我照顧、獨立生活能力可以減緩衰退,從而降低照護成本。回歸家庭、社會,這是減少精神障礙復發的重要因素,在軍人精神康復中有利于移交和退轉工作。技能培訓,參考“程式化”訓練模式[30],內容結合軍人康復者具體需求、部隊工作實際情況,可以是日常生活技能如餐桌清潔、居室整理,也可以是食物制作、隊列指揮。針對早期治療效果良好、回歸部隊崗位的軍人,提前以本職工作為背景開展技能訓練,特別是結合職業康復,模擬具體崗位展開訓練更有意義[29]。
4.3 以個性化方案為基礎
精神康復中應用團體訓練的效果明確[31],目前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精神康復并未建立明確的分類標準,但從專業的角度分析或一般常識的角度講,差異化的康復方案一定優于非差異化[32];因此制訂個性化的康復方案應是精神康復的基礎[33],其理念應是“集體康復訓練以團體形式出現,是基于每名康復者個性化方案的基礎上,共同的需求”,而非“集體康復的基礎上,增加個性化的訓練”。
開展個性化精神康復的目的是達到“精準康復”,即針對性的康復措施。有學者實施了分組群管理[34],有學者報告了“分級康復”的成果[35],但距離因人而施的康復方案仍有差距。具體實施中,可以考慮康復者生活自理能力、社會功能、精神癥狀等因素綜合評估并制訂分級分類標準和康復目標及方案。
[13]? 楊月明.國內外精神康復服務的經驗與啟示[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7,16(20):140-141.
[14]? 李欣.比利時社區精神衛生服務概況[J].中國醫院管理,2000,20(12):67.
[15]? 曾廣基.澳大利亞精神衛生服務體系[J].現代醫院,2009, 9(10):153-156.
[16]? 馮燕華.香港精神康復護理介紹[J].精神醫學雜志,2012, 25(1):66-67.
[17]? 吳際,萬心蕊.臺灣地區兩類精神障礙康復機構服務理念和內容的介紹[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6,30(12):886-890.
[18]? 吳麗巧,盧杏翔,蘇穎瑩,等.澳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對日間康復中心活動的感受[J].護理學雜志,2013, 28(21):77-79.
[19]? Hill JV,Lange C,Bacon B. Becoming a successful division psychiatrist:The sequel [J]. Mil Med,2007,172(4):364-369.
[20]? 李曉瓊,胡興煥,劉柳成,等.軍隊精神病人康復醫療中的人性化服務[J].解放軍醫院管理雜志,2006,13(1):46-47.
[21]? 甘景梨,高存友,張東衛,等.綜合心理行為訓練對軍人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效果的影響[J].第四軍醫大學學報,2007,28(8):738-740.
[22]? 胡光濤,李學成,賀英,等.“全病程醫療服務管理”模式在軍隊精神疾病患者中的應用[J].醫學教育探索,2010, 9(12):1595-1598.
[23]? 徐亞金,陳洪生.軍人精神疾病患者康復模式的實施與效果[J].護理管理雜志,2012,12(8):588-589.
[24]? 許鵬,張宇,盧山.“集中收治康復”模式在軍隊精神衛生服務中的應用[J].解放軍醫院管理雜志,2014,21(10):904-905,925.
[25]? 甘紅梅,徐洋,曲紅艷.體系部隊跟蹤隨訪管理對出院后精神分裂癥患者預后的影響[J].中國療養醫學,2015, 24(3):304-305.
[26]? 白晶,史振娟,賈艷菲,等.準軍事化管理模式對軍隊精神分裂癥康復期患者述情障礙和社交能力的影響[J].中國療養醫學,2015,24(11):1131-1133.
[27]? 張瑞星,李麗,Michel Probst,等.精神運動統合治療在精神康復中的應用與研究進展[J].中國全科醫學,2017, 20(20):2539-2542.
[28]? 杜菊梅,石晶,徐璐,等.運動療法配合心理干預對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9,27(7):991-996.
[29]? 李日照,汪云芳,王學林,等.多元化職業康復對精神分裂癥住院患者的影響[J].齊魯護理雜志,2018,24(4):32-34.
[30]? 林志平,趙安晶,甘紅梅,等.精神科程式化健康教育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的作用[J].解放軍預防醫學雜志,2016,34(3):392-395.
[31]? 謝平,張月蘭,朱黎雯,等.結構式團體康復訓練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療效及自尊水平的影響[J].心理醫生,2018,24(33):310-312.
[32]? 程東英.社區醫生督導下的重性精神障礙患者社區管理效果分析[J].中華健康管理學雜志,2015(2):98-101.
[33]? 鄧娟,梁鳳珍,盧勇花,等.個性化護理在促進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心理康復中的應用[J].中國醫藥科學,2016, 6(21):128-130.
[34]? 呂月娣,姜楊,沈校康,等.精神康復群組管理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技能的影響[J].中華現代護理雜志,2017,23(17):2259-2262.
[35]? 顧秀華,趙惠英,陳康,等.精神分裂癥患者分級康復干預效果觀察[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14(5):121-122, 123.
[36]? 王會秋,李群,徐桂娟,等.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治療現狀[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8,26(11):1756-1760,封3.
[37] 林翠綠,張麗君,張魯,等.積極性康復干預對首發精神分裂癥康復期患者社會認知影響的臨床研究[J].中國現代醫生,2018,56(36):77-81.
[38]? 董赟鵬.個案管理在精神康復社會工作的應用——以佛山市X醫院醫務社工站為例[D].蕪湖:安徽師范大學,2018.
[39]? 鄧蘭芳,孫寶川,黃海鋒,等.中山市病情穩定期重性精神障礙個案管理服務探索[J].中華健康管理學雜志,2016, 10(4):275-279.
[40]? 宋典雄.激勵理論指導下的護理干預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影響[J].醫學信息,2018,31(18):166-168.
[41]? 袁素麗,朱春燕.綜合心理治療及干預對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的影響[J].中國現代醫生,2019,57(26):143-146.
[42]? 陸紅英,袁勤,陶麗,等.支持性心理干預對社區精神分裂癥病人病恥感的影響[J].護理研究,2017,31(15):1831-1834.
[43]? 王芳,陳靜,薛麗,等.行為干預聯合心理護理對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療效研究[J].中國醫藥導報,2018,15(23):142-145.
(收稿日期:20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