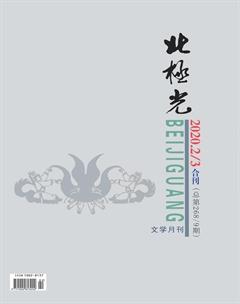疫情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楊竣焱
盡管我們困在屋子里不能走動,時光卻照常運轉。氣溫開始上升,遠處山川上的積雪慢慢褪去,那條蟄伏了一冬的山路露出尊容,窗外屋檐上的雪開始融化,滴滴答答,仿佛在向這世界講述大自然的活力,泥土變得濕潤而柔軟,風中夾雜著來自大自然的某種味道,令人覺得親切,看來春的氣息絕沒有困在這個冬天里,“草木蔓發,春山可望”的日子不遠了。在最冷的省會城市哈爾濱,偶爾還飄起幾片雪花,輕描淡寫一番,之后便沒了影蹤。節氣的轉變是誰也阻擋不了的,包括病毒。
盡管困于斗室,我也并非無所事事。自大年初二開始,翻譯許多礦業領域的俄文材料。自知水平有限,皆倚仗網絡輔助、查字典和四處討問來完成,但是也感覺到自己的些許價值,自己的精力還算充沛。翻譯之余,協助市作家協會整理和修改一些征文,寫一些心得,偶爾還讀讀書,在網絡上看看電影,收拾屋子,下下廚房。反正自己現在多的是時間和精力,自主擇業后也沒有像樣的工作,便可以“油油地在水底招搖;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當然,有時候一天的時間,也會在百無聊賴中度過。“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起床、睡覺、吃飯全不成規律,時間也被打亂,隔幾天去超市買點菜,也如做賊一般,匆匆來去,不敢與人過多搭訕。在這樣的背景下,老老實實服從安排,是普通民眾最需要做的。偶爾還于夜間在大學校園里走走,信馬由韁一番,換個環境,也換種心情,而首要前提當然是絕對避開陌生人,絕對做到不與人擦肩而過。想到網上有人曬出的條幅上寫道:“你上街遇到的每一個陌生人都是索你性命的勾魂野鬼。”這當然過于夸張,但是嚴加防范還是好的,至少不給國家添亂。看到這冷清的夜,不免想起電影《我是傳奇》,雖然不會有僵尸出現,可是真是把這么空曠的校園都交給了你,你絕對不會感到快樂。人的生命危機,在于剝奪了他的社會屬性。
退役軍人事務局組織人員在哈爾濱火車站值勤,做測溫和登記工作,我也報了名,算是為抗擊疫情做點貢獻。組織者的安全防護措施十分到位,自然不用畏懼。不過,穿著厚重的防護服,一天或者一夜站下來,也確實挺累。于是想到一線的醫護人員,他們面對死亡和病痛,面對擁擠不堪的醫院,面對不同病灶和情緒的患者,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壓力可想而知。
疫情也影響著需要出門的人。2月12日,送兩位朋友去機場,我算是出趟遠門,他們則更是遠涉重洋。一路頻繁檢測,好在各類手續一應俱全。朋友居住在東寧市,目的地是對面的烏蘇里斯克市。正常情況下,坐上單人票價220元錢的大客車,3個小時就到了。可是在此非常時期,他需要坐火車來到哈爾濱,然后換乘飛機到達北京,再轉機8個小時到莫斯科。之后等上一天時間,乘坐俄羅斯境內航班,經過8個小時到達海參崴,最后換乘客車到達東寧對面的烏蘇里斯克。原本3個小時的車程,他需要4天時間,原本160公里的距離,變成了空中2萬里,從亞洲中轉歐洲再回到亞洲。我不知道,當他站在烏蘇里斯克的某處山岡,望向中俄邊境線,想象著對面不遠處就是東寧市,會是怎樣的心情。
比起疫情,輿情是另一個戰場。輿情同疫情一樣,在華夏大地上蔓延,復雜甚至相悖的信息不斷涌進腦子里,讓我不明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普通民眾要學會站穩立場,要相信官方媒體的報道,為全面客觀的評論鼓掌,特別是學會甄別帶有套路的低級紅和高級黑。我記得。人民日報特別批判過低級紅和高級黑,這是對黨的威信和人民覺悟的害。
生活中不止有疫情,還有對生活的向往,對寫作的熱愛。我常常想,倘若人過中年,還不能懂得如何更好地對待生活和生命,這便是一種悲哀。好在有了一些條件,可以留出些時光放進文字里。作為寫作者,許多感受付諸筆端,就要對它負責,使它生長成一棵有滋養的小樹,而不是歪瓜裂棗。看到許多寫作者都在從不同角度描述疫情,這是一種積極的信號,表明我們學會了審視當下,學會了反思,這有助于我們走好今后的路。
疫情之下,留給人們許多思考。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思考就是:人們要學會承認,災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1910年冬的哈爾濱肺鼠疫,19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1966年邢臺大地震,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長江松花江特大洪水,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還有2003年非典型肺炎和今天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及數百年來的戰爭,許許多多的天災人禍,構成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不僅要學會歌頌成就,也要學會接納災難。有時候,災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特別是災難避不可免的時候。生活中有出生和死亡,有快樂和悲痛,有安居樂業和漂泊流浪,有民族的千秋大業,也有國家的生死存亡,就是沒有一帆風順,一路高歌。
未來,我們有許多夢想,也會有許多困難。對于國家、民族是這樣,對于個人也是這樣。把疫情看作生活的一部分,人類的經歷才能豐滿起來,人類才能學會與萬物相處,學會遵循自然規律,降下身段,更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