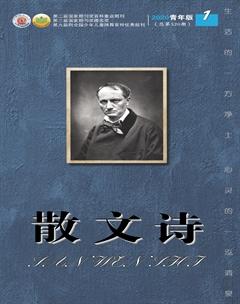木工器具
劉彥林
墨斗
它的個頭,大不過一拳之握;它的膚色,比墨汁還要黧黑;它的功用,直尺也難以比肩。
小小的墨池,細細的長線,是它身體上所有的部件。只需少許墨汁,就有明辨和洞察的能力,勝過學富五車的睿智和博識。一根線經過墨池的叮囑,在彈起和落下的剎那,所有的歪斜和結疤都心知肚明。
它內心的黑,是為了取直一根木頭,也是為了矯正視覺偏差,更是為了校對是非曲直。一根細線,一條道走到黑。它的抵達——凹陷的地方,感到羞怯;凸起的地方,感到忐忑。歲月的滄桑也同化不了它,它對一根木頭是否能成為可造之才,有著最中肯而公正的評判。一個聰慧的思維,也催生一項偉大的發明。祖師爺生命中遇見的草,更具神性的呼喚和昭示。
一塊鐵,經爐火的焚燒、鐵錘的打制、清水的淬火,就有堅硬、柔韌和鋒利的脾性,就有深入木頭體內的激奮。最初,伐木的鐵斧對待木頭的方式兇狠、野蠻,傷木頭更深;鋸子的溫情、迅速和直接,讓木頭少受了許多疼痛。所有的木頭,對鋸子都多了從未表白的感恩。
一把鋸子伐木,是木頭和鋸子相愛;明知是最決絕的傷害,木頭卻從來都充滿期待。一把鋸子把粗笨的木頭肢解,分解為方木和木板,成為一件家具的部件,呈現出精美的韻味,木頭得到了重生,鋸子卻被時光磨損得失去鋒利。只有邀約小小的銼刀,才能重新喚醒最初的剛性。
鑿子
瘦削、細長,是它的形體;前端為鐵,末端為木,是它的材質;每敲打一下,它就嵌進一分,這也是鐵和木材不能更改的存在方式。
鑿眼、挖空、剔槽、鏟削,是它的使命,也是它一輩子的宿命。鑿出更多的卯眼,挖空更多的障礙,剔出更多的凹槽,鏟削更多的粗糙,讓木頭更具生活的用度,更具光滑的肌膚,更具穩固和美觀的構架。
以墨線為準繩,以鑿進為目標。鑿多少個孔洞,鑿多少個卯眼,它銘記著那一點點的痛、一點點積攢的喜悅。當尖部銹鈍時,便到磨刀石上,找回最銳利的秉性,給予木頭以疼痛,這也是一種相濡以沫的恩愛。
它也感激斧頭和錘子的助力——它們的敲打,是嵌進的動力,也是執著的堅守,更是一種默契的配合。它記住了這份久長的形影不離,也記住了這種敲打也是一種深沉真摯的情義。
即使終會從忙碌的鑿進中撤退,回到陽光再也照不到的地方,然而,它的回憶和反芻里,總會飄蕩著木頭的醇香,以及和木頭曾經傾心相談的快慰。
哦,這被歲月曾經緊緊攥在手里的鑿子啊!我對它始終心懷崇高的敬意。
錛子
同樣是心有靈犀的鐵哥們,它和斧子算是一對孿生兄弟,只不過,它能被握在手中的木把更長,它能比斧子更加威嚴地對待任何性格倔強的木頭。
它砍的對象是木頭,它的目標是讓木頭更加符合橫平豎直和方圓有度的要求,只不過,它進取的方式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步步為營。它終讓那些超出墨線的部分瞬間潰敗,紛紛撤回對一根木頭預設的障礙,甚至是木頭心里的那些疙疙瘩瘩……
它以自己的平面面向木頭,和木頭的交流更有銳度和鋒芒;它被師傅緊緊攥在手中,看到哪里有凸起,哪里有結疤,哪里有盈余,都會將其三下五除二地砍削殆盡。當一截木頭接近規整的形體,錛子就可以稍作歇息,放下此前的任何芥蒂,心平氣和地回到工具箱中,而木頭則被交給鋸子截成所需的長度,或交給刨子取直拋光,達到成為房屋構建的要求,甚至達到一個家具所需的光滑程度。
砍啊,砍啊……
它會把木頭砍上一輩子——這是它不可推卸的責任。
木頭也對它給予溫柔地反抗,把它反擊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甚至是容顏俱老、滄桑滿目,歲月的皺紋也犁上了臉龐,風霜更是在黑色的發絲上落下一場大雪,綻放著別致而隱秘的花朵。
木匠一生不能離棄的錛子啊!它的模樣已經深深地鏤刻在我心靈的壁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