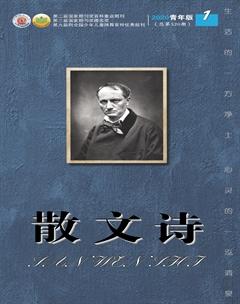像風一樣來去
夢兮
給父親理發
白的柔軟,灰的剛硬,黑色的還有鋒刃
小心地取下父親的光陰,我像一柄彎刀,像一枚半月
更像一葉扁舟,在人世的潮水中掙扎
盡是父親的牽掛
而我又在一寸一寸剃掉他僅存的日子。
夕陽返照過來
我知道黑暗緊隨著,我知道這一切終將會離開
葡萄藤
盤起來,像一個被霜殺過的人,蜷曲著
一根裸露著的筋骨
等待冰雪覆蓋,春天就是這樣,在枯干的枝條上
燃起嫩綠的火焰,這種時候
我總是不由自主地
扭頭看看,蹲坐在屋檐下地臺上的父親
蜷縮著,像落滿白霜的葡萄藤
我相信在春天面前,一定會伸直腰身,開花,掛果
一只麻雀
麻雀輕輕地站在枝頭
孤獨的背影
像一個蹲坐著的老人,更像失了聰的四奶奶
此時,我剛好走過
它并沒有飛起,像看見了一個異類
一雙渾濁的眼眸
在我臉上胡亂地撞,在我身上胡亂地掃
我們就這樣站著
像站在村子脆薄的睡夢里,或一個人歲月的深處
一地苞谷秸稈
一稈稈走到盡頭的
卸下黃金鎧衣
直挺挺躺在田里等著被收走的秸稈
我不敢看
提著鐮刀的父親
站在地埂上
我羞恥于不敢做他的兒子
終有一日
一縷秋風會割倒這一株老玉米
須子都白了
頭上落滿一層白霜
而我又無能
擦去雪花的痕跡,誰能告訴我,日子該怎么續接
在蒼茫的黃昏里
從來都是目送著我們遠走
仿佛我們這些熟透了的果實,還需要他親自照看
從來都是他一生的追求
最亮的光始終都要給我們
可是白晝從來都不會眷顧一個老態盡顯的人
日子奉了時光的旨意
取走他所剩無幾的黑發,在蒼茫的黃昏里
一切都是靜止的
只有我們越走越遠,仿佛黑夜是一塊燙手的炭塊
舍不得一株麻子的氣味
霜降過了,葉子開始黃起來,香氣才會彌漫
父親也是這樣有了獨特的香味
可惜,一株麻子最后會變成黑色,應該是光陰
最后的色彩,我不敢奢望
但我崇拜的就是一只飛臨村莊的小鳥
可惜,鳥兒的羽翅太脆
還禁不住暴風雨,我把你稱之為我的朋友
靈魂上唯一的朋友
我的父。我舍不得一株麻子的氣味
我希望在你的疆場上
我是一匹垂頭吃草的馬駒兒,多少年,我都未長大
鏡中人
我不認識他
這種陌生前所未有,這人不可辨別
失色的眸光中
剩下些盡是痛苦、膽怯、懦弱、茫然
我無法觸摸他的孤獨
更無法接近
他的內心,他的家門一直緊鎖著
絕望是他唯一的朋友
無人知道他所走過的路有多么崎嶇
黑暗之于他是唯一的光明
風兒的剃刀也倦了,旅人的疲憊
只是人世不堪的一擊
他的身后光,和眼前黑,是他一生虔誠的信仰
像風一樣來去
幸好還有不滅的燈
幸好還有一息尚存的父親點著不滅的燈
幸好還有風自由來去
幸好我還能像風一樣來去
幸好理智還在努力
幸好守住村子底線的野草一直都沒有沉睡
幸好大門一直敞開著
幸好掌紋中還有貧窮遺留下的根梢
幸好神明的指示還在
幸好露珠還能夠托起太陽
幸好晨曦還需要眸光
幸好潛意識里的需要能夠端起陽光
幸好還有神愿意接受我如此清貧的敬獻
雨露的仁慈
它們不會一直站在草尖上
為吸引更多陽光
心中的海傾瀉而下,葉瓣才能嘗到最溫暖的甜美
它們不會壓垮父親的眉梢
為留住汗水的鹽分
像陽光那么直白地傾其所有,澎湃涌動的
是一個人的心
在一滴雨露最后的時光中,看到了歸來的車輦
屈尊者
山,放下堅持已久的高度
草,堅決把披靡之勢用瘦弱的身子延續下去
雨水笑著不知所畏
那些歸來的腳步
臣服于路。路從來都不會貪功
它們只是舉著
像野草舉著露珠,它們相信
這些馱著太陽,奔跑的水,一定會低到塵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