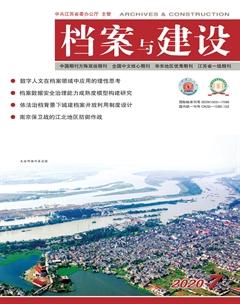淮河安瀾看今朝
張紹力
1950年6月,華東防汛總指揮部急電:“淮河中游水勢仍在猛漲,估計超過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 8月1日急電:安徽淮北、淮南2萬多平方千米土地水深3米,從蚌埠到五河也是一片澤國,被淹沒農田3100萬畝、倒塌房屋80余萬間、受災人口990萬,失足落水或被樹上毒蛇咬死者489人……告急電報接二連三,直達京城。毛澤東心情無比沉重,數度流下淚水。僅兩個月時間,毛澤東就先后4次親自批示,治理淮河的迫切心情躍然紙上,刻不容緩。10月14日,政務院頒布《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揭開了新中國大規模治水的序幕。1951年5月,毛澤東揮毫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淮河全長1100多千米,水位落差達200米。河南、皖北、蘇北三地存在著較大的意見分歧。尤其是地處淮河入海尾閭的蘇北,擔心上游淮水停滯蘇北,不能順利入海,反而加重蘇北的水患災害。在政務院召開的治淮工作會議上,有關“蓄泄”爭論異常激烈,安徽、蘇北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周恩來總攬全局,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上游以蓄為主,中游泄蓄兼施,下游以泄為主。毛澤東確定了“河南皖北蘇北,三省共保,三省一起動手”的團結治淮原則。
淮河古稱淮水,與黃河、長江、濟水并稱“四瀆”,有著自然入海的獨立通道。淮河流域面積達27萬平方千米,人口1.78億、耕地2億畝。流域面積僅占全國版圖的2.8%,然而占有的耕地和生產的糧食分別占全國的12.5%和13%。
早在13世紀前,淮河自河南省桐柏山太白頂發源,一路向東而下,直抵云梯關入海。那時淮河底寬500米左右,水深面闊,水流通暢,入海口淵深澄澈,行洪能力達1萬立方米/秒,可承襲上中游20多萬平方千米的匯水順暢入海,潮汐影響亦可西達盱眙。那時的淮河水位比長江還低,是一條利多弊少的河道。“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諺語曾廣為流傳。
宋紹熙五年(1194),黃河決堤南犯奪淮,打亂了原有的淮沂沭泗下游水系,淤廢了淮河的入海通道。歷史上黃河曾屢屢奪淮,史稱“黃河四徙”,危害最烈、持續時間最長的當數1194年。此次奪淮演變成全流奪淮局面,延續661年,直到1855年黃河拋棄淮河故道北徙山東利津入海。沉淀的大量泥沙給淮河下游造成了深重的災難,淮陰以下至入海口,原來又寬又深的河槽普遍淤高4 ~ 9米,成為地面河道,即“廢黃河”,釀成了浩瀚淮水入海無路、入江不暢的殘破局面。
歷代王朝都曾將治理淮河擺上議事日程,意在維系漕運,然而勞民傷財,災害有增無減。明永樂年的“蓄清拒渾”,萬歷年的“蓄清刷黃”“分黃導淮”,清王朝的“蓄清刷黃利運”“蓄清利運”等等,修葺補苴猶有不及,何談全面治理。
孫中山在其《建國方略》中懇切提出:“修浚淮河為中國今日刻不容緩之問題”,但心有余力不足,空留一腔遺愿。清末民初實業家張謇潛心研究20余載,導淮方案不斷深化,從“全流入海”到“江海分流”,“七分入江三分入海”等,留下了紙上談兵的種種草案。
1929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導淮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可是,在他統治的20多年中,淮河水患有增無減,愈演愈烈。1934年,國民政府選擇在淮陰向下沿186千米廢黃河拓浚入海水道,拖拖拉拉4年多時間,設計規模不斷縮減,原計劃泄洪450流量,實際僅能通過200流量。自濱海小鬼灘向下至套子口僅開挖了20千米新河道,成為國民政府唯一的“導淮政績”。為了彰顯“導淮政績”,將整治過的20千米河道命名為“中山河”,尚余河段仍為“廢黃河”。
自1194年至1938年700多年間,淮河流域水旱災害不斷,鹽堿、飛沙、蝗蟲、暴風、海潮等助紂為虐,先后發生洪澇災害達1000多次,船行樹梢,餓殍遍野,慘不忍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朝不保夕。
1950年11月,治淮委員會成立,地址在安徽蚌埠。同時,豫皖蘇三省建立相應的治淮機構,將治理淮河擺上了重要日程。毛澤東批準將屢立戰功的解放軍兩個師整建制改編為水利工程建設第一師、第二師,2萬余名官兵全部轉業治淮,直屬水利部領導。
首先打響興建蘇北灌溉總渠的戰役。1951年7月26日,周恩來拍板“在蘇北開挖灌溉總渠”,并撥給大米1億斤。
興建灌溉總渠的動員令不脛而走。外出逃荒的災民紛紛返鄉,積極報名,踴躍投身于治淮運動。涌現出父子、兄弟、夫婦爭相報名、互不相讓的動人場景。治理淮河與抗美援朝同樣重要、同樣光榮,參加治淮的民工與報名參軍是一個標準,同樣要經過自愿報名、基層審查和區鄉批準。在工地召開的誓師大會上,決心書、挑戰書、倡議書雪片般飛向主席臺。民工們喊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我們如今翻了身,也讓淮河翻個身”“長城是人修的,總渠是人挑的”等,宣傳標語隨處可見,群情激奮、士氣旺盛。
灌溉總渠西起洪澤湖高良澗,穿越淮陰、鹽城2個專區、6個縣,至濱海縣扁擔港匯入黃海,全長168千米,規劃設計800流量。淮陰、揚州、南通、鹽城共出動民工119萬人。各縣成立治淮工程總隊,正職縣長出任總隊長兼政委,親自帶隊開挖總渠。各區鄉正職區鄉長親自帶隊,齊心協力打響了治淮的攻堅戰,速戰速決,確保翌年汛期到來之前投入運行,發揮效益。時間緊任務重,百萬民工們硬是憑著肩挑鍬挖車推,起早睡晚酣戰83個晴天,如期完成,挖土7300多萬立方米,創造了人間奇跡,僅鹽城專區即出動民工58.9萬人,完成土方3239萬立方。
“老區人民以工代賑,83個晴天建成蘇北灌溉總渠”的喜訊傳到北京,周恩來深有感觸地說:“根據蘇北的經驗,他們可以動員幾十萬人參加治水,可見治淮的能力是有把握的。”蘇北灌溉總渠具備灌溉、泄洪、排澇、航運、發電等多種功能,自此,洪澤湖有了一條獨立入海的泄洪通道。1952年5月亞太和平會議期間,20多個國家代表強烈要求前往總渠一探究竟。當他們邁步總渠大堤,十分震撼。灌溉總渠成為下游地區3000萬畝耕地、2600萬人口的安全屏障。
洪澤湖位于淮河中下游交匯處,是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也是一座特大型平原水庫,更是千里淮河的總調度,牽一發而動全身。1956年,淮委《淮河流域規劃報告》確定了“洪澤湖按千年一遇設計,萬年一遇校核”的治理目標,且洪澤湖下泄最大流量為16600立方米/秒,規劃分別由入江、入海通道下泄。
按照“千年一遇設計,萬年一遇校核”的目標,蘇北灌溉總渠具備泄洪入海的功能,僅是建國初期的權宜之計,建設名副其實的“淮河入海水道”勢在必行。按照規劃,淮河入海水道將分兩步實施:近期工程泄洪流量為2270立方米/秒,洪澤湖防洪標準將由5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遠期工程泄洪流量為7000立方米/秒,防洪標準將提高到300年一遇。
淮河入海水道緊挨灌溉總渠北側,與灌溉總渠成三堤兩河,灌溉總渠的北堤即為入海水道南堤。近期工程于1999年10月開工建設,2003年6月28日竣工通水,比計劃工期提前整整900天。7月4日,竣工僅6天時間的入海水道啟動行洪,最大流量達1870立方米/秒,連續行洪33天,共泄洪44億立方米;灌溉總渠同期泄洪10億立方米。據《中國水利報》當年報道:2003年洪澤湖最大入湖量達14500立方米/秒,比1991年高3000多立方米/秒。2003年淮河流域僅啟用了9個行洪區,而1991年則啟用了17個行洪區。2003年避免啟用100萬畝良田分洪、80萬人緊急轉移,實現了“不決一處堤,不死一個人”的安全目標,據匡算,避免直接經濟損失達100億元。2007年汛期,入海水道再度泄洪,泄洪量高達2070立方米/秒,洪澤湖防洪達到了百年一遇標準。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即遠期)已經箭在弦上。二期工程實施后,泄洪流量達到7000立方米/秒,洪澤湖防洪標準將實現300年一遇。
淮河上游號稱“人工天河”的淠史杭灌區,成為我國最大灌區之一。佛子嶺大壩成為中國第一座混凝土連拱壩,亦為亞洲第一壩、世界第三壩。號稱“千里淮河第一壩”的出山店水壩,大大減少了王家壩以下行蓄洪區啟用幾率,切實減輕了中游以下防洪壓力。有著“千里淮河第一閘”美譽的王家壩閘,位于上中游結合部,地理落差為178米。遙看王家壩閘,猶如一條巨龍橫臥在蓄洪庫上游,最高處達28米,有萬夫不當之勇。王家壩閘成為保護淮河中下游的一道重要屏障,是淮河防汛抗洪工程的重中之重。
70年來,新中國不斷地加大治理力度,淮河流域已經形成一個集防洪、排澇、灌溉、航運等功能比較完整的運行體系,基本能夠控制常遇的水旱災害。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經投入治淮資金達3000多億,地方政府組織民眾累計投入勞力亦達數百億元。建成大小水庫6000余座,總庫容300多億立方米,形成了由水庫、河道堤防、行蓄洪區、湖泊等防洪體系,理順了“淮沂沭泗”水系,實現了淮河洪水入江暢通、入海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