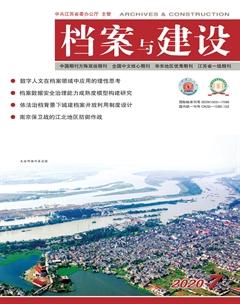耄耋之年筆耕不輟 搶救歷史資政育人
徐立剛


江蘇金壇的地方史專家范學貴老先生年屆86周歲,又出第五本書了。
范老并非專業出身的史學工作者,自1994年從金壇市級機關退休后,他成為口述史料采集、地方抗戰史研究的志愿者,成果累累。范老先后出過四本書:《戰斗在茅山下——江蘇省金壇地區新四軍老戰士訪談錄》29萬字,2007年出版;自傳體回憶錄《伴隨共和國走過60年》30萬字,2009年出版;《金壇慰安所遺址資料匯編》,2010年印發;《新四軍老兵尋蹤》,2013年印發。這些書都是范老用自己走訪搜集整理的第一手史料或者他自己親身經歷寫成的,都是扎扎實實的新鮮成果。
大概是在2018年6月,范老從網上傳給我30多萬字的電子書稿《記述無韁》,我既贊嘆又好奇地打開,開始細細拜讀起來。《記述無韁》這本書稿跟范老以前的書一樣,是范老用他走訪搜集整理的第一手史料或者他親身經歷寫成的文章的結集。其內容十分豐富多彩:既有中國抗日軍民的艱難處境和英勇斗爭,也有日偽軍的罪惡行徑與可恥下場;既有抗日戰爭時期的詳實史事,也有解放戰爭、和平建設、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片斷;既有對公開直接的政治、軍事斗爭的描述,也有對驚心動魄的隱蔽戰線、地下斗爭的記錄;既有戰爭年代中日軍隊的你死我活,也有戰后中日民間的和平友好;既有近現代、當代過來人的親身經歷,也有古代宗族先人源遠流長的史跡;既有金壇本鄉本土的恩恩怨怨,也有僑胞、臺胞、海外華人的血濃于水、故鄉親情;既有英雄模范、社會精英、老革命、老領導的個人形象,也有普通干部、平民百姓、邊緣人物的人生蹤跡;既有金壇的鄉土氣息,也有北歐的國際視野……其語言一如范老以往的風格,真實生動,娓娓道來,扣人心弦,令讀者如同身臨其境。謹在此例舉一二。
《一位難得的統戰人才——范征夫》記錄了抗戰時期曾在金壇戰斗過的老干部、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政協秘書長范征夫,為了落實黨的統戰政策,堅持實事求是,無私無畏的動人事跡。
征夫同志,從解放前到解放后,從唯物史觀到現行政策,從孫大雨的點點滴滴到全部歷史,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全面的基本準確的孫大雨。此時的征夫想:同一戰壕的戰友,二十多年來苦了你了。他已與孫大雨肝膽相照,孫案不糾,不公平、不公正。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他去向張承宗部長匯報。一開頭就斬釘截鐵地說:“張部長,我個人認為孫大雨這個右派可以改正。”接著,征夫條理分明地一一細說:1.孫大雨解放前表現是好的,帶領廣大教授參加學運,沖鋒陷陣,甚至冒丟腦袋瓜的危險也在所不惜;2.解放后他唯一女兒在他支持下參軍,走上保衛祖國參加國防建設崗位;3.他個性倔強,性格桀驁偏執,思維方法特別,遇到不盡如人意就口出狂言罵人,正如沈從文送他八個字,多才、狂放、驕傲、天真。但這是另一種性質問題,不是什么反黨反社會主義;4.對這樣的人,解放后我們安排工作不到位,也是應當檢點的;5.他的底線是寄希望于黨和政府,不服就申訴,包括向胡喬木同志申訴。他有著廣泛的海外關系,在那種情況下,他也沒做出于黨和國家不利的事;6.即便是1957年,毛澤東同志對他也不主張一棍子打死。到了撥亂反正的今天,我們更沒有理由不去超越歷史上的恩怨是非,團結好這樣一個學有專長的垂暮之年的老知識分子吧。張部長聽完匯報,完全贊同征夫意見。并召集部里相關部門開會,心平氣和,各抒己見,取得共識。辦完改正孫大雨右派程序,最后誰也不愿拿去與孫見面,原因很簡單,怕罵。這又落到范征夫肩上。
某日,范征夫在衡山賓館約定與孫大雨見面,按時由另一人陪來。一見面,征夫說,今天請您來談談您右派改正問題。他說,談什么談,我又沒有錯!征夫心里明白,這就是真正的孫大雨,倔強、爽直、坦蕩、沒有虛偽和矯情。征夫接著說,不用你認錯,是把統戰部關于改正您右派決定正式告訴你。他說,我根本不是右派,我從來都不是右派。講話就這么硬撅撅的。征夫深知自己是代表黨組織與孫大雨見面的,人民干部就應當理解他幾十年心中的郁積,拿出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姿態為民(他)服務,這是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所以,已掌握孫大雨個性的他,豁達大度,談笑風生。心想,只要你孫大雨從今天起,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做好你的學問,目的就達到了。這不正是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核心精神所在么。[1]
《本多下跪背后的故事》記錄了侵華日軍老兵本多立太郎兩次來金壇謝罪,而為了讓本多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宿愿,范老等多人做了許多艱苦細致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勞動。
眾所周知,92歲的侵華日軍老兵本多立太郎,因1939年在金壇親手殺害過一名新四軍戰士,兩次來金壇謝罪。為什么2005年、2006年連續來兩次,這背后還有哪些故事?
2005年5月,本多第一次來金壇謝罪,此刻,已是小泉純一郎執政第五個年頭了。
五年來,小泉無視國際社會、亞洲鄰國和日本人民的反對,悍然四次參拜供奉有14名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挑戰國際正義,踐踏人類良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多次表示強烈抗議,中日兩國關系可想而知。哪怕一點兒不慎,也會成為外事活動中的麻煩。因此,有關方面把這一活動確定為“民間”往來。于是乎有關人士請我這個老百姓到場應酬。
他們提供被日軍殺害的一名無名小戰士,烈士墓地在下新河,本多到達后見了說,這小戰士不是他所加害,結果沒有達到目的。一些事新華社記者黃明寫稿公開了我的姓名,刊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所以遺留下來的問題就成了我的事兒了。
于是我與金壇檔案局的施志霞、趙亞平還有公安警官余堯等四人利用假日調查研究,最后確定,指前鎮王家橋亂墳崗,這里埋葬著侵華日軍老兵本多立太郎在67年前受命殺害十名新四軍戰俘中的一名。當旅日華僑朱弘獲悉,將此轉告本多后,他打算再次來到金壇在十位蒙難壯士碑前下跪贖罪。
這在中日兩國,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本多這一舉動,我們當然表示歡迎。
在中日關系的這個節骨眼上,我必須認真對待這次“民間交往”活動,具體事情我愈想愈多,靠我個人是難以完成的。

無奈,我只得寫封信向金壇市委、市政府報告。市委書記徐惠中作了批示:“請外辦受理”。外辦艾副主任接待了我并去指前實地察看,認同了這個結論。一個周末,我直闖金壇市市長吳曉東辦公室,自我介紹。吳曉東市長正與袁月冬副市長面對面談話,見我到來,非常禮貌地接待我。先表示感謝我為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再聽我一番敘說,就直接交代分管外事工作的袁副市長把接待工作、安保工作、應急預案、烈士認定等一一落實,并主動答復范學貴同志。這次辦事效率之快是我意想不到的。周一,袁副市長便與公安局等三個部門落實到位,還有一個部門作出口頭回應。
2006年春,江蘇廣播電視總臺廣電新聞中心《1860新聞眼》征集評獎節目,向他們省臺老搭檔旅日華僑、獨立制片人朱弘詢問,朱弘就向他們推薦了這一內容。省臺領導研究覺得可以,于是先派王小蓓攝制組率記者張寧、楊勇等三人先來前期采訪。市外辦賀主任親自接待。王小蓓向省海事局借金壇海事快艇一艘,由金壇市區直往指前鎮,再由指前鎮向溧陽竹簀橋、黃金山,沿途采訪老游擊隊員、地下黨員、當地年長者知情人,收獲頗豐。[2]
這本32萬字的《親歷、親見、親聞,記述無韁》,由常州市金壇區檔案館編印。范老與金壇市(區)檔案局、館長期以來友好合作,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范老是一位建國前半脫產參加革命的老干部,1949年7月入團,1951年6月參軍,1956年11月入黨。他為人耿直率真,其人生由此歷經坎坷曲折,“文革”后才苦盡甘來。范老的人品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的——他是范仲淹的后裔,第29世孫,此非虛言,有族譜為證。范仲淹七世孫范克家,南宋寧宗嘉定八年(1215)任湖州府四安鎮務,調潤州府金壇縣丞。由此,范仲淹有一支后裔在金壇繁衍。范老繼承了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境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剛直風骨,一生不變。
范老又是見過世面之人,1980年代他曾負責金壇縣的僑務工作數年,晚年又曾居住瑞典、游歷多國,頗有國際視野。因此他雖然年紀大、資歷老,但思想解放、辦事開明。
范老做事踏實勤奮,退休后四處奔走,調查采訪,筆耕不輟,成績斐然。其實他1996年就已經身患癌癥,但他仍無所畏懼。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評論文章《從范學貴看“走出書齋”的知識分子》,對于當時72歲的范老自發地實地調查侵華日軍設在金壇的“慰安所”,給予高度肯定:
以腳步丈量歷史的軌跡,刻錄時間的真實,我對于這樣耄耋之年依舊執著于尋訪那段血色記憶的民間志愿者,除了敬意,還是敬意。也許,相較于高屋建瓴、侃侃而談的學者專家們,范學貴老先生沒有那么深厚的學養,但他做到了學者專家們很少做到的一點:走進最真實的民間鄉土,在尋尋覓覓中淘沙取金,最終獲得鮮活的一手資料。……和許許多多名重一時的正史、文獻有所不同,這些大多出自個人的、民間的文字記憶、殘垣破壁,其實也蘊涵著豐富的學術與歷史價值,若不加收集、整理,很容易在茫茫時空中消失得無蹤無影。[3]
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秘書長左玉河博士,翻閱了范老所著《戰斗在茅山下——江蘇省金壇地區新四軍老戰士訪談錄》后,對范老肅然起敬:“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抱著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拖著病弱的身軀來從事這種艱辛的口述訪談工作,真是不容易。”[4]
2008年11月,應范老本人要求,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經該會理事會研究討論,破例接收范老為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個人會員。
范老的可敬精神和可喜成就,著實讓我這讀歷史專業出身的后輩欽佩、汗顏。

我與范老交往開始于2005年。這一年,經金壇市檔案局、館的同行牽線,范老開始向《檔案與建設》雜志文史欄目投送口述歷史稿件,此后多年連續不斷。其稿件質量較好,只是文字需再加工處理,于是大多陸續被選用,其中還有文章獲得該刊201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主題征文活動一等獎。2011年1月,范老到南京辦事,順便來《檔案與建設》編輯部,與編輯當面溝通。那次他跟我一見面就說:沒想到你這個編輯這么年輕。其實當時我已年近50歲。我心里說:沒想到范老你這么瘦。十幾年間交往中,范老送過我幾本書和自制年歷片等,彼此卻只見過這一面。范老2018年在《記述無韁》電子書稿中統計說,十多年來《檔案與建設》共編發他的稿子23篇。我看了略感意外,因為此前我真沒想到能達到這個數字。
大家應該知道,做口述歷史工作是非常艱辛的事——先尋找歷史當事人,說服其同意作口述訪談;確定了口述者之后,采訪者自己需要熟悉相關歷史背景知識;訪談要嚴格依照科學規范進行,作文字記錄、錄音錄像,采訪者對口述者口述內容作適當引導;訪談后采訪者整理口述記錄,進行必要考證,核實疑難細節;最后采訪者須征得口述者認可口述成果等等。各個環節都是事務繁瑣,耗費精力,成本很高,事倍功半。比起一般的史學研究,這要吃力費勁許多,且還是替人作嫁衣,因而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正如口述歷史專家左玉河反復強調的:“沒有一點奉獻精神,沒有一點對歷史負責和對后人負責的精神,就根本不會來做口述史,也根本做不好口述史工作。”[5]
正因為這一點,我在《檔案與建設》雜志的文史欄目編輯工作中,對于口述歷史類的來稿處理很慎重。編輯部曾有同事說范老的稿子刊發偏多了,我便認真地強調:這些稿子都是范老用自己走訪搜集整理的第一手史料寫成的,都是扎扎實實的新鮮成果,絕非那些拼拼湊湊的文章可比。大家覺得有道理,也就都認可了。
2018年6月《記述無韁》電子書稿發來后,范老來電話要我為他的《記述無韁》新書寫序,我嚇了一跳,自覺不夠格。但在八十多歲老人的執意要求下,恭敬不如從命,我只好斗膽答應了。經過通讀《記述無韁》書稿,思前想后,在那年中秋節后,我寫下了一些內心感言奉上。
范老這位金壇地方史研究的常青樹,是激勵我等后輩不懈努力的榜樣!
參考文獻
[1][2]范學貴主編:《親歷、親見、親聞,記述無韁》,常州市金壇區檔案館編印,2020年,第134-135、198-199頁。
[3]畢舸:《從范學貴看“走出書齋”的知識分子》,《南方周末》2005年7月21日。
[4][5]范學貴編著:《金壇慰安所遺址資料匯編》,2010年,序一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