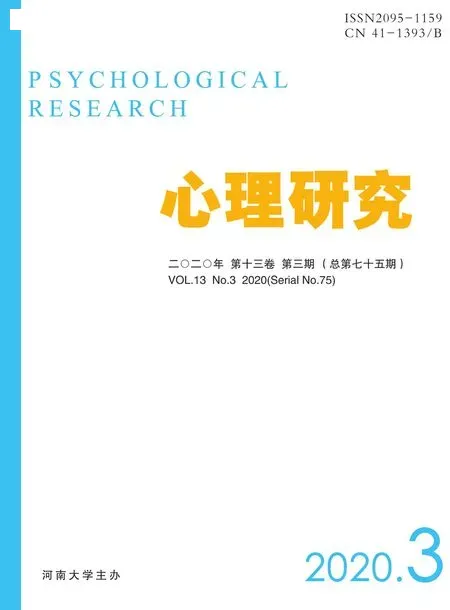文化自信問卷的編制
周 婷 畢重增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人格發展與社會適應實驗室,重慶400715)
1 引言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習近平, 2016),基本、深沉和持久說明了文化自信的地位和屬性。認知文化自信的起源與表達、理解文化自信的影響因素與塑造路徑,是教育學、文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探討的對象。 心理學是探討文化自信不可缺少的一個視角, 其中的量化研究更是認識文化自信的心理內涵,挖掘文化自信的功能,發展文化自信的基礎性工作。開展系統的量化研究,需要概念的操作化界定和設計有效的測量工具, 本研究的目標即編制一個可用于量化研究的文化自信問卷。
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緊密相連,文化自覺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和形成的過程, 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創造現代的中華文化,以完成文化自覺的使命(費孝通, 1997, 2003)。 正是這種自覺促生了文化主體理解自身文化, 并在此基礎上產生文化認同和依戀,也就是宏觀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功能是在實踐活動中賦予心理與行為以價值和肯定,形成具有適應性的社會心理模式和個性特征。一方面, 建立在文化自覺基礎上的文化自信系統地賦予了人們行為的價值階梯,另一方面,文化主體的文化意義和情感表征及對應的心理與行為, 對文化具有反應性和能動性。
文化是群體現象, 個人與群體的關系是界定文化自信的最基本角度, 也是進行文化自信測量的邏輯基礎。文化自信包含了對文化群體、社會群體及族群的認識、認同和依戀。 從內容成分來看,內群體認同包含了認知、情感和個人/群體相互依存(Hinkle,Taylor, Fox-Cardamone, & Crook, 2011), 社會認同包括自我歸類、 群體自尊和群體依戀(Ellemers,Kortekaas, & Ouwerkerk, 1999), 族群認同的核心因 素 則 是 參 與 度 與 自 豪 感 (Roberts, Phinney,Masse, Chen, & Romero, 1999; Spencer, Icard,Harachi, Catalano, & Oxford, 2000)。 這些概念描述了文化主體探索、了解和融入內群體的認知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族群歸屬感、自豪感和滿意感。文化認同和族群認同 (Bhugra, Bhui, Mallett, Desai,Singh, & Leff,1999;Phinney & Ong, 2007)等個人與群體關系概念的有效測量為設計文化自信測評工具提供了方法論支撐, 文化自信中無論是個人能依據經驗和公共知識對自己所屬文化做出評價和判斷, 還是具有內群體共同性的文化心理評價體系和經驗感受系統,都是可以有效測評的。
評估文化自信需要確定作為評價對象的文化主體和評價的內容。 雖然每個人對文化的理解復雜多樣, 但超越個體的文化對象和文化內容的共通性使得評估文化自信具有現實的可行性。首先,中華文化可以作為文化自信評價的對象。中華文化超越地域、性別、階層等群體差異,具有最廣泛的可認知性,是文化自信的核心載體。其次,認識和評價紛繁復雜的文化需要一個簡約而有效的認知框架。 文化也是個體社會認知的對象, 可從社會認知基本維度的框架去評價。 社會認知包含能動性和社群性兩個維度(Wojciszke, Baryla, Parzuchowski, Szymkow, &Abele, 2011), 是回應群體生存和發展的兩大基本問題(Bi, Ybarra, & Zhao, 2013),這兩大問題也是任何文化群體發展所應當解決的問題, 理所應當構成認知和評價文化及文化自信的兩大內容領域。文化的能動性是文化為群體提供的現實生存基礎,即涵養生活、創富經濟、富強國家的價值,展示出文化對社會和文明的基礎性作用, 這也是文化最顯著的、可以為人們所知覺和判斷的一面,也正是文化自信中評價文化、認同文化、依戀文化的基礎內容。 文化的社群性是文化的價值與功能所渲染出的心理感受,如依戀、驕傲等,在這個文化多樣化的時代,個體可借此緩解文化碰撞帶來的壓力 (Hong, Fang,Yang, & Desiree, 2013)。 且個體感受與評價文化時,不僅有認知上的感受,還會激發一些情感體驗。因此, 文化自信的評價體系既有對文化能動性的認識,也有文化情感的成分,二者構成了評估文化自信的基本內容架構。 中華文化確定了評價文化自信的主體維度,使文化自信評價有了群體性認同對象,而文化的能動性價值表現則為文化自反性評價提供了內容系統。
本研究關注的是文化自信心理評價層面的共通性特征,即個體對文化的一般看法,而不涉及參與本族群文化活動的意愿及頻率等行為模式。由此,文化自信與測量文化具體行為的相關概念有區別, 如文化 智 力 (Dyne, Ang, Ng, Rockstuhl, Tan, &Koh, 2012)、 族群認同(Spencer, Icard, Harachi,Catalano, & Oxford, 2000); 也與測量抽象文化表征的相關概念有區別,如文化本質論(Lin, Arieli,& Oyserman, 2019)、 文化距離感 (Galchenko &Vijver, 2007)。 這些聯系和區別為檢驗文化自信測量工具的有效性提供了概念和實證依據。 文化智力指個體在具有文化多樣性的情況下, 根據文化線索發現、 吸收、 推理并采取適當行動的能力(Dyne,Ang, Ng, Rockstuhl, Tan, & Koh , 2012)。 文化智力反映出個體的文化交往與適應能力, 是跨文化認知與行為的基礎性變量。 文化全球化拓寬了文化交往、凸顯了文化之間的沖突和挑戰,也加深了文化認同(Holdstock, 1999),直接的或間接的多文化經驗會增強對本文化的認同。因此,文化智力高意味著更能辨明文化邊界, 在文化對比中增強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自信。 文化本質論指某一文化中為其成員共同接受的文化特征與信條, 認為文化中有固定的本質,不可改變(Lin, Arieli, & Oyserman, 2019)。這些特征和信條與文化的能動性和價值性及文化認同纏繞在一起,成為文化自信的內生關聯維度,文化本質論為文化自信提供認識上的方法論。 極端的文化本質主義可能會導致文化宿命論, 但適度的文化本質論可以為人們的文化自信提供客體支撐。
總的來看,為了提供一個高信效度的測量工具,促進文化自信的實證研究, 本研究基于概念分析認為,文化自信的基本內涵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以文化的能動性和情感因素為核心內容, 在自反性認知過程中形成評價性心理結構,并以大學生為對象,通過心理測量學的合理建構程序編制文化自信問卷,系統考察其信效度。
2 方法
2.1 研究對象
樣本1:成都某高校大學生305 人,年齡均值為20.9 歲(SD=1.50),男性127 名,女性178 名。該樣本完成文化自信問卷。
樣本2:重慶某高校大學生380 人,年齡均值為21.1 歲(SD=2.17),男生92 名,女生288 名。 該樣本完成文化自信問卷、 文化本質論問卷及文化智力問卷。
2.2 研究工具
自編文化自信問卷。 本研究從擬訂的文化自信能動性、情感兩維度的概念出發,分析學者們關于文化自信的研究,抽取有代表性的論點編寫相應項目,獲得文化自信量表的相關條目。 能動性維度8 個項目考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與信心, 如:“與其他文化相比,中華文化更有開放性和包容性”、“中華文化有一個光明的未來”;情感維度8 個項目表達對文化持有的積極情感, 如:“我對中華文化充滿了驕傲和自豪”、“我對于中華文化總體上是滿意的”。 文化自信問卷的作答形式為Likert 式7 點量表, 即在1~7 量尺上表達自己對每個項目的同意程度 (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
文化智力量表。Dyne 等(2012)編制,包含16 個項目,回答者在1~7 量尺上表達自己對每個項目的同意程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分數越高表示文化智力越高。本研究中,該工具的克隆巴赫α 系數為0.81。
文化本質論量表。 采用Lin,Arieli 和Oyserman(2019)組合有關工具(Chiu, Dweck, Tong, & Fu,1997;Haslam, Rothschild, & Ernst, 2000)形成的文化本質論中文版, 共有8 個項目, 回答者在1~7量尺上表達自己對每個項目的同意程度 (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 分數越高表示越認同文化本質論。 本研究中,該工具的克隆巴赫α 系數為0.71。
3 結果與分析
3.1 項目分析
采用題目得分組間差異和題目與總分的相關為指標確定項目的質量(見表1)。 以問卷總分前27%作為高分組,后27%作為低分組,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進行組間題目得分平均數差異檢驗發現, 所有項目高分組與低分組的得分都有顯著差異。 計算每一個項目與量表總分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發現, 除c9外,其他項目與總分均有顯著相關,相關系數在0.30以上。 綜合這兩項指標,刪除問卷的第9 個題目。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為了檢驗數據是否適合做因素分析, 首先對數據進行取樣適當性檢驗。 KMO 值為0.91,Bartlett 的球形度檢驗χ2值為2389.95,df=120,p<0.001, 說明各項目之間有共享因素的可能, 進行因素分析是恰當的。

表1 文化自信問卷的項目分析
對15 個項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使用主成分、等量最大旋轉法抽取因素。因素抽取以特征值大于1 為基本原則,輔之以平行分析。真實數據特征值的第三個因子小于隨機數據特征值的平均值和95%分位值,故保留兩個因子。參考測量工具編制類文獻(董軍, 李洪玉, 李曌宇, 盧山, 2018)將題目刪除標準定為: 共同度小于0.20, 最高載荷小于0.45。由此,一共刪除5 個題目。最終保留10 個題目形成一個兩因子結構, 各項目均在相應因素上具有較大載荷,處于0.58 至0.87 之間,見表2。
因素1 有5 個項目, 涉及主體對自身文化持有的積極情感,如驕傲、自豪等,命名為文化自豪。因素2 包含5 個項目, 主要衡量主體對自身文化的確信感,是對主體文化的肯定、贊許,以及認定文化能應對挑戰、蓬勃發展的信心,命名為文化贊揚。
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見表2, 兩維度及總問卷的克隆巴赫α 系數為0.80~0.86,總問卷的組合信度為0.86,問卷的信度較為理想。
3.3 驗證性因素分析
依據概念界定設定研究模型包含兩個因素,每個因素由對應探索性分析題目測量, 誤差或獨特因子彼此均無關。 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對模型進行擬合估計。
驗證性因素分析得到主要的擬合指標為,χ2=75.15,df =34,p <0.001,χ2/df =2.21,RMR =0.04,GFI =0.96,AGFI=0.94,TLI=0.96,RMSEA=0.06,RMSEA 的90%置信區間為0.04~0.08,PCLOSE=0.25>0.05。 從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來看, 研究模型的擬合指標達到了推薦標準 (Sharma, Mukherjee, Kumar, &Dillon, 2005)。 評價測量模型好壞的標準還包括各個觀測變量在潛變量上的載荷, 以及在誤差或獨特因子上的載荷大小。一般來說,在潛變量上的載荷較高, 就意味著各個因素在誤差或獨特因子上的載荷較小,表示模型的質量較高。 表3 的因素載荷及圖1的標準化路徑圖說明, 每一個觀測指標為相應的潛變量所解釋的比例較高,而誤差或獨特部分較小。這些指標表明該模型結構對數據的擬合良好, 表明文化自信問卷具有較好的構想效度。

表2 文化自信問卷的因素分析摘要表

表3 文化自信問卷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因素載荷
3.4 實證效度

圖1 文化自信問卷驗證性分析的標準化路徑圖
相關分析結果可看出,文化贊揚與文化本質論、文化智力顯著正相關,文化自豪與文化本質論、文化智力顯著正相關,與理論預測一致,表明文化自信量表具有較好的效標效度(見表4)。

表4 文化自信與校標變量的相關分析矩陣
4 討論
4.1 文化自信問卷的結構
文化自信的結構是編制文化自信測量工具的依據,而結構的確定又取決于概念的性質。文化自信是文化主體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礎上, 賦予文化充分肯定,進而產生的積極情感體驗,包含文化贊揚和文化自豪兩個維度。 文化贊揚是認知與評價文化時產生的確信感, 是文化自信的首要內容也是文化情感無法剝離的基礎, 文化自豪是文化認知內容在情感上的自然體驗。文化贊揚與文化自豪是不可分割的,贊揚是基礎和先導,而自豪是核心和歸宿。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 文化贊揚和文化自豪的解釋率分別為22.73%和26.63%。 文化認可、贊許和頌揚自然會伴隨對文化的積極情感, 缺少了認知內容的文化自豪感是空泛的,難以體現文化的自覺和成熟,更難勝任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因此,兩個因素用于衡量文化自信符合文化自信命題提出的背景、 內涵和功能。
從社會認知的視角看, 文化自信的兩因素也是合理的。 文化以人群為載體,個體認同文化,也認可相應的文化群體,文化認同和群體認同是融合的。具體體現為評價文化時能動性認知和情感兩方面的整合, 來自于文化認同和群體認同 (Mccowan & Alston, 1998; Schwartz, Montgomery, & Briones,2006)過程中對文化群體的信仰、價值觀和能動性的認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聯結性情感,服務于文化過程和群體過程所需要解決的生存與發展兩大基本問題。 文化自信的認知維度是在個人與群體認同的基礎上發展出與文化信念有關的堅定感受, 表達的是具有廣泛性和超越性的更深層次認可。 文化自信所包含的情感成分,產生于個人、群體以及文化的交互作用過程,以文化認同、贊許和頌揚為載體,表現為對文化群體、內容和精神的自豪。從個體層面所測得的文化驕傲與自豪不僅僅是個體文化認同與體驗的情緒情感, 更是一種與文化聯系所產生的超越個體的群體性情緒, 反映了群體和文化的自我認同與評價的情緒情感基調。 文化自信有驕傲、自豪、滿意等積極情感成分, 這些情緒也是人們群體歸屬與認同的典型情緒,諸如此類的情緒可見諸內群體認同、族群認同、 社會認同(Ellemers, Kortekaas, & Ouwerkerk, 1999; Henri, Turner, & John, 1986;Roberts, Phinney, Masse, Chen, & Romero,1999)。
4.2 文化自信問卷的有效性
對本研究編制的文化自信問卷的有效性, 我們有系統的證據:采用合理建構取向編制項目,內容通俗易懂; 各個因素及總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達到了測量學的要求;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及相關分析均支持文化自信問卷的因素結構。
文化自信與文化本質論的關系, 從文化認知生成與發展的角度提供了文化自信問卷有效性的證據。本質論是認識文化的一種高效方法,學齡前兒童已具備本質論思維(Gelman, 2003),并持續影響對事物的認知。 文化自信與文化本質論的關系表明人們是基于文化本質去理解文化, 將文化的內容以本質化的形式概念化、類別化,作為文化自信認知和評價的對象。 被本質化的內容可以是廣為人知的中華文明光輝燦爛的歷史, 可以是現時代經濟社會建設的偉大成就,是個體評價文化,產生文化認同、自豪感的根源基礎。 本質化將個人經驗與文化意向和符號聯系在一起,是認知文化、體驗文化、評價文化的形式,為個體在心理上提供了一個清晰、穩定、有效的方法,使文化自信具有了穩定、清晰、一致的特性與表現(畢重增, 2017)。這也意味著,以本質論的方式去理解中華民族勤勞、勇敢、智慧等品格,不單是民族驕傲情感產生的心理過程, 是產生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徑,也是文化自信的評價依據。
文化自信與文化智力的關系從文化接觸、交往、溝通的角度提供了效度證據。文化交往中,多種文化對比會激發人們認識自身文化, 也正是引言中所述的文化自覺是形成文化自信的路徑之一。 文化智力反映出個體文化間的交往能力, 其內容和過程來自于文化接觸、交往、溝通中個體全方位的認知、體驗、評價。從文化智力的各成分來看,元文化智力使個人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顯性的文化意識和執行過程;認知文化智力使個人關心不同的文化的制度、規范、實踐和習俗; 動力文化智力使個人將注意力和精力引導到學習文化差異的情境中; 行為文化智力使個人在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時運用多種語言和非語言行為溝通。 這些都是文化交流中文化自信產生的具體心理過程和內容。 從文化智力的理論來看(Earley & Ang, 2003),文化智力高是文化認同整合良好的結果, 也是對所屬文化的認同提升的過程。換言之,文化交往過程促成了有關的文化智力所界定的文化技能, 而這些技能更有助于對文化之間的關系形成更廣泛、更深刻的認知,發現所屬文化群體優秀品格, 形成文化自信。 這在問卷中有條目體現,如“與其他文化相比,中華文化更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需要注意的是,跨文化交流能力,對異文化的規范、實踐和習俗的知識與實踐技能,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更多處于想象和消極接觸層面, 而文化自信具有自我認定、信念的性質,這并不依賴于文化他者的存在, 文化間的對比對于文化自信的形成和表達是不充分的。 這種文化對比的外在現實因素和文化自信的內在特征在研究結果中也得到了展示,表現為文化智力與文化自信之間雖然相關顯著, 但相關并不高。
4.3 文化自信問卷的應用
文化自信問卷的編制具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首先,文化自信問卷提供了探究公眾文化自信心理的研究工具, 可用于驗證和發展有關學科的理論,如文化自信對個體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因素的作用模式。其次,個體會通過文化依戀來定義自我、 增強自我 (梁麗, 楊伊生, 肖前國, 利愛娟,2019),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個體是如何依據個人的經驗建構出層次更高的文化自信的?再次,文化自信問卷作為一個測評工具, 可用于培育文化自信的實踐評估。文化自信理論上有利于心理健康、道德發展和品格養成,因而評估個體、群體、地域的文化自信特點,就能一定程度反映文化自信的建設情況。價值觀、道德、科技等都是文化的具體內容,相關的評估可反映對應領域的文化自信的特點。最后,文化自信概念測評,為使文化自信成為大眾概念,進而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水平,發展文化歸屬感、建立文化價值感,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4.4 研究局限
首先, 本研究編制的文化自信量表中文化主體指的是中華文化,并不涵蓋其他的文化主體;其次,對文化自信的界定是形式性的,只包括認知和情感,并沒有具體的文化內容載體,如飲食、服飾、建筑等,具象文化內容層面等的自信量表需要進一步編制;再次,本文編制的工具以大學生為對象,在推廣應用到其他群體時,需要視具體情況檢驗其有效性。
5 結論
本研究編制了信、 效度均符合心理測量學要求的文化自信問卷,為人格、社會、文化等有關領域開展系統的實證研究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測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