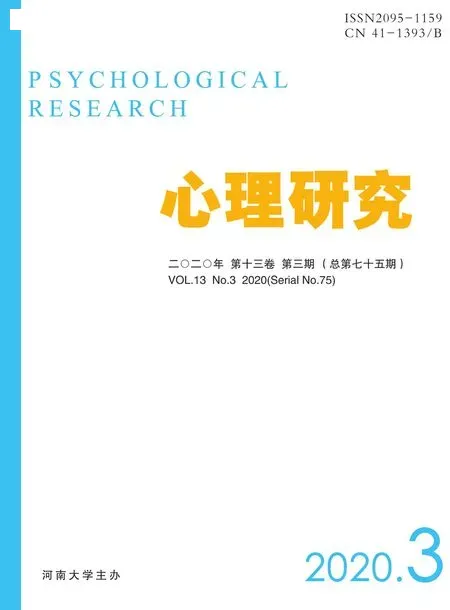女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與抑郁的關系:消極認知應對的調節作用
朱行健 汪郁云 陳 晨 秦金亮
(浙江師范大學杭州幼兒師范學院,杭州311215)
1 引言
隨著時代的發展, 越來越多的女大學生呈現出復雜多變的心理特點,“女漢子”“萌妹子” 等開始成為95 后女大學生的代名詞。而很少有研究單獨關注95 后女大學生的心理狀態。 抑郁是一種常見的負性心理狀態, 大學生群體學業壓力和抑郁狀態顯著正相關(趙萌,麻雨婷,張寶山,2019),且抑郁可能使個體產生非持續性自我傷害行為等不良影響(趙若蘭,樓淑萍,陳輝,2019)。我國女大學生群體的抑郁檢出率為21.6%(唐慧,丁伶靈,宋秀麗,2013)。 同時,對人際關系敏感的女大學生可能比男大學生更易出現嚴重的抑郁癥狀(陳程,陳方方,劉曉宇,2020)。 因此, 女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應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
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與抑郁狀態的關系受到諸多研究的探討。 例如,陳曉霄(2015)的研究發現,被他人誤解、戀愛不順利、學習壓力過高、與他人關系緊張等負性生活事件會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產生消極的影響。 同時,季善玲和王惠萍(2019)的研究也發現, 負性生活事件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這些研究結果也許可用抑郁認知易感模型解釋, 個體抑郁易感性受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 在負性生活事件的刺激下可能會激活一些負性認知思維和行為(Young,2001)。 此外,不同性別群體中,負性生活事件與抑郁狀態的關系可能不同。男生比女生可能有更多負性生活事件 (邢存瑞,2019),但是女生在負性生活事件中壓力的感知可能高于男生(袁文萍,馬磊,2019),可見女生可能更易受負性生活事件影響而產生抑郁情緒或抑郁傾向(Codispoti,2008)。
認知應對是個體在處理沖突時常用的策略。Garnefski 基于不同維度的認知應對特征將其分為消極認知應對和積極認知應對(Garnefski,2001),不同的認知策略在應對抑郁、 負性生活事件時呈現不同的影響。 依賽男等人(2018)的研究表明,積極認知應對和抑郁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 而消極認知應對和抑郁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同時,唐海波等人(2014)的研究表明,消極認知應對與負性生活事件正相關, 積極認知應對與負性生活事件負相關。 而女生在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可能采用更多自我責難、 災難化等消極認知應對方式 (肖晶,黃任之,凌宇,2009)。 這些研究結果可能表明,認知應對可能在負性生活事件與抑郁狀態間存在一定的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焦慮等消極情緒狀態與自殺意念有高度的相關 (Fawcett et al., 1990; 蘇斌原,張衛,周夢培,等,2015)。 同時,應激-易感模型(Cavanagh, Carson, Sharpe, & Lawrie, 2003;宮火良,李思雨,2012)指出,負性生活事件作為個體生活中重要的應激因素,其對個體的抑郁狀態,甚至是自殺意念風險有正向預測作用(李亞敏,雷先陽,張丹,等,2014;辛莘,何成森,2010;張月娟,閻克樂,王進禮,2005)。 認知應對作為人們對付內外環境要求及其有關的情緒困擾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是否可降低或增加應激反應水平, 從而影響負性生活事件(應激)和抑郁狀態(易感因子)之間的關系? 已有研究對此的探討付之闕如,而以心理復雜多變,抑郁檢出率較高,對負性情緒事件更易感的95 后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則更是未見。基于此,本研究以95 后女大學生為對象,探討女大學生抑郁、負性生活事件和認知應對之間的關系, 驗證認知應對在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間的調節作用。
2 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在浙江省四所高校(省屬高校) 中抽取女大學生779 人參與問卷調查,回收問卷后剔除規律性作答、 遺漏問題數量超過1/5 的問卷, 保留有效問卷674 份, 有效回收率為86.5%。在有效樣本中,被試的平均年齡為19.88 歲,標準差為1.34。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負性生活事件量表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
采用劉賢臣等編制的青少年自評生活事件量表(劉賢臣,劉連啟,楊杰,1997),量表由可能給少年帶來心理生理反應的負性生活事件構成, 共27 個條目,包括6 個分量表:人際關系、學習壓力、受懲罰、喪失、健康適應、其他。 采用五級評分(1 為無影響,5為極重),得分越高,說明這一類負性生活事件對該個體的影響越重。本次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6。
2.2.2 流調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采用流調中心抑郁量表測量抑郁(汪向東,王希林,馬弘,等,1999)。 該量表共20 題,包含4 個分量表:抑郁情緒、積極情緒、軀體癥狀與活動遲滯、人際關系困難。 采用4 級評分,各項目按0 到3 評分(偶爾或無=0,有時有=1,經常或一半時間有=2,大部分或持續有=3), 總分范圍為0~60, 反向題重新記分后,得分越高表示抑郁傾向越強。判定抑郁癥狀的標準是: 總分≤15 分無抑郁癥狀;16~19 分可能有抑郁癥狀,≥20 分肯定有抑郁癥狀。 本次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9。
2.2.3 認知情緒調節問卷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
采用由羅伏生(羅伏生,2006)引進并修訂的中文版認知情緒調節問卷,共36 個條目,包括9 個分問卷:自我責難、接受、沉思、積極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評價、理性分析、災難化、責難他人,每個分問卷4 個條目,在九個認知策略中,自我責難、沉思、災難化和責難他人為消極認知應對;而積極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評價、接受和理性的分析為積極認知應對。 評分方式采取五級評分(1 為幾乎從不,5 為幾乎總是)。 在某個分問卷上得分越高, 被試就越有可能在面臨負性事件時使用這個特定的認知策略。 本次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9。
2.3 研究程序
研究以浙江省某高校為單位進行問卷施測,課題組成員聘請施測高校一名心理學專業的同學為負責人,負責人經過線上的系統培訓后擔任主試。施測過程統一組織完成,測試時長為20 分鐘,測試結束當場回收問卷。
2.4 數據管理與統計分析
采用SPSS22.0 進行數據的錄入和分析。 通過Pearson 相關分析,考察女大學生生活事件、抑郁、認知應對的關系。 運用Hayes 的SPSS 宏程序PROCESS 考察大學生的認知應對(積極認知應對、消極認知應對) 在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關系中的調節作用(Pengcheng Wang,2017)。 進一步采用Johnson-Neyman 法,考察認知應對的取值對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關系的影響(Hayes,2009)。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檢驗
本研究采用自我報告的方法測量和收集研究數據。 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對結果的影響,我們根據已有研究者的建議(周浩,龍立榮,2004)重點從施測程序和數據處理方面進行了控制。具體而言,在施測程序上:(1)選用信效度較高的成熟量表進行測量;(2)對不同量表采用不同指導語,適當采用反向計分方式;(3)采用匿名式測量,強調問卷的保密性。在數據處理上,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即對所有量表題目進行未旋轉因子分析,獲取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4 個, 最大因子的解釋變異量為35.94%,小于40%,說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2 女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抑郁、認知應對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為考察女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抑郁、認知應對的關系,采用皮爾遜相關法分析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果見表1。 負性生活事件、抑郁、認知應對均呈顯著正相關,其中負性生活事件、抑郁、消極應對之間的相關更為顯著(p<0.01)。

表1 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抑郁、認知應對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3.3 女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關系:認知應對的調節作用
使用Hayes(Hayes,2013)的SPSS 宏程序PROCESS 分析負性生活事件對抑郁的影響是否受到認知應對(消極認知應對、積極認知應對)調節。對各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之后,把抑郁作為因變量,負性生活事件作為自變量,消極認知應對、積極認知應對分別作為調節變量,結果見表2。

表2 認知應對與負性生活事件對抑郁的交互效應分析
如表2 所示,負性生活事件(β=0.17,p<0.001)、消極認知應對(β=0.18,p<0.001)、積極認知應對(β=0.12,p<0.001)對抑郁的預測作用顯著;負性生活事件和消極認知應對的交互項(β=0.08,p<0.01)對抑郁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結果說明負性生活事件、消極認知應對、積極認知應對都可以正向預測抑郁,消極認知應對可以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關系。
另外, 為檢驗消極認知應對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關系, 進一步采用Johnson-Neyman 法進行檢驗, 分析結果如圖1 所示。根據圖1 的結果,當中心化后的消極認知應對取值低于平均數1.06 時([-1.06,2.17]),簡單斜率檢驗顯著。因此,當消極認知應對取值低于平均數1.06時,可以顯著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關系。
4 討論
近年來,大學生總數快速增長,但是大學生就業漸趨飽和。 同時, 就業單位對人才學歷要求不斷提高,直接增加了大學生的就業壓力和學業壓力。而與壓力緊密關聯的抑郁作為大學生常見的一種負性心理狀態,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但是很少有研究關注女大學生的抑郁情緒, 同時也較少探討造成女大學生抑郁的潛在因素。 因此,本研究基于量化數據,以95 后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究女大學生抑郁、負性生活事件和大學生認知應對之間的關系, 為女大學生身心健康、 前途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本研究發現,女大學生抑郁和負性生活事件、積極情緒調節策略和消極認知應對呈顯著正相關。 同時負性生活事件、 積極認知應對和消極認知應對均能顯著預測大學生的抑郁水平, 消極認知應對在一定區間內對抑郁和負性生活事件的關系起調節作用。
4.1 女大學生抑郁與負性生活事件和認知應對的相關分析

圖1 負性生活事件對抑郁的調節效應分析
本研究發現, 抑郁和負性生活事件呈顯著正相關,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徐寧,張偉波,楊美霞,2019)。這說明女大學生在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中經歷的負性生活事件越多,抑郁的水平越高。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女大學生作為一個青春有活力的群體, 每天在社交中都需要面對種類多樣的負性生活事件,而女大學生較為內向,在人際交往中也較拘謹,這些性別特征導致負性生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女大學生的心理應激,導致其處于一個不愉快的心境中,從而使抑郁水平上升(陳程,陳方方,劉曉宇,2020)。所以, 女大學生在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需要及時調整自己的心態,克服過分的焦慮;學生工作部門的相關老師需要關注女大學生在一些特別時期的心理狀態,比如考試周、生理期、失戀期等,給予女大學生更多的關心、關愛,加強咨詢和幫扶的力度,盡量減少負性生活事件對女大學生的影響。
抑郁和消極認知應對呈顯著正相關, 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劉夢楠,2019),說明女大學生越頻繁地采用消極認知應對面對生活事件, 抑郁水平越高。 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相比于男生來說,女大學生在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更容易采用自我責難、沉思、災難化和責難他人等消極認知應對(肖晶,黃任之,凌宇,2009)。 同時,女大學生的情緒化程度高,很容易被自己的消極態度繼續感染,產生“破罐子破摔” 的破窗效應, 最后導致自己的抑郁水平上升。所以,女大學生在學習生活中需要盡可能地采取積極科學的認知應對方式,在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首先要沉著應對,冷靜分析,適時調整自己的情緒,以積極樂觀的情緒面對負性生活事件。
本研究發現, 抑郁和積極認知應對也呈顯著正相關, 即女大學生在采用積極認知應對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抑郁水平也會上升,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席明靜,2017)。 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女生的表達方式較為拘謹, 在使用積極情緒調節策略時,比如與人溝通時沒有表達出內心的真實想法,導致積極認知應對并沒有起到有效調節抑郁的作用,所以抑郁水平還是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 同時,已有研究結果(凌宇,彭君,鐘明天,2014)表明,在積極情緒調節中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評價等與大學生抑郁水平顯著正相關的原因可能是,三種應對方式均是對負性事件的再加工, 從而再次提高了抑郁水平。
4.2 女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關系:認知應對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認知應對在負性生活事件預測抑郁中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顯示,負性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預測抑郁, 消極認知應對在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而積極認知應對不能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間的關系, 這一結果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劉雙金,胡義秋,2015)。 具體而言,女大學生采用消極認知應對的頻率增加,負性生活事件對抑郁有正向預測作用, 即女大學生經歷越多的負性生活事件,抑郁水平越高。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在心理方面,女大學生頻繁地使用消極認知應對,會降低個體的心理彈性(唐海波,周敏,2014)。這說明, 擁有較低心理彈性的大學生在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會產生較大的壓力,體驗到更大的挫折感,進一步導致抑郁水平的提高;在生理方面,消極認知應對會導致大學生睡眠質量下降(李炳,2015),睡眠質量不佳的女大學生在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容易疲憊、倦怠,從而產生不良的情緒體驗,最終導致抑郁水平的上升。 這一結果驗證了應激-易感模型,相關分析顯示, 負性生活事件和消極認知應對之間有正相關,消極認知應對可能可以增加應激反應水平,從而在負性生活事件(應激)和抑郁狀態(易感因子)之間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另外,本研究發現,積極認知應對不能顯著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間的關系, 這一研究結果和以往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劉小娟,陳沖,楊思,2010)。以往的研究表明,當個體使用消極認知應對更多時,采取積極認知應對則會相應減少(劉啟剛,2009)。當面對較為嚴重的負性生活事件時, 由于女大學生使用消極認知應對較多, 負性生活事件提高了抑郁水平,女大學生已經處于不愉快的心境中,這時采取積極重評等事后的積極認知應對很難再改善不良的心境,所以積極應對不具有調節作用。
此外, 以往的研究忽視了消極認知應對在什么程度上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當消極認知應對的取值低于平均值1.06 時才能顯著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間的關系。 這一結果進一步驗證了情緒調節的情境理論, 當消極認知應對水平沒有過低時,還未超出自身能力資源范圍,因此對抑郁和負性生活事件的調節作用不明顯。 這說明過低的消極認知應對在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間的關系中調節作用不明顯。 推測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 過低的消極認知應對對女大學生心理和生理的影響不明顯, 因此消極認知應對需要達到一定的水平才能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間的關系。
4.3 啟示
在本研究中,認知應對的調節作用得到驗證。消極認知應對在低于平均值1.06 時開始在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間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當女大學生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 過多地采用消極認知應對會增加他們的抑郁水平。 這啟示女大學生在學習生活中多采取科學有效的積極應對來面對負性生活事件, 學生工作相關人員應給予女大學生群體更多心理的支持和輔導, 針對大學生開設認知應對訓練等心理課程, 從而有效地預防女大學生抑郁水平的上升。
5 研究結論
在女大學生群體中,負性生活事件、抑郁、認知應對三者存在關聯,其中負性生活事件、抑郁、消極應對之間的相關度更高且顯著。負性生活事件、認知應對可正向預測抑郁。 消極認知應對在在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狀態間起調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