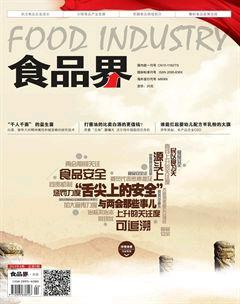大開眼界 美公司發明水變酒神器
2014-06-10 16:30:08
食品界 2014年4期
對于愛飲葡萄酒的人來說,這一釀酒神器帶給他們無數的方便和欣喜,只要在家就可以釀造葡萄酒,菲利普·詹姆斯和凱文·博耶發明了這款釀酒神器,他們兩個是商人同時也對酒特別癡迷。消費者只要在其中加入1~2種物質,就可以在3天內把水釀成酒,而且發明者表示,用這款釀造神器釀出來的酒和從市面上買的沒有任何不同。
這款釀酒神器由泵、通風口、傳感器和微處理器上的電子元件組成,它可以將水、酵母和葡萄濃縮汁混合之后釀成美酒。瓶子可以通過藍牙和智能手機相連,并且通知用戶什么時候釀造結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