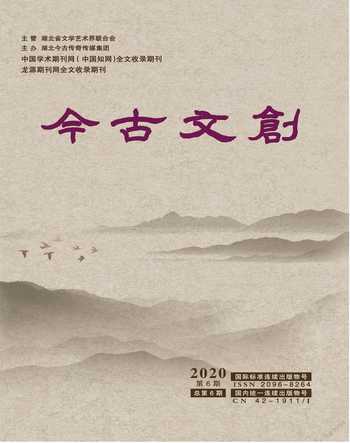試析春秋筆法在《桃花扇》中的體現
劉冰
【摘要】 春秋筆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下一個極具特色的顯性話語,廣泛存在于以倫理教化為旨歸的古典戲曲、小說的創作及評點當中,歷來頗受研究者矚目。其“懲惡勸善”的褒貶大義與委婉曲折的表達方式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主題選擇、敘事策略及藝術構思等方面均產生著深遠影響。在明清兩代的文人戲曲當中,存在著大量借用春秋筆法進行創作的例子,孔尚任的《桃花扇》便是其中一個典型。春秋筆法在《桃花扇》中具體體現為筆削手段的靈活運用,冷峻客觀的敘事態度以及篇章布局上的史家體例。
【關鍵詞】《桃花扇》;春秋筆法;筆削手段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06-0014-03
一、春秋筆法概念流變
春秋筆法經歷了一個由經及史、由史及文的復雜流變過程,是一個經歷代經學家、史學家不斷開拓完善的概念范疇。由最初孔子開創的“一字定褒貶”的寫作范例發展為左傳、太史公之筆以及文學意義上的深文曲筆。春秋筆法的概念存在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觀點一般寫作《春秋》筆法,指孔子在編訂《春秋》時所使用的那種“筆則筆”“削則削”,從中寄托“微言大義”的史家寫作范例;廣義的觀點泛寫作春秋筆法,指在一切敘事作品當中暗含褒貶,以一種委婉曲折的方式表達作者主觀思想傾向的文學創作方法。既包括“直而不污”、據事直書的一面,也包括“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曲筆的一面。實際上,春秋筆法的流變過程,即是由狹義到廣義的內涵擴大過程,如王基倫就在《〈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一文中指出:“源自《春秋》經而來的‘《春秋》筆法’,原是我國自發性的經學名詞,先后經由《左傳》《孟子》《公羊傳》《史記》乃至歷代文學理論家的詮釋之后,逐步邁入史書筆法及文學碑志傳狀寫法的領域,成為很重要的文學觀念。” 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論及的《桃花扇》中的春秋筆法,主要是指廣義上概念范疇。
二、春秋筆法在《桃花扇》中具體體現
(一)筆削手段的靈活運用
孔尚任雖然在《桃花扇·凡例》中標榜《桃花扇》對于史料處理的嚴謹:“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其地,全無假借。”但我們通過對史料的搜集比對可以發現,《桃花扇》中人事與史實之間出入之處頗多。梁啟超在批注《桃花扇》的過程中,對其與史實相去甚遠之處提出了批評,而我們認為,這些相去甚遠之處正是春秋筆法中的一大特色——筆削手段造就的結果。正是有了筆削手段,作者才可以自由地對筆下人物進行騰挪轉接,使得人物樹立起來,更好地為褒貶大義而服務。所謂“筆削”手段,“筆”即指直錄其事,秉筆直書;“削”即指“不錄”,包括“隱而不書”“諱書其事”“改書其事”,指對寫作材料進行有選擇的刪減。在《桃花扇》一劇中,孔尚任為了實現“懲惡勸善”的褒貶大義,運用筆削手段對重大歷史關節事件以“書法不隱”的良史之筆進行了秉筆直書,并對部分歷史人物進行了有選擇的裁剪、嫁接。
1.對奸佞馬士英人物形象的加工
為了收到懲創人心、使“亂臣賊子懼”的教化效果,孔尚任必須在劇本當中樹立鮮明的忠奸對立派別,并且給忠臣一定的抬高褒獎,給奸臣必要的口誅筆伐。正所謂“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還他個揚眉吐氣;那班得意的奸雄邪黨,免不了加他些人禍天誅;此乃補救之微權,亦是褒譏之妙用。”馬士英便是作者精心結撰勾畫的一個奸臣形象。《桃花扇》中的馬士英禍國殃民、喜好奉承,跟阮大鋮一道,構成了一對實打實的丑角形象。雖然歷史上的奸臣馬士英與《桃花扇》中所作所為大部分吻合,但為了加重馬士英身上的奸臣色彩,孔尚任將原本諸多不屬于馬士英的劣跡加諸到了其身上。
馬士英在《桃花扇》中為人詬病的一大過失為重用閹黨余黨阮大鋮,兩人臭味相投狼狽為奸,加速了南明王朝的滅亡。而歷史上馬士英之所以在做了弘光朝首輔之后啟用阮大鋮,卻是出于投桃報李的“報恩”目的。據史料記載,馬士英在萬歷四十四年考中進士正式開啟了宦海生涯,在崇禎五年被提拔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但僅到任一個月便因挪用公款賄賂權貴事發被流放邊疆,在賦閑期間,與因“魏忠賢逆案”被革職的阮大鋮相交甚歡。后在東林黨人、復社成員的活動周旋下,被罷相的周延儒得以復官,其中花費的銀錢萬兩主要來自阮大鋮的捐贈。阮大鋮請求周延儒為己翻案不成轉而舉薦馬士英,馬士英得以成功復官。出于投桃報李的心態,馬士英在弘光朝極力舉薦了阮大鋮,而上臺后的阮大鋮瘋狂打擊報復曾將自己打入“魏閹逆案”的東林士子,導致超綱混亂、民不聊生。《桃花扇》中將馬、阮并成,共列閹黨,而事實上,馬士英并非閹黨成員。阮大鋮迫害清流的罪狀,后人因“馬、阮”并稱而大多推到馬士英身上,對于這一點,《明史》記載中也提道:“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已居惡名,頗以為恨。”根據當時的一些史料記載,馬士英對江南的一些復社成員,并沒有抱有趕盡殺絕的敵對態度,反而啟用了一些才干優渥之人。馬士英曾言:“若輩講聲氣耶?雖然,孰予若?予吊張天如,走千里一月,為經紀其后事也,人誰問死天如也?”盡管張溥為東林領袖,一手創辦復社,但當時的東林諸子卻大多忙著去周旋周延儒的官位,張溥的后事是由奸臣馬士英一手操辦、憑吊的。由此可知,歷史上的馬士英雖不能稱得上是一個重情重義之人,但也絕非十惡不赦之輩。關于其賄賂權貴一案,其中還頗有隱情。據《烈皇小識》記載:“宣府巡撫馬士英,甫蒞任,冒侵餉銀六千兩。鎮守太監王坤疏發其事,士英逮問遣戍。例:巡撫到任,修候都門要津,侑以厚賄,贖緩不能猝至,則撮庫中正額錢糧應用,而徐圖償補,此相沿陋習,各省各邊皆然,不獨一宣府也。士英蒞任未幾,一時不及抵償,遂為王坤所糾。坤既以發奸為功,上亦心喜內臣之果能絕情面而剔積弊也,故凡言內臣者皆不聽。”崇禎朝時期官場形成了一條約定俗成的規定,凡是巡撫到任都要給京城權貴送以豐厚的錢兩,如果自己一時間拿不出那么多錢,那就挪用公中錢兩應用之款,之后再想辦法慢慢償還。結果內臣王坤出于邀功的目的告發了尚未來得及償還錢兩的馬士英,導致上任僅一個月的馬士英就這樣被罷免了。
馬士英在《桃花扇》中第二大罪狀為與阮大鋮一起迎立君德全虧、驕奢不堪的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桃花扇》第十四出《阻奸》當中寫到馬士英邀功心切,主動給史可法傳書商議立福王之事,史可法原本猶豫不決,后聽從侯方域“福王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論回絕了馬士英的提議。但歷史上的真實事實卻是史可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與馬士英一起迎立了福王。據侯方域《四憶堂詩集》卷五《哀辭九章·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開府都督淮揚諸軍事史公可法》所寫:“……福邸承大統,依次適允諾,應機爭須臾,乃就馬相度。坐失倫扉權,出建淮揚幕。進止頻內請,秉鉞威以消。”可知,在認為應當由福王繼承大統這件事上,侯方域與史可法持有相同的看法,而史可法并沒有爭取時機第一時間擁立福王,而是主動去與馬士英商議,導致馬士英搶占先機奪得擁立之功。侯方域的友人賈開宗在注釋中對該詩詩意做了闡釋:“甲申燕京之變,公為南京兵部尚書,掌機務。時弘光以福邸當承大統,倫序無可易者。公以強藩在外,不即決,乃就鳳陽總督馬士英謀之,而擁立功盡歸士英矣。”由此可知,迎立福王的罪責不應完全由馬士英一人承擔,孔尚任以“隱而不書”的春秋筆法抹去了忠臣史可法在迎立福王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此外,孔尚任對馬士英言行改動較大的一處為其抗清而亡的結局。既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將馬士英描繪得如此作惡多端死有余辜,那么就必須為其設計一個合適的結局以得到大快人心、懲惡勸善之目的,因而為馬士英安排的結局是在臺州山中被雷劈死,而事實上馬士英卻是在抗清失敗之后英勇就義而亡。史學家陳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對此持公允論斷:“惟士英實為弘光朝最后奮戰一人,與阮大鋮之先附閹黨,后復降清,究大有別。南京既覆,黃端伯被執不屈。豫王問,‘馬士英何相?’端伯曰,‘賢相’。問,‘何指奸為賢?’曰,‘不降即賢。’諒哉!馬、阮并稱,誠士英之不幸。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可為士英誦矣。”抗清名士黃伯端在臨刑之前所說的“不降即賢”未免失之簡單粗暴,但跟錢謙益等一眾剃發易服投降清廷的前明大臣比起來,馬士英畢竟沒有失去一個明朝官員應有的節氣。
2.對“有明三忠”之一左良玉的人物形象加工
左良玉是孔尚任精心刻畫的一大忠臣,在《桃花扇》中一出場便是一位忠君愛國、威武英勇的將領形象:“七尺昂藏,虎頭燕頜如畫,莽男兒走遍天涯。活騎人,飛食肉,風云叱咤。報國恩,一腔熱血揮灑。”但梁啟超在《桃花扇》第九出《撫兵》的批注中,卻以嚴厲的口吻指出《桃花扇》于左良玉袒護過甚。事實的確如此。歷史上左良玉一大污點便是治軍不嚴、軍紀散亂,放縱部下燒殺搶掠,百姓深受其苦。高斗樞在《守鄖紀略》中提到左良玉率軍追擊張獻忠軍隊時“左兵二三萬,一涌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污之狀不可言。”普通百姓“不恨賊而恨兵”。對于這一點,清代著名文學家王士禎也有論斷:“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于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為名,而并諱其做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昆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為作傳……愛及烏上之烏,愛及烏上之烏,憎及儲胥。噫,亦愚矣。”據明史記載,張獻忠在攜重寶賄左良玉時,甚至以“公所部多殺掠”來拉攏彼此的關系。由此可見左良玉軍隊軍紀敗壞可謂人所共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針對這些不利于左良玉形象塑造的史料非但采取“隱而不書”的方法,還對此多加諱飾。如在第十一出《投轅》中借柳敬亭之口為其辯白:“俺柳敬亭沖風冒雨,沿江行來,并不見亂兵搶糧,想是訛傳了。”甚至在第三十一出《草檄》中營造左軍軍紀嚴明、無人敢喧嘩的氛圍,借唱曲藝人蘇昆生之口說出:“今日江上大操,看他兵馬過處,雞犬無聲,好不肅靜。”蘇昆省深夜唱曲還被店家打斷:“客官安歇罷,萬一元帥聽得,連累小店,倒不是耍的。”
歷史上左良玉另一大污點是引兵東下被認為有謀逆之心。對于這一點,《桃花扇》極力刻畫左良玉就糧南京實屬被饑兵脅迫,無可奈何之舉。《桃花扇》第九出《撫兵》集中描繪了兵糧缺乏、人心浮躁的危機場面:“你聽外面將士,益發鼓噪,好像要反的光景。”直到左良玉發出“就糧東去,安歇營馬,駕樓船到燕子磯邊耍”的承諾,這一危機才安全度過:“慰三軍無別法,許就糧喧聲才罷,誰知俺一片葵傾向日花。”緊接著孔尚任借兩個士兵的對話暗示左良玉從此蒙上不白之冤,難免被人懷疑的無奈事實:“[副凈向末]老哥,咱弟兄們商量,天下強兵勇將,就扯起黃旗,往北京進取,有何不可![末搖手介]我們左爺爺忠義之人,這樣風話,且不要題。依著我說,還是移家就糧,且吃飽飯為秒。[副凈]你還不知,一移南京,人心慌張,就不取北京,這個惡名也免不得了。”孔尚任對左良玉袒護之心可見一斑。
(二)篇章布局上的史家體例
孔尚任在《試一出 先聲》里借老贊禮之口說出:“但看他有褒有貶,作《春秋》必賴祖傳;可詠可歌,正《雅》《頌》豈無庭訓。”直接把一部《桃花扇》傳奇當作《春秋》來看待。事實上,《桃花扇》的確突破了傳奇體制,沒有按照常規的傳奇框架進行結構,而是在篇章布局上借鑒了史家體例。
首先,是記事體例上對編年體的仿照。《春秋》為記史首先開創了編年體體例,敘事嚴格依從年、季、月、日的時間順序。《桃花扇》在每一出開頭均模仿《春秋》按照時間先后注明年月,如在第三出《哄丁》下標明癸未三月,第八出《鬧榭》下標明癸未五月,使其整部書的結構看起來更像是一部史書而非普通的傳奇。每一出結尾處的四句七言詩跳出劇情進行總結,又極類似《史記》的“太史公曰”。
其次,是人物群像的宏觀展現。史家記史永遠是著色分明、均衡用力地,不可能集中所有筆墨濃墨重彩地去突出刻畫某一個英雄人物,在人物形象展現上具有群像性特征。《桃花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同樣具備史家的群像性特征。縱覽全書,描寫主人公侯方域、李香君離合之情的為第二出《傳歌》、第五出《訪翠》、第六出《眠香》、第七出《卻奩》、第十七出《拒媒》、第二十二出《守樓》、第二十三出《寄扇》、第二十四出《罵筵》、第二十五出《選優》、第二十八出《題畫》、第四十出《入道》,所占戲份與代表興亡之感的史可法、左良玉等人戲份差之不遠,諸多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呈現方式上具有接踵而來、設色均勻的史家群像特征。
(三)冷峻客觀的敘事態度
雖然《桃花扇》一劇有著鮮明的忠奸對立,但作者對人物的呈現始終采取了一種冷靜客觀的敘事態度。作者的主觀好惡態度隱于文后,行文用筆做到了“不動聲色”。作者只負責客觀呈現不負責表達愛憎,觀眾只能憑借劇中人物的言談與行動對人物的道德品格做出個人判斷。孔尚任對客觀敘事有著極為強烈的自覺意識,早在開篇的《試一出 先聲》里便將自己與敘述者進行了隔離。孔尚任先是借老贊禮之口說出:“昨在太平園中,看一本新出傳奇,名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營造出一種《桃花扇》已經先于敘事者存在的假象,緊接著又將敘事的權利賦予老贊禮:“今日冠裳雅會,就要演這本傳奇,你老既是舊人,又且聽過新曲,何不把傳奇始末,預先鋪敘一番,大家洗耳?”從而大大疏遠了自己與敘事者的關系,使得故事的演繹更少作者感情的直接流露,而以一種更為冷靜客觀的旁觀者視角緩緩鋪展開來。
其次,《桃花扇》大量采用了限知視角進行敘事。譬如第十出《修札》 楊龍友驚慌失措地向侯方域傳遞消息:“兄還不知道嗎?左良玉領兵東下,要搶南京,且有窺伺北京之意。本兵熊明遇束手無策,故此托弟前來,懇求妙計。”作為觀眾的我們因為看過左良玉“誰知俺一片葵傾向日花”的內心剖白,所以明白楊龍友之說為訛傳,但身處故事當中的楊龍友根據自身見聞所得出的判斷卻是左良玉要謀反。作者就這樣將自己深隱于文后,讓人物自己講話自己判斷,完全淡化了作者的存在感,從而使敘事態度達到真正的冷靜客觀。
三、結語
《桃花扇》作為中國戲曲長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跟情致浪漫、一往而深的《牡丹亭》《長生殿》相比,呈現出了迥異的藝術特色。其較少虛幻色彩,敘事視角聚焦于發生不久的現實人生,有著其他同樣優秀的戲曲作品所不具備的深廣的思想與察補時弊的救世情懷。而這一切,跟作者對春秋筆法的嫻熟使用多少脫不開干系。厘清春秋筆法在《桃花扇》中的具體體現,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桃花扇》主題思想、透視孔尚任寫作壸奧,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注釋:
①王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孔學研究,2005年,第00期。
參考文獻:
[1][清]孔尚任著,李保民校點.云亭山人評點桃花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陳才訓.“春秋筆法”對古典小說審美接受的影響[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