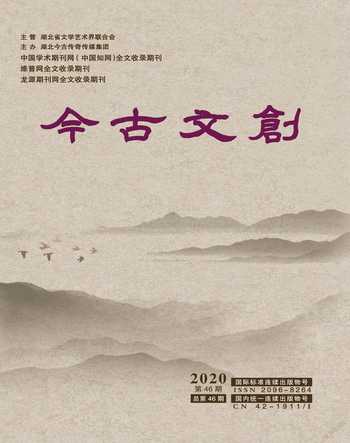圖像、文字、言語語言符號系統的關系
【摘要】 本文試圖從漢字之“象”出發,闡釋語言、思維與符號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論述圖像、文字、言語符號系統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又彼此相對獨立的關系。最后提及圖像作為能指具有生產意義的能力和特質,說明在后現代社會越來越顯現出其優越地位的原因。
【關鍵詞】 “象”;圖像;文字;語言符號
【中圖分類號】H1?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46-0044-03
一、從漢字之“象”說起
中國社科院王樹人提出,象思維“指運用帶有直觀、形象、感性的圖像、符號等象工具來揭示認知世界的本質規律,從而構建宇宙同一模式的思維方式。” “象思維將宇宙自然的規律看成是合一的、相應的、類似的、互動的,借助太極圖、陰陽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河圖洛書、天干地支等象數符號、圖式構建萬事萬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鮮明的整體性、全息性。” ①《周易·系辭上專》中提道:“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②象形字(甲骨文等)是漢字的最基本形態。名詞是造字之初首先出現的詞性,而后的詞性則是由名詞詞義的引申。最初的名詞,都是指向某物的,不是抽象名詞,而是具體名詞,即是通過事物本身的形象來表示它。隨著抽象化程度的升高,字形越來越簡化,詞義越來越豐富,人們的思維模式也越來越超象。
以一首中國現代詩——陳黎的《戰爭交響曲》 ③為例,以便解釋漢字之“象”的同時,引出各符號系統之間的關系的論述。
這首詩全詩共分3節,每節16行,全詩只有四個字形相近的字組成:兵、乒、乓、丘。第一節由每行24個、共384個“兵”整齊排列而成;第二節每隔若干“兵”便夾雜著幾個“乒”和“乓”,出現頻率由低轉高,第十一行開始出現大面積的空白,“兵”字消失,“乒”和“乓”字也逐漸減少;第三節由每行24個、共384個“丘”字整齊排列。
具體來講,“兵”即士兵,16×24的排列方式表示一個整齊行進的軍隊;第二節中,“乒”“乓”在字典中的本義只是一個象聲詞,在本詩中具有了雙重含義:作為象聲詞,它們在本詩中代表戰斗中的槍炮聲;與上一節的“兵”聯系起來,在字像上它們表示了在戰爭中瘸腿的戰士們。字里行間出現的空白和停頓,也具有形象化的意義,代表了士兵們陸續死亡。“丘”,指墳墓,士兵們從肢體的殘缺最終變成了戰場上的土冢,整首詩暗示著戰爭的慘烈和對生命的摧殘。
從聲音角度,詩以“戰爭交響曲”為題,可以將詩看成交響樂的三個樂章。“乒”與“乓”代表戰爭中的槍炮聲,最后一切歸于靜默和虛無,變成寂寥的墳墓。
二、語言、思維和符號的關系
在論述符號系統之間關系之前,有必要先簡單地對語言、思維和符號的關系進行一點說明。
語言和思維具有同一性這一表述是建立在語言決定/影響思維和思維決定/影響語言的分歧上。而實際上,不論是誰決定誰、誰影響誰,前提都是將語言和思維放在一個統一體的角度來講的,二者首先不能是絕對獨立存在的個體,并且事實證明他們也的確不能離開彼此存在。而對誰決定誰、誰影響誰這個分歧的論證,往往集中在二者的發生學角度,去討論如何產生和誰先誰后的問題,即到底是先有語言還是先有思維。
但事實上,拋開誰先誰后的開端,在歷史長河里,不論是群體的語言與思維,還是個人的言語行為和思維方式,都存在此消彼長的現象和時期,因此對這兩個分歧的研究者就總能找到例證及反例,來論證自己并駁斥對方。不可否認,思維和語言總是如影隨形的。
當提到語言的時候,總是將其與文字混說,在論證語言與思維關系的時候,人們要么拿語音層面論證,要么拿文字層面論證。但文字只是語言的“第二重符號系統”,語言既然闡明思維、并創造意義,那么一切能闡明思維、創造意義的東西都可以稱之為語言嗎?圖像、文字、言語、聲音都是語言符號系統。人的思維總是伴隨著語言的,每一種語言符號對思維的表達存在不同的側面。因為人們的思維和語言,不會直接面對意義,而是用各種語言符號系統來面對意義。人們可以用圖像來表達語言,可以用文字來表達語言,可以用言說來表達語言。但是它們都是語言的一種符號化形式,也是思維的符號化呈現,但也是對思維的不同面的切割。
三、圖像語言、文字語言、言語等語言符號系統之間可以互相轉化
“文者,物象之本。”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造字之初,漢字從一些“象”轉化而來的。也就是說,起初人們的思維過程是,先有了對某物的“象”的認識,再有了對這個象的符號化表示。因此是一個“象——字”的過程。漢字最初通過象形的方式造字,隨后又根據各種需求對其進行會意、指事、假借、轉注等,不斷發展成現在的漢字系統。因此,最初的漢字,具有了某種圖像的性質。而西方的表音文字,從其本身不能窺見物的形象,從二者的造字思維能夠窺見在中西思維的不同。上文提到的《戰爭交響曲》一詩曾入選美國新版大學文學教科書Literature: Craft and Voice,由于漢字字形、字義的獨特性,除題目外,這首詩是無法譯出的。曾有網友將其翻譯成:a man(代“兵”), ah man(戰斗驚呼), amen(阿門)。可以說這樣改寫雖然巧妙地將字音字形變化轉變為英文,但是如果不看詩題,“man”便不會被人認為是“兵”;沒有結構上的排列組合,就不能表達出“軍隊”的意象;在字形上,“兵”表現出的士兵們雄赳赳的精神氣質也埋沒其中。
當然,這并不是說西方的文字就不能轉化為圖像,但是根據他們的造字法與形象化思維之間的聯系程度,漢字轉化起來也許要比表音文字轉化起來更容易。
無論中西,當有了整個文字系統,文字組合起來形成有意義的一段話時,人們先看到文字或者聽到它的聲音,然后浮現出對于這段文字的想象。這時候人們的思維過程是“字——圖”的過程。因此接受者在接受語言時,例如抒情或敘事時,會有意無意地將文字轉化為動態變化著的圖像。這種轉化不存在能量守恒,并且會有意義的損益。
四、圖像語言、文字語言、言語等符號系統之間具有相對獨立性
正如上述所說,他們之間的相互轉化,是有意義損益的,因此不可能在兩種語言系統之間進行完全對等的轉化。例如在“象——字”的轉化階段,并沒有讓“象”完全變成“字”的形態,還保留了其他各種各樣的形態,例如器皿上的花紋、洞穴上的涂鴉、部落圖騰等,他們有些至今還存在并且繁榮發展著。
那么,為什么人們造字之初就能夠將物象轉換成文字,現在卻很難將文字轉化為具體物象?
例如,在影視改編中,人們將文字敘事中的人物形象轉化為熒幕演員,多少會讓人感到對其形象有所損失。
簡言之,物象不是圖像,物象接近物,或是物本身;圖像是對物本身的再創造,是思維以某種方式對某物的感受,但不流連于對物的模仿。因為最初,世界作為物象,承擔的是所指的角色,人們希望用音、形、書寫物等對其進行表達,指向這個所指。但如今圖像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質上和量上都遠遠超出了給某事物命名、描述等簡單地將能指與所指緊密結合的行為,人們的所指變得復雜,所指指向的不一定是物象世界,也許是夢,或是某種情緒、情感、主張、立場等。圖像世界不再是一個“原生態”世界,對圖像的創造能力遠遠快于人們對客觀世界的塑造。所以,圖像不滿足于成為所指,而是和文字一樣,是一種能指。
總有言語和文字是不面向圖像的,例如理論;也總有圖像不面向文字和言語,例如抽象畫、后現代藝術裝置等等。他們不能或者不愿意被轉化。如今,似乎看不出,到底是文字還是圖像或其他占據主導地位。人們不再滿足于進行“字——象”之間的這種轉換了,而是更希望圖像直接呈現在面前,而不是靠其他語言符號的視覺想象。因此,第一,他們有時可以互相轉化,但是他們不以互相轉化為目的;第二,他們在時間的產生上也許存在先后,但他們在地位上不存在先后。他們一旦作為能指的角色存在,就都指向所指和意義。這樣,文字和圖像作為兩種符號,他們不再相互轉化面向對方,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面向對象,或者說對象的意義。
五、圖像作為能指生產意義
維特根斯坦說,“一個名稱的含義有時是由指向它的承擔者來解釋的”。圖像和聲音、文字、言語,都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媒介,或者說,媒介也承擔了“解釋”意義的效果。如前所述,圖像成為一種能指,并生產意義。“如何去看”決定了“看到了什么”,因此,圖像可以生產不同的意義、不同的所指。
假設,兩位水平相當的藝術家,同時用寫實的、摹仿手法畫同一個物體,兩幅畫可能差別不大,但如果用抽象的手法畫同一個物體,二者差別會很大。他們抽象的角度、程度、能力等各不相同,用電影來描述事件也是一樣。因為前者畫布上的那個東西,和現實生活中的物,非常接近,它和物幾乎可以相當;但后者則出現變形,它自己變成能指,其抵達的所指,各不相同,在后者這里,是人們對“物”的一種闡釋,人們用畫的方式來闡釋物(象)或者事件。圖像本身成為能指,但這個能指不再指向物本身,而是自身又去生產新的所指,因此所指是什么取決于人們如何結構能指、如何塑造這一圖像,也就是以什么方式闡釋原本的那個物。方式問題,是一個思維問題,說到底,各種語言符號系統都是思維的某種方式,以某種或某幾種思維方式來結構一個能指,生產意義。圖像作為一種語言符號,也是一種思維的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在當下社會中越來越重要。
上文說到,各種類型的符號各自表達意義,但他們都是思維想要表達的意義的某個側面,因此他們既可以互相轉化、也有必要獨立存在,當然更需要結合。這一結合,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圖像或者視覺符號在后現代變得尤為重要。在后現代以前,文字、言語、聲音符號的結合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音-形結合形成語詞,音調-歌詞形成歌曲;在中國古代,詩畫結合是一種傳統,詩歌的吟唱也是一種傳統。隨著攝影技術、后現代藝術品(裝置)的出現和發展,人們在視覺感官上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當然,不論什么年代,人們對某事物的感知總會伴隨著視覺化,不論是不是將事物實體化,都要對其進行視覺想象,這取決于人們對世界最直觀的感受方式——看。人們能意識到,世界呈現給大家的是空間化的世界,時間的流動必須置于這個空間內才有意義,而圖像世界,正在變得空間化。
文字、言語、聲音都是線性的,它們也能構筑空間,但是他們構建空間的能力有限,大部分時候靠視覺想象而不是產生視覺接觸,但圖像世界則具有更強的空間結構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乘著科學技術之翼,具有呈現視覺想象、使視覺想象實體化的野心。這種空間結構能力與其他語言系統相結合,將產生時空化的效果,人們的世界、思維方式、闡釋世界和生產意義的方式變得一致,即時空化。
注釋:
①王禹:《從思維到漢字象思維的審美特征研究》,《藝術科技》 2019年第3期,第98頁。
②黃壽祺、張善文譯注:《周易譯注·系辭上傳》(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頁。
③陳黎:《戰爭交響曲》,《島嶼邊緣》,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頁。
參考文獻:
[1]段煉.視覺文化與視覺藝術符號學:藝術史研究的新視角[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
[2](奧)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陳嘉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3]劉燕.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述評[J].外國語文(雙月刊),2012,28(02):89-92.
[4]楊朝春.語言與思維關系研究述評[J].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5,(10):1-5.
[5]王禹.從思維到漢字象思維的審美特征研究[J].藝術科技,2019,(03):98.
[6]黃哲雅.語言與思維的關系[J].青年記者,2015,(04):63.
[7]陳曉強.論漢字的“象”[J].古漢語研究,2015,(01):63-68.
[8]魏慧萍.論漢字的“形”與“象”[J].漢字文化,2001,(04):30-32.
[9]潘云萍.漢字“象”的分析[D].青島:中國海洋大學,2010.
作者簡介:
劉藝多,女,漢族,上海大學,文藝學專業,研究方向:20世紀西方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