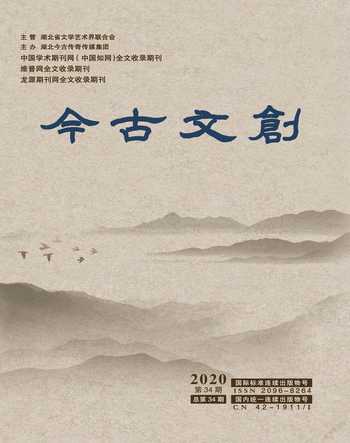對(duì)現(xiàn)代性和身體的反思
【摘要】 到了20世紀(jì),啟蒙精神、理性和科學(xué)技術(shù)自身發(fā)展演變成工具理性,科技的進(jìn)步使得世界呈現(xiàn)出井然有序的面貌,然而現(xiàn)代秩序下,身體被理性忽視的問(wèn)題越來(lái)突出。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詩(shī)人格奧爾格·海姆的敘事散文Jonathan通過(guò)變形怪誕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外化主觀情感,揭示現(xiàn)代理性話語(yǔ)對(duì)身體的戕害。詩(shī)歌、戲劇是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文學(xué)藝術(shù)的高峰,針對(duì)短篇敘事的研究較少,Jonathan與海姆表現(xiàn)主義詩(shī)歌構(gòu)成對(duì)話關(guān)系,表現(xiàn)身體與空間的張力,聚焦主人公的主觀宣泄,探討現(xiàn)代語(yǔ)境下身體轉(zhuǎn)變的思想史,揭示現(xiàn)代文明與個(gè)體情感的沖突。
【關(guān)鍵詞】 詩(shī)歌互文;空間規(guī)訓(xùn);身體
【中圖分類號(hào)】I107?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0)34-0029-03
格奧爾格·海姆(1887-1912)是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時(shí)期杰出的詩(shī)人。受到法國(guó)象征派的影響,他的語(yǔ)言簡(jiǎn)練,比喻生動(dòng)形象,作品想象力豐富,中心主題是現(xiàn)代文明下大都市的冷漠與無(wú)情,表現(xiàn)疾病、孤獨(dú)、絕望和死亡。他的一生短暫,為表現(xiàn)主義文學(xué)留下了7部詩(shī)集,1部敘事散文集,1部戲劇和1篇雜文。
敘事散文(Erz?hlprosa)Jonathan收錄在海姆的中篇小說(shuō)集Der Dieb第5章中,于1913年,即詩(shī)人逝世后的第一年首次出版。輪船上的機(jī)械師Jonathan四處游歷,經(jīng)歷豐富,帶著一名法國(guó)醫(yī)生前往利比里亞尋找一種珍稀蘭花的返航途中,遭遇海上風(fēng)暴,他跌下鍋爐房,被活塞桿弄斷了兩條腿。命運(yùn)把他丟到漢堡一家現(xiàn)代醫(yī)院進(jìn)行救治,在這里他像犯人一樣被囚禁在病房中,飽受病痛與孤獨(dú)的滋味,機(jī)緣巧合下他結(jié)識(shí)了隔壁病房的女孩,在同這位女病友交流的過(guò)程中病房里的恐懼消失,他感受到愛(ài)。但是醫(yī)生卻以靜養(yǎng)為名禁止兩人交談,此外醫(yī)生診斷Jonathan將面臨終身殘疾,擊碎了他最后的希望。緊接著Jonathan腿傷急劇惡化,他因?yàn)殡p腿被鋸變得麻木羞忿,這也導(dǎo)致死亡加速到來(lái),在女孩的呼喚和死神的迎接中他走向了死亡。
一、與表現(xiàn)主義詩(shī)歌的對(duì)話關(guān)系
相較于表現(xiàn)主義詩(shī)歌的影響力,海姆的敘事作品表現(xiàn)不算亮眼。一是因?yàn)閿⑹律⑽牡膬r(jià)值和評(píng)估的美學(xué)尺度相較詩(shī)歌更為清晰,此外他的中篇小說(shuō)經(jīng)常被認(rèn)為是詩(shī)歌的附屬品,所以對(duì)抗表現(xiàn)主義詩(shī)歌時(shí)顯得力度不足。Fritz Martinis認(rèn)為,海姆的短篇小說(shuō)“敗在了以極端的表現(xiàn)力加以說(shuō)明一切的夸大的意愿之中”,Inge Jens卻在他的論文中作出了相異的判斷。海姆的短篇小說(shuō)反響平平的原因之二在于其文本的敘事結(jié)構(gòu),理解表現(xiàn)主義詩(shī)歌有表現(xiàn)主義圖像作為背景,難度不大,然而散文卻拒絕被納入其中。所以對(duì)海姆短篇小說(shuō)文本的分析仍存在一定的困惑和不解。筆者試從與表現(xiàn)主義詩(shī)歌的對(duì)話關(guān)系中揭示表現(xiàn)主義時(shí)期敘事作品與詩(shī)歌的共性,分析表現(xiàn)主義敘事作品中對(duì)人的主觀感受的表現(xiàn)美學(xué),探討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身體與話語(yǔ)空間。
盡管出版商Ernst Rowohlt在海姆死后出版了中篇小說(shuō)集Der Dieb,但是一開(kāi)始他就表現(xiàn)出對(duì)這些敘事作品的懷疑。在給海姆的信中他寫道:“對(duì)于一本只涉及瘋狂,疾病,癱瘓和尸體的書來(lái)說(shuō),甚至不可能贏得一小部分讀者和顧客。” ①出版之后并沒(méi)有出現(xiàn)出版商的擔(dān)憂,相反,批評(píng)家都認(rèn)為海姆的詩(shī)歌和散文具有同步性:詩(shī)歌從一開(kāi)始就構(gòu)成了散文接受時(shí)的期待視域和讀者視角。“短篇小說(shuō)是否超越詩(shī)歌”這一論題也被提出。筆者認(rèn)為高下之分,超越之見(jiàn)實(shí)無(wú)必要,倒不如將他們的位置擺正放平,從互文性角度看待海姆詩(shī)歌和散文的同步,本篇研究的短篇小說(shuō)中也有表現(xiàn)主義詩(shī)歌的蹤跡,與海姆的組詩(shī)《發(fā)燒醫(yī)院》(Fieberspital)構(gòu)成互文對(duì)話關(guān)系。
詩(shī)歌文本短小精悍,容量有限,深層次的意義需通過(guò)隱喻表現(xiàn)出來(lái)。完整的人類是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詩(shī)歌中永恒的主題,表現(xiàn)主義文學(xué)以“時(shí)代的激情與痛苦,意志與渴望②”為抒發(fā)對(duì)象,產(chǎn)生于思想?yún)T乏,冷漠機(jī)械的年代。這個(gè)時(shí)代中人們感受到的無(wú)能為力越來(lái)越清晰。人類運(yùn)用理性,科學(xué)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的創(chuàng)造,編織出一張巨大的網(wǎng),人類黏附其中反被其所噬。詩(shī)人敏感的神經(jīng)已經(jīng)清晰地感受到愛(ài)被剝奪,這一切都是由高傲,冷漠的人一手造成。在碾壓過(guò)的詩(shī)行中海姆制造出“恐懼、腐爛和死亡景象③”。用生動(dòng)的比喻,簡(jiǎn)練的語(yǔ)言和豐富的想象力將機(jī)械文明中死氣沉沉的暗色調(diào),可怖的意象揉進(jìn)詩(shī)行,表達(dá)了他對(duì)人性的審視,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思考。雖然在這組詩(shī)中病人和醫(yī)生這組指向明確的詞在詩(shī)中隱而不見(jiàn),但是通過(guò)抓取詩(shī)行中的隱喻和換喻,病人和醫(yī)生這兩組形象慢慢浮現(xiàn):病人是“疾病”(V1,Z3),“在醫(yī)院通道中蹣跚的瘦削木偶”(V1,Z3),“白粉筆寫下的數(shù)字”(V2,Z1),醫(yī)生是“冰冷的亞麻布上吐絲結(jié)網(wǎng)的蜘蛛”(V3,Z1),“緋紅額頭上布滿的皺紋”就像“耕犁過(guò)的農(nóng)田,燃燒著死亡的朝霞”,它們的“背部裂開(kāi)一道黑縫”,里面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扼住喉嚨”。(V6-10)裂開(kāi)的這道黑縫中充斥著病人的痛苦與孤獨(dú),形成漩渦,病人在醫(yī)院里無(wú)法痊愈,這個(gè)漩渦加速死亡,死神在其中顯現(xiàn)。詩(shī)人嗅到欣欣向榮的人類文明中暗藏的腐敗氣息。
而敘事文本依賴一定的時(shí)間規(guī)律建構(gòu)敘事秩序,敘事的本質(zhì)在于凝固,保存,創(chuàng)造或超越時(shí)間。文本開(kāi)篇交代主人公“在病房可怖的孤單中”躺了三天,一閉眼睛“就會(huì)聽(tīng)到墻上的時(shí)間慢慢下滲”(S.42),病房的孤獨(dú)使得對(duì)時(shí)間的主觀感受變得遲鈍麻木。敘事在這種延長(zhǎng)的時(shí)間節(jié)奏中慢慢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環(huán)境色調(diào)昏暗慘淡,充斥著令人不適的景象。Jonathan被生活的花園丟出,“被遺棄在孤獨(dú),黑暗,悲涼的秋夜,冬天,死亡和永恒的地獄之中” (S.44),被醫(yī)生禁止同隔壁病房的女病友交談,宣判終身殘疾后他終于“發(fā)出了一陣可怕的,拉長(zhǎng)的哀嚎”(S.54),發(fā)出了表現(xiàn)主義那聲驚悚的吶喊。Jonathan用極具夸張地藝術(shù)變形手法進(jìn)行主觀感受的表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和意象中同詩(shī)歌進(jìn)行對(duì)話,走廊上的響鈴響三下是死亡的符號(hào),死亡站在每張病床的旁邊,病人是帶著注釋眼睛的數(shù)字,病痛從墻壁中伸出細(xì)削泛白,不住抖動(dòng)的手指,病人的呻吟是可怕的音階,上下起伏,手里拿著嗎啡注射器,晃動(dòng)藥水瓶的白衣護(hù)士像古怪禮拜里的僧侶,他們供奉著站在醫(yī)院屋頂上的死神。這些視覺(jué)和聽(tīng)覺(jué)上的意象作為 “隱喻存在” ④從屬于主人公的知覺(jué),再現(xiàn)了主人公的內(nèi)心世界,將需要表達(dá)的感情進(jìn)行物化,增強(qiáng)了審美情趣,留下大量想象空間,敘事張力得到強(qiáng)化。
二、空間規(guī)訓(xùn)下身體的變形
福柯認(rèn)為規(guī)訓(xùn)是在一個(gè)“人造的”,“空的”空間中運(yùn)作的。現(xiàn)代安全依賴諸多既定的物質(zhì)條件,病房這一人造密閉空間將風(fēng)險(xiǎn)和不便降低到最小,實(shí)現(xiàn)對(duì)病人的規(guī)訓(xùn),整個(gè)敘事基本上沒(méi)有游離于醫(yī)院病房之外。病房空無(wú)一人,病房里大大的鐵床張大了嘴巴,吞噬病人;病人自從進(jìn)入病房的那天起,就被遺棄在孤獨(dú),黑暗,冬天,死亡和永恒的地獄之中,疾病帶來(lái)的痛苦使得主人公內(nèi)心極度渴求人性的關(guān)懷,然而關(guān)心往往是遲到的,是沒(méi)有溫度的。主人公直言歐洲先生們(醫(yī)生)對(duì)病人的關(guān)心少得可憐,將病人囚禁在孤獨(dú)中,禁止病人間的溝通,要求服從病房規(guī)定。醫(yī)學(xué)話語(yǔ)企圖將生命塑造成“緘默的尸體”,醫(yī)生在其中發(fā)現(xiàn)和展示身體的秩序,解開(kāi)生命的秘密,“您必須及時(shí)做好終身殘疾的準(zhǔn)備”,這種目光聚焦于身體之上的平面式的、冷靜客觀的話語(yǔ)得出了疾病的確切性。
空間意識(shí)的覺(jué)醒后人感受到的現(xiàn)時(shí)的空間是產(chǎn)生孤獨(dú)和無(wú)助感的直接原因。時(shí)針走得越來(lái)越慢,對(duì)于時(shí)間的感受被無(wú)限延長(zhǎng),這種感受被黏附在空間之中,“他閉上眼睛的時(shí)候,就會(huì)聽(tīng)到墻上的時(shí)間慢慢往下滲,就像昏暗的地窖洞里慢慢聚攏的水珠滴之不盡(S42)”,病房讓他深陷可怖的孤單中。他希望有人向他伸出手,有人給他安慰,有人對(duì)他溫聲細(xì)語(yǔ),然而他痛苦的呻吟遭到嚴(yán)禁。身體必須破壞這一封閉空間的完整性,才有可能重獲關(guān)懷。“門開(kāi)了”,空間的裂痕下暗藏著主人公沖破空間束縛,召喚人性溫暖的嘗試。透過(guò)門的縫隙Jonathan接觸到外界投射的進(jìn)來(lái)的目光,悄然升起了Jonathan心中的一絲希望。在昏暗的燈光中,他看到了隔壁病房的女病友,他們互相問(wèn)候,這是短暫的,稍縱即逝的(flüchtig)的問(wèn)候,是幸福的符號(hào)(S44)。
對(duì)于主人公來(lái)說(shuō),封閉空間是恐懼的源頭,而身體的特征在于“非空間化”“非固定化”,“非轄域化”。身體和密閉的空間永遠(yuǎn)處于一種緊張狀態(tài),身體總是試圖沖破空間的束縛,正是在這種對(duì)抗中,身體與空間達(dá)成臨時(shí)的平衡。⑤但是這種暫時(shí)性的和諧在規(guī)訓(xùn)的話語(yǔ)中敗下陣來(lái),兩人的交談違反了病房規(guī)則,“病人應(yīng)該靜養(yǎng),他們應(yīng)該休息,也應(yīng)該保持安靜”(S47),空間再次封閉。更糟糕的是,主人公的雙腿在繃帶的束縛下腫脹腐爛,他拉響了死亡的符號(hào)——按三次鈴,半小時(shí)后,他被永久地剝奪了行走的權(quán)力,“曾經(jīng)是腿的地方,現(xiàn)在裹著厚厚的浸滿血液的白布。”
交流中斷了,孤獨(dú)再一次侵襲他,取而代之的是Jonathan極端的主觀想象:“房間的墻紙好像動(dòng)了幾下”,地下的墻紙碎了,從地下鉆出許多小矮人,很快就填滿了房間,所有的墻越隔越遠(yuǎn),最后消失在鉛灰色的地平線中。空間完全消失不見(jiàn),Jonathan赤身裸體地空地上的一副棺材上,他拖著腳步跟著死神穿梭在可怕的黑暗之中(S.59-62)。
三、機(jī)械文明與現(xiàn)代身體觀
西方傳統(tǒng)話語(yǔ)體系下一直強(qiáng)調(diào)身體與靈魂的對(duì)立,身體一直被排斥,被貶黜,柏拉圖認(rèn)為“保證身體需要的那一類事物是不如保證靈魂需要的那一類事物真實(shí)和實(shí)在的” ⑥。理性主義認(rèn)為,知識(shí)和真理是意識(shí)和自然互動(dòng)的產(chǎn)物,身體是動(dòng)物性的,是反智的因而排斥身體。現(xiàn)代以來(lái),尼采宣揚(yáng)一切從身體出發(fā),要“以身體為準(zhǔn)繩” ⑦,靈魂和意識(shí)是被發(fā)明的,而身體才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身體就是生命本身,身體和力量是一體的,“身體因?yàn)槠滏覒颉⑽璧负透行缘牧W(xué)效果,因?yàn)槠浼ち业膭?dòng)態(tài)性,它就不再表現(xiàn)為井然有序、循規(guī)蹈矩。⑧”
主人公在回憶中建構(gòu)了對(duì)一段充滿個(gè)人和異域色彩的經(jīng)歷:返鄉(xiāng)途中他曾在非洲一所臟臭、落后的醫(yī)院因病滯留4周,但是在這里,他并不是孤獨(dú)一人,當(dāng)?shù)氐牟∪嗽诖采陷d歌載舞,死亡前還要再一次高高地跳起。回憶是基于此在的需要,是現(xiàn)下感受和過(guò)去經(jīng)歷的積壓。在建構(gòu)的回憶中,病人的身體在非洲社會(huì)中是有力量的,是歡樂(lè)的,即使要面對(duì)死亡,仍以一種跳躍、歡騰、舞蹈的形象出現(xiàn),Jonathan對(duì)此表現(xiàn)出迷戀和向往,在哪里他們永遠(yuǎn)不會(huì)獨(dú)自一人,在那里他們總能聊上幾句。這種以自然天性、情欲享受為主導(dǎo)的價(jià)值認(rèn)同彰顯了身體與力量結(jié)合的美學(xué),身體是生命的限度,以生命為由的各種意義的發(fā)散正是基于身體這一基礎(chǔ),身體是自我的一個(gè)標(biāo)志性特征⑨,即使遭受疾病,身體也不是聽(tīng)?wèi){理性觀念驅(qū)使的被動(dòng)機(jī)器,這一價(jià)值取向與主人公當(dāng)下所在的以理性價(jià)值為主導(dǎo)的現(xiàn)代文明社會(huì)形成強(qiáng)烈反差——?dú)W洲對(duì)疾病衛(wèi)生的態(tài)度極為謹(jǐn)慎,主人公被隔絕在封閉空間內(nèi),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得到的關(guān)心也少的可憐。比起惡劣的醫(yī)療條件,將人囚禁在孤獨(dú)中更為可怕,現(xiàn)代醫(yī)學(xué)文明空間的秩序是克制的、理性的,身體處處受到管制,病房是單個(gè)地隔離空間,交流總是發(fā)生在固定的時(shí)間,特定的對(duì)象之間,身體成了只是需要被治愈的對(duì)象,然而聲嘶力竭的痛苦得不到回應(yīng),極端壓迫對(duì)疾病的恢復(fù)有害無(wú)益,孤獨(dú)比疾病、死亡更加可怕。
孤獨(dú)感也是現(xiàn)代人普遍的精神疾病,是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的產(chǎn)物。理性的思考,知識(shí)的豐富雖然帶來(lái)科學(xué)進(jìn)步,物質(zhì)繁榮,但是卻抹去了人的痕跡。海姆正是借主人公之軀,表現(xiàn)社會(huì)危機(jī)和精神危機(jī),呼吁人性的回歸。
注釋:
①K. Hermann:GeorgHeym. J.B.Metzler,1982,第71頁(yè)。
②③K.Pintus、姜愛(ài)紅譯:《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經(jīng)典詩(shī)集:人類的曙光》,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yè)。
④L·韋勒克、A·沃倫:《文學(xué)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頁(yè)。
⑤汪民安:《身體、空間和后現(xiàn)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頁(yè)。
⑥柏拉圖、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guó)》,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版,第375頁(yè)。
⑦尼采:《權(quán)力意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yè)。
⑧⑨汪民安:《身體、空間和后現(xiàn)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頁(yè),第23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GeorgHeym: Jonathan. In: Martus Verlag: GeorgHeym. Der Dieb [M], München 1995, S. 42-61.
[2]Hermann Korte: GeorgHeym.[M], J.B.Metzler. Stuttgart 1982, S. 71-82.
[3]GeorgHeym: Ausgew?hlteGedichte[M], Reclam. S. 56-60.
[4]汪民安.身體、空間和后現(xiàn)代性[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5]Kurt Pintus.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經(jīng)典詩(shī)集:人類的曙光[M].姜愛(ài)紅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2.
[6]柏拉圖.理想國(guó)[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7]L·韋勒克,A·沃倫.文學(xué)理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8]尼采.權(quán)力意志[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作者簡(jiǎn)介:
楊曉慧,女,漢族,碩士,武漢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言文學(xué)學(xué)院,研究方向:德語(yǔ)語(yǔ)言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