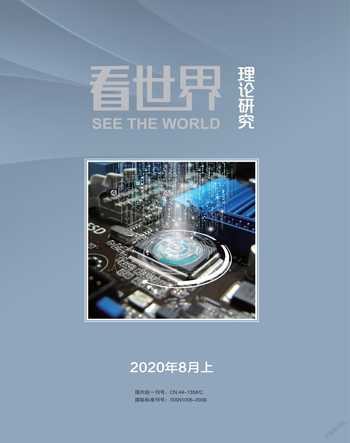從精神分析理論看《沉淪》主人公的病態心理
摘要:本文將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探討《沉淪》主人公的病態心理。小說主人公的種種行為及心理變化,都與他自身的人格結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我”對愛情與性極度渴求,但“超我”這一保守意識又極度否定“本我”的追求,“自我”處于二者不可調和的矛盾中不斷躲避,再加上作為“支那人”的自卑心理,最終只能一步步走向“沉淪”,人格失調讓他再無生的希望,只求祖國富強起來,拯救所有同他一樣飽受折磨的中華兒女。對《沉淪》主人公的精神分析,能夠深刻理解他的這種病態心理,以及其行為的合理性。
關鍵詞:精神分析理論;人格結構;《沉淪》;病態心理
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提出完整的人格結構由三大部分組成,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一個無意識結構,它沒有道德觀念,遵循“快樂原則”。自我是社會的產物,其功能是控制和指導本我與超越。超我是人格在道義方面的表現,它是禁忌、道德、倫理的規范和標準的體現者。《沉淪》小說主人公的這種病態心理及行為,正好和其人格結構相呼應,對其“本我”、“自我”及“超我”進行深入分析,便能理解小說主人公他為何會面臨如此劇烈的心理沖突,乃至于走向自我毀滅。
一、本我:在對愛情與性的極度渴求中一步步沉淪
小說主人公曾接觸了大量的國內文本與西方作品,因此在接觸到西方自由與開放的觀念后,想要融入這種自由、開放的世界。首當其沖的,便是小說主人公身體本能欲望的萌發,這種青春期的性萌動,對“本我”來說,理所應當不應該受到限制,但他卻說“他每天早晨在被窩里犯的罪惡,也一次次的加起來了”,很顯然,把性本能看成“罪惡”是受中國封建禮教的影響,它潛移默化地讓小說主人公龜縮在這種保守文化中,由此產生了“本我”與“超我”的不斷抗爭,但這種抗爭只能加劇“自我”的痛苦與掙扎,卻無法真正束縛“本我”對原始欲望的渴求。
伴隨著性意識覺醒,主人公在異國他鄉也產生了對愛情的渴望,但這種渴望只能成為他內心深處的自我幻想,究其原因,除了封閉保守的自鎖意識之外,還由于作為弱國子民的自卑心理。一開始,路上偶遇“兩個穿紅裙子的女學生”,雖渴望她們的“秋波”,卻只能自嘲“怕羞,沒有那樣的膽量”,甚至開始憤恨自己是支那人。最終,“本我”意識促使他在日記中完全吐露對愛情的病態渴望,“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能安慰我體諒我的‘心’。”在他交游離絕后,外部孤獨壓抑的環境,導致“本我”對愛情越發渴望,甚至產生了一種變態心理,偷窺“伊扶”洗澡,偷聽男女在葦草邊交合,最后進了妓院,“本我”徹底壓倒了“自我”,也越發逃不掉作為支那人的自卑心理,最終在心里怒吼“我再也不愛女人了。”就這樣,“本我”對性和愛情的熱烈渴望,讓“他”在逐步變態的心理中慢慢沉淪,在“超我”的準則面前,只能哀嘆“我所求的愛情,大約是求不到了。”
二、自我:一個孤獨憂郁的性苦悶、性變態青年
《沉淪》全篇是對一個憂郁癥青年的解剖,從這些病癥中,我們能看到“自我”對靈與肉沖突的不斷調和,到最后完全失調的地步。
首先是孤獨與憂郁癥的反復循環。“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他“早熟的性情”,其實就是中國傳統的保守意識,再加上深深烙印在“自我”意識中對中國國際地位低下的自卑,他的“憂郁癥也愈鬧愈甚了”,這種憂郁癥讓他“覺得他的日本同學都似在那里排斥他”,雖然“自我”對現實世界不斷懷疑,但也在不斷地掙扎,看見他們有說有笑,剛開始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去尋訪幾個中國同學,但無一例外,這些調節得不到平衡,反而加劇了他的憂郁與孤獨。
3、除此之外,小說中“自我”的調和更多體現在封建禮教與性和愛情的沖突中。“本我”對性和愛情的渴求作為人之本能,不可能被磨滅,而“超我”這一保守意識又決定了小說主人公對原始欲望的避諱,由此,二者永遠也得不到調和。剛開始,“自我”沒能抑制住手淫,因愛惜身體的原因,“每天總要去吃生雞子和牛乳”,而“超我”則強勢指證這一犯罪證據,讓“自我”產生自責感與羞愧感;接著,由于“超我”對性和愛情的愈加壓抑,“自我”開始走向了由性苦悶轉為性變態的道路,窺浴與窺淫成了“自我”的宣泄方式。
《沉淪》通篇都在寫小說主人公關于“性的要求與靈肉的沖突”,“超我”堅持行為的準則,如果這些準則沒有得到遵守,超我就采以自卑感和犯罪感來懲罰自我。小說中,主人公曾“鎮日鎮夜的蟄居在他那小小的書齋里”,由此可知,他在傳統文化教育中養成了一種保守意識,而這種意識,在他留學日本,接受西學的開放觀念時,完全暴露了出來,成為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也由此產生了人格結構的種種沖突。
其次,小說主人公對作為弱國子民的自卑感以及悲憤感,其實也反映了“他”想要祖國富強起來的強烈愿望。小說開頭,“他”翻譯“The solitary reaper”,“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是唱的前代的衰歌,或者是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看到這首詩歌,小說主人公由此聯想到自己的祖國,悲嘆祖國曾受到的侮辱,雖然是“過去的回思”,但“他”也想借此來“指訴”。除此之外,小說中多次提到“復仇”二字:對“他”的同學,“他”埋怨“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對那兩個女學生,“他”自罵“她們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我總要復她們的仇!”;接著又對侍女和她的兩三個客人復仇,“狗才!俗物!你們都敢來欺侮我么?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你們的仇。”這些看似是偏激話語,但實際上,“他”為何要復仇?又如何復他們的仇?“他”認為自己的一切遭遇都由于他作為弱國子民的身份,如果要復仇,那就只有等中國強大起來了,有了話語權以及平等的地位,才能夠對抗“他”所遭遇的欺侮!因此,“他”的每一次復仇,其實都暗含著“超我”這一愛國意識,以及希望祖國富強的強烈愿望!小說最后,主人公認為他的死是祖國所害,因著封建保守意識對“本我”的壓抑,因著作為支那人的自卑,生活如同死灰,而如果要拯救所有同他一樣飽受折磨的中華兒女。
《沉淪》小說主人公的悲劇,用精神分析理論進行剖析,就是其人格結構的極度失調。全文都在描寫一個病了的抑郁癥青年,且又有非常多的心理描述,通過這些大量的心理描述及其病態行為,我們能夠感知到主人公內心的孤獨、苦悶、抑郁以及自卑。從性壓抑到性變態、人際關系的隔離、作為“支那人”的自卑,這些都是“他”內心的重重巨石,當其人格結構的爭斗達到不可挽留的地步,這些巨石都成為了他走向自我毀滅的導火索。對小說主人公病態心理的解剖,我們深知其“沉淪”結局的不可逆轉性。
參考文獻:
[1]李林臻. 精神分析理論與現代小說之流變[D].天津師范大學,2017.
[2]陳昶.試論《沉淪》中人物形象的精神分析[J].安徽文學(下半月),2008(04):47-48.
[3]邱運華.文學批評方法與案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6.
[4]郁達夫.沉淪.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5]唐君國.從《沉淪》看郁達夫早期創作與弗氏精神分析學的暗合[J].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00(02):63-66+92.
作者簡介:
胡珍平(1997-),女,漢族,四川宜賓,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文藝學。
作者單位:西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