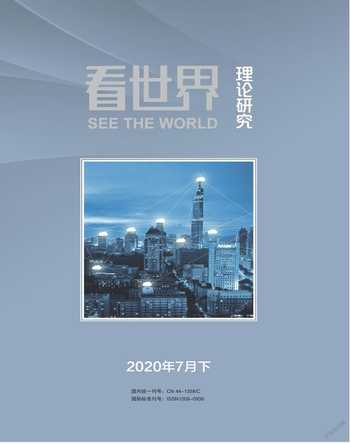《中國詩與中國畫》質(zhì)疑
摘要:錢鐘書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簡單的將中國詩與中國畫對應(yīng),這種界定往往容易使對象模糊而難以界定,應(yīng)該不拘泥于“實”或“虛”之類的單一標準,辯證的看待問題。
關(guān)鍵詞:中國詩;中國畫;南北宗
錢鐘書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提出了這樣的質(zhì)疑:“我們常聽人有聲有勢地說:中國舊詩和中國舊畫有同樣的風格,體現(xiàn)同樣的藝術(shù)境界。那句話究竟是什么意思?這個意思能不能在文藝批評里證實?”在書中錢鐘書對這個質(zhì)疑給予了否定的答案,他認為:“相當于南宗畫風的詩不是詩中高品或正宗,而相當于神韻派詩風的畫卻是畫中高品或正宗。”這其中“南宗畫風的詩”,即是指與南宗畫簡約、含蓄相類似的“神韻”一派風格的詩,以王維為代表,這類詩錢鐘書認為在傳統(tǒng)文藝批評中處于次位,相反與居于次位的北宗畫寫實風格相似的詩卻是詩中高品。至于為什么中國詩與中國畫兩種風格、韻味均相似的藝術(shù),在不同的藝術(shù)領(lǐng)域下,會產(chǎn)生如此迥然不同的社會地位呢?在書中錢鐘書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這樣看來,中國傳統(tǒng)文藝批評對詩和畫有不同的標準:論畫時重視王世貞所謂‘虛’以及相聯(lián)系的風格, 而論詩時卻重視所謂’實’以及相聯(lián)系的風格。”錢鐘書認為這與人們常說的“書畫一律”相違背,舊詩與畫存在著明顯的“不一律”。
錢鐘書提出以上論點后, 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 分別從詩、畫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證。首先對于中國畫錢鐘書仍沿用了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的概念,認同以王維為代表的南宗畫是中國舊畫的主要流派,其所代表的南宗畫的原則是“簡約”,以經(jīng)濟的筆墨獲取豐富的藝術(shù)效果,以減削跡象來增加意境。并且在文中對夏敬觀先生否定“南北宗“的觀點持以太過簡單化,而不值得一提。倒是啟功先生,從根本上否定南北宗,但主要是出于對董其昌人品的懷疑與憎惡,啟功認為“南北宗”是董其昌偽造出來的,是一種非科學的說法,其目的是為了給自己正名,動機是自私的。關(guān)于南北宗論的說法時至今日仍是眾說紛紜,大家都各持一言,難下定論。筆者認為陳傳席在《中國畫之韻》中講到:“中國畫理論,北宋至明皆無甚大發(fā)明。明末董其昌研究畫史,發(fā)現(xiàn)了中國畫有兩種指導(dǎo)思想和藝術(shù)風格,于是倡“南北宗論”,道出了宮廷和士夫之間兩種不同的審美情趣。可惜很多人不能明白董其昌的深意,以自己的分宗法猜想董其昌的分宗法,或云董其昌為了標榜門戶,抬高吳派,其實董不滿于吳派。或云此論從師承關(guān)系分,從水墨、青綠分以及按國家籍貫、身份分,皆漏洞百出。董分南北宗自有他自己的道理,南北宗論以尚韻為主旨(董論書法亦尚韻),并不在水墨、青綠、寫意、工筆之分,”這句話很好的解釋了大家對“南北宗”的紛說之因。無論董其昌人品如何低下都不能否認他在藝術(shù)上的貢獻,在上海博物館舉行的為期三天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shù)國際研討會”,策展人凌利中認為此次研究可將其列為中國畫史的一門“董學”,可見董其昌在中國畫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和研究價值所在。
夏敬觀和啟功對“南北宗”簡單地否定是將有作無,錢鐘書先生在承認傳統(tǒng)山水畫的“南北宗”后,卻將其套用在詩的分類上,把詩也強作分派,屬于以無作有。他將詩分為與南宗畫風格相似的南詩即“神韻詩”以及和北宗畫風格相似北宗詩即“寫實詩”,此種宗派分類太過籠統(tǒng)與寬泛,往往容易使對象模糊而難以界定。其實無論杜甫、李白或者白居易等詩人的風格都不能輕描淡寫地歸為寫實或神韻,每個人的風格隨著時局與個人境遇的不同而一直在轉(zhuǎn)變與融合。中國詩常常給人韻外之致、味外之味的綿綿不盡的藝術(shù)享受,有限中包孕無限,瞬間里涵蓋永恒。正如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所說:“中國人不是象浮士德‘追求’著‘無限’,乃是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鳥中發(fā)現(xiàn)了無限,所以他的度是悠然意遠而又怡然自足的。”“中國人于有限中見到無限,又于無限中回歸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復(fù)的。”正是這樣詩歌有這樣獨特的美學格調(diào),才能被譽為一個民族文化的結(jié)晶和最高體現(xiàn),被譽為文學之祖,藝術(shù)之根。
錢鐘書由“中唐以后,眾望所歸的最大詩人一直是杜甫”,推斷出中國傳統(tǒng)文藝批評的論詩 標準,是“重視所謂`實’以及相聯(lián)系的風格”,這其中他自定義了一個隱含的前提: 眾人推崇杜詩都遵守一種標準,即重視所謂 “實”以及相聯(lián)系的風格。然而事實上,歷代文藝批評家推崇杜詩的標準復(fù)雜多樣,在審美價值取向上彼此都存在著差異,有的觀點甚至相互排斥對立。錢鐘書依據(jù)杜甫“詩圣”的地位將杜甫納入“北宗”寫實派,而忽視了他神韻且抒情的部分。在杜甫的《月夜憶舍弟》中,開篇“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雖是描寫的邊塞地區(qū)人煙稀,孤雁鳴的蕭瑟之景。而后一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露水從今夜就開始慢慢變白,月亮還是家鄉(xiāng)的最亮。運用了倒裝的句法,將想表達的“今夜露白”和“故鄉(xiāng)月明”的詞序稍作調(diào)整,寥寥數(shù)字,凄楚悲傷。尤其是“月是故鄉(xiāng)明”一句,真實的抒發(fā)出了異鄉(xiāng)游子對家鄉(xiāng)解不開的濃濃思念之情。雖字字寫實,但情意綿綿。在家喻戶曉的《絕句》中,“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短短20字就把春天的自然美景囊括在內(nèi)。在春風和煦,芳草絨絨,鮮花灼灼的景象下,感受到作者心底生出的歡脫喜悅之情難以掩飾,如此虛境,豈不抒情?錢鐘書將杜甫歸納在北宗“寫實派”里,這與儒家登上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寶座后,人們在潛意識里認為中國以詩歌為代表的古典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也因是與儒家相符合的,應(yīng)偏向于政治與倫理的實用型模板,杜甫的崇高地位與此思想觀念不無關(guān)系。但錢鐘書忽略了杜詩雖以時事入詩卻也含有淚水和深情,杜詩的感情是深沉闊大的,在深處蘊涵著一種厚積的感情力量。所以,錢鐘書將中國畫的“南北宗”論定義在浩瀚的詩詞上,將北宗“寫實派”定義在杜甫上還是略顯牽強。
同樣被納入北宗“寫實派”的詩仙李白更是一位將情感揉進肺腑的詩人,他的詩有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美譽。從一句人盡皆知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說起,在月白霜清的夜晚,當銀輝灑向床前,李白一下子慌了神,恍惚間覺得那皎潔的月光好似皚皚的濃霜鋪地。這錯覺是李白夜不能寐的寫照,分外明亮的月光,觸動了詩人思緒,使詩人產(chǎn)生遐想,他不禁低下頭來想到了故鄉(xiāng)的山水,故鄉(xiāng)的親人。如此平淡又細膩的詩句,激起讀者內(nèi)心的微微波瀾,簡單的三言兩語卻道盡了一切意境,此等抒情豈該被列入寫實中去。在《秋風詞》中:“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fù)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長相思兮長相憶,短相思兮無窮極。早知如此絆人心,何如當初莫相識。”李白灑脫浪漫的外表下竟也藏著一顆如此柔情蜜意的內(nèi)心,能將對心上人的思念如此細膩綿柔的融進詩中,充分體現(xiàn)了言有盡而意無窮,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將此情種納入寫實實屬不該。
再說王維, 在錢鐘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中,他與杜甫的風格是對立的。王維信佛, 以至于詩、畫都受其影響。錢鐘書說: “在他身上, 禪、詩、畫三者可以算是一脈相貫。”王維的詩、畫可以相提并論, 因為二者的本質(zhì)特征都富有“神韻”。錢鐘書同樣對王維的“神韻” 推崇備至, 雖然在此文中他把“神韻”與“寫實”對立了起來, 但在《談藝錄》中論述神韻的問題,說:““故無神韻,非好詩;而只講有神韻,恐并不能成詩”,“有于高古渾樸見神韻者,有于風致見神韻者,有在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虛處見神韻者,神韻實無不該之所”,可見錢鐘書認為二者的關(guān)系往往是融合的, “寫實”也并不排斥“神韻”。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錢鐘書取“神韻”的狹義,而在其它地方取“神韻”的廣義, 這就是他自身的一個矛盾性。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姜玉琴在《唯美的藝術(shù):中國古典詩歌的審美主流》中甚至認為“在中國詩歌的最鼎盛時期,古典詩歌的正宗代表恰是以王維為代表的神韻一派。比較之下,以杜甫、白居易等為代表的‘寫實’派詩風,倒有旁門左道之嫌”。筆者認為中國舊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絕對地位, 一部中國詩史堪稱一部中國文學史, 而中國舊詩又體系龐大、風格多樣,因而很難嚴格的劃定神韻與寫實的風格,更何談用這兩種風格來界定中國詩中正宗、正統(tǒng)的地位。神韻和寫實本就是兩個共生體,不能用中國畫的南北宗來偷換概念。王維早年也像中國傳統(tǒng)的文人士大夫一樣,有一顆積極入世,渴望建功立業(yè)的心,卻因為寫歌的時候,一句 “憐人舞獅子” 而被罷黜,分配邊疆。現(xiàn)實的壓迫導(dǎo)致他看淡名利,甘愿歸隱罷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開篇便寫道:“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詞之美,美在其境界。王國維將“境界”標榜為詞論的審美核心,評詞標準。如果按照錢鐘書對中國詩南北宗的劃分,王國維應(yīng)力推神韻詩為詩中高品。王國維在第二篇中寫道:“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必鄰于理想故也”。王國維的“造境”指虛構(gòu)之境,是錢鐘書所認為的南宗詩所具有的創(chuàng)作特征。“寫境”指描寫現(xiàn)實之境,是錢鐘書所認為的北宗詩所具有的創(chuàng)作特征。這是理想與寫實兩派的區(qū)別所在。但是王國維認為兩者實際上很難區(qū)分的,任何“境界”都要既反映客觀現(xiàn)實,又要表現(xiàn)主觀情感,只是側(cè)重點有所不同,因而才有了“造境“與“寫境”的區(qū)別。大詩人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境界必然合乎自然,所描寫出來的境界,也必然是內(nèi)心真實情感,亦難以區(qū)分是“造境”還是“寫境”。
無論是對中國詩還是李白杜甫王維等人的評價都因考慮多重影響因素,而不是拘泥于“實”或“虛”之類的單一標準從而使得問題變得簡單化和片面化,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我們應(yīng)該辯證地看待錢鐘書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所表達的觀點,如他所說的作“鞭辟入里的解釋,而不是舉行授予空洞頭銜的儀式”。
作者簡介:
任婕(1995.12—),女,漢族,籍貫:山西太原人,南京藝術(shù)學院美術(shù)學院,18級在讀研究生,碩士學位,專業(yè):美術(shù)學,研究方向:中國美術(sh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