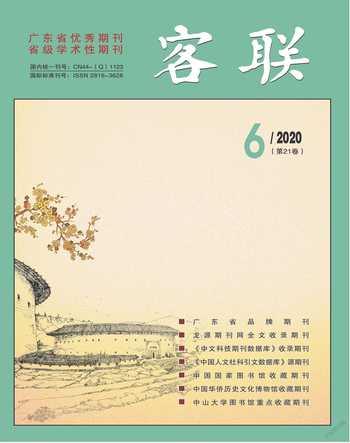法律、法治與人權
聞匯
【摘 要】法律是理性人命令或體現,法律的統治理性的統治。中國的法治推進有其獨特性,法治進程雖然無法同經濟改革進程相提并論,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國的法治正在逐漸建立,法治進程正在穩步推進。
【關鍵詞】法律;法治;人權
“人們必須制定法律并且要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就像是最野蠻的獸類一樣(Mankind must have laws,and conform to them,or their life would be as bad as that of the most savage beast)。”在柏拉圖眼里,人類的本性永遠都是傾向于貪婪、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沒有任何理性,他們的行為使整個國家都充滿了罪惡。擺脫這種令人絕望的處境,有人治和法治兩種辦法。柏拉圖把法律比喻成金色的繩子,認為它是最好的,文雅而不粗暴,可以幫人們區分善惡。他說,我們只能選擇法治(法律和秩序)。法律是理性人命令或體現,法律的統治就是上帝和理性的統治,“服從法律,這也是服從諸神”。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如今已深深根植于當代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之中,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就呼吁“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抗爭,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中國自1996年以來,法治流行起來,2004年寫入憲法修正案。2014年10月20日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中國的法治進程雖然無法同經濟改革進程相提并論,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國的法治正在逐漸建立,法治進程正在穩步推進。
當代對于法治最為精辟的論述當屬羅爾斯。他將法治定義為“一致的、公允的,以及在此意義上公平的”依照“公開規則”進行的治理。他的法治觀念主要包括如下內容:
1、遵守可能性之要求。法律制度應當遵守“應當意味著可能”之戒律。包括:法律規則所要求或禁止的行動,必須是人類可以理性期待的;制定和頒布法律的人應當以誠信的態度行事;法律制度應認可無法履行的抗辯。
2、一致性之要求。法律制度應當遵守“相同案件相同對待”之戒律。包括:法官應當相關法律規則及原則來論證區別對待的合理性;在解釋所有法律規則時必須符合法律前后一致性的要求。
3、公開性之要求。法律制度應當遵守“法律應公開”之戒律。包括:法律應當廣為人知且明示頒布;法律的意義應當予以清晰的界定。
4、一般性之要求。制定法和其他法律規則在上應當具有一般性,不得針對特定的個人。
5、正當程序之要求。法律制度應當為案件的裁決過程提供公平且有序的程序。包括:法律制度應當規定有序并公開的審判和聽審程序;法律制度應當包含足以保障理性詢問程序的證據規則;法律制度應當提供合理設計的程序以查明事實;法官應當獨立且公允,且不得審判自己的案件。
二、法治與人權保障
人權與法律具有不可分享的密切關系,在法的價值體系中,人權居于最高層次,是法的核心價值。人權的法律化是現代法治社會形成的根本標準。
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是當代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和發展要求。中國立足國情,順應時代趨勢,提出要在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時,加強政治文明建設,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治國,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59年“關于法治問題的《德里宣言》”指出:立法機關的職能不僅要創造各種條件以尊重和維護個人尊嚴,而且要盡力通過立法來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法治原則不僅要防范行政權力的濫用,而且要求有一個有效政府來維持法律秩序,保障人們擁有充分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的條件,保護個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法治要求正當的刑事程序,保證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等等。
法律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一種規范性社會調整,法律被制定出來,有法可依,才能使人們的行為確立標準和范圍。但是,有法不依,同沒有法律的結果是一樣的,必然會引起社會秩序的失控和混亂,生活于其中的人毫無安全和幸福可言。法對社會生活和影響是全方位的,法具有社會作用、規范作用和思想影響作用。
法治可以保證可預見性和穩定性,在法治受到尊重的情況下,公民和企業可以根據法律為他們的行為做出預告的籌劃。法治是人民對抗暴政、騷亂和不正義的堡壘。法治缺失后噩夢必須接踵而至。
三、法律與法治
“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也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We have distinguish two senses of the rule of law-one which means obedience to such laws as have been enacted,and another which means that the laws obeyed have also well enacted)。”
亞里士多德指出,服從良法包括兩種情況,其一是樂于服從最好而又最可能制定出來的法律;其二是寧愿服從絕對良好的法律。絕對良好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因為法律不可能完全覆蓋生活的全部,社會情勢的變更很多時候也絕非法律所能預測。因此,只能服從最好而又最可能被制定出來的法律。
“法律不應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對立的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To live by the rule of constitution ought not to be regarded as slavery ,but rather as salvation)。”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離開城邦,非神即獸”,全體公民都應遵守城邦所制定的生活準則,應該讓每個人的行為都有所約束。
站在兩千多年之后的時間節點上,我們依然確信:法律和自由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之間有內在的邏輯聯系。法律是維護自由的秩序和規則,公民在守法的狀態下不受他人干涉,享有想其所想、說其所愿說、去其所愿去的自由;自由則法律制約下的自由,享有個人自由和權利時,必須考慮是否危及他人的利益以及作為集體代表的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自由從來都不是絕對的,絕對的自由就是不自由。
“如果一個國家,刑罰并不能使人產生羞恥之心的話,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結果,暴政對惡棍與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罰(If there are countries in which shame is not an effect of punishment,it is a result of tyranny,which has inflicted the same penalties on scoundrels as on good people)。”
孟德斯鳩認為,公民的精神受到刑罰的影響,在刑罰從輕的國家和在刑罰從重的國家是一樣的。因為人們對嚴刑峻法在思想上習慣之后,正如對寬法輕刑習慣了一樣。他舉例說,為了消除攔路搶劫這種禍害,有的國家(法國)發明了車輪軋殺刑。這個刑罰特別恐怖,使搶劫暫時停止,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在大路上攔路搶劫又和從前一樣了。孟德斯鳩認為,治理人類不能用極端的方法,對于刑罰的手段應謹慎使用,他說“法律不是一種純粹的‘權力作用’;在性質上無關緊要的東西就不屬于法律的范圍,”“一切不是由于必要而施用的刑罰都是暴虐的。”自然既然給了人類羞恥之心,那么應該把不名譽作為刑罰最重的部分。他認為,如果刑罰不能產生羞恥之心,只是單純靠恐嚇使人們因懼怕發明而守法的話,這主要是因為政法的暴戾,對輕微的過錯也使用了相當殘酷的刑罰。他主張,立法者在糾正弊端的時候,不能眼睛只盯著這個目標,而對于所采取措施可能造成的其他弊害視而不見。法律過于嚴酷,將全阻礙法律的實施。
“人們必須制定法律并且要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就像是最野蠻的獸類一樣。”重溫柏拉圖的經典法律格言,我們發現,制定法律并且遵守法律(有法可依并且有法必依),對于人類社會來說,是幸福和秩序的基礎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