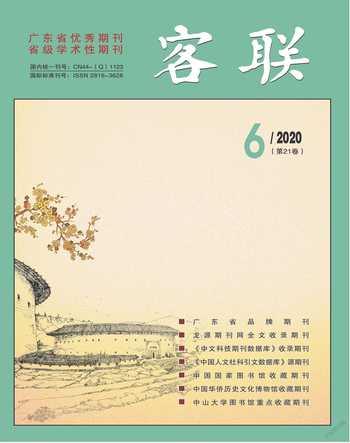多元河西文化下的反思與尋根
朱珂瑤 汪迎瑩
【摘 要】河西走廊這片奇幻而又獨特的土地上涌現出大批本土作家,他們深受河西文化的浸染,在創作中書寫本土特色,挖掘河西文學的獨特魅力,運用他們作品中的獨特意象傳遞情感,同時賦予這片土地新的色彩。本文擬通過分析河西地區的作品概貌,本土作家創作,及作家創作與本土文化資源相互作用,來探尋在多元河西文化背景下,河西當代作家的創作與本土文化資源的關系。
【關鍵詞】河西地區;本土文化資源;當代作家;作品創作
一、大漠中的悲歌與反思
河西地區地處甘肅省西北部,河西走廊狹長分布,降水稀少,氣候干旱。河西境內中部及西部分別分布著騰格里沙漠及塔克拉瑪干沙漠,河西本土作家生于斯長于斯,大漠的廣袤、戈壁的雄奇早已深深印刻在他們的腦海中,成為作家創作中不可或缺的素材。河西本土作家在創作中多描寫廣袤雄奇的大漠戈壁景觀,視野開闊,蕩氣回腸。與大漠人民的性格樸實真誠一般,作者創作的風格以現實主義為基調,兼有對奇異神秘事物的浪漫主義的詩意描繪。然而廣袤的大漠中,干旱的氣候與無情的風沙使得這里生存環境極其惡劣,在這樣的環境下,人與自然矛盾尖銳,百姓生活艱難,大漠中農民生存現狀不容樂觀。因此本土作家在書寫大漠景觀之下更多表露出的是對人與自然以及在大漠中農民生存現狀的反思。
雪漠和唐達天便是書寫大漠并進行反思的代表作家。雪漠花費了12年的時間,嘔心瀝血創作了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白虎關》以及《獵原》[1]。他自是河西大漠中的一份子,對于這片土地有著非同尋常的情感。在作品中,雪漠以一種鄉土情懷來體察、書寫生活在西部大漠中生活的農民,無不為他們感嘆與唏噓。其大漠三部曲以涼州農村為歷史大背景,描寫了以老順家為代表的幾家農村人民在大漠里馴鷹、獵兔、捉狐、勞作、偷情、繳糧等日常發生的各種糾葛和事件展開的故事,反映出西北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劣,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下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共處不可調和的矛盾。唐達天的《沙塵暴》[2]講述的是發生在西北甘肅涼州市鎮番縣一個名叫紅沙窩村子的故事。由于地處西北,植被稀少,每年春天沙塵飛揚,暴風四起,且常年干旱少雨。在村支書老奎的帶領下,紅沙窩村的鄉親們開始打地井、栽樹苗、保衛莊稼地。作者唐達天以蒼茫詭奇的獨特西北沙漠氣象為背景,在歷史的進程中人們打破自然平衡受到懲罰,醒悟后懺悔補過,重獲新生,描繪出當地百姓波瀾壯闊的生活畫面,展現出風情濃郁的地域特色。
荒漠戈壁的貧瘠,物質生活的貧困,作者筆尖觸及此處進行描寫剖析,究其深層,是對農民精神匱乏、思想保守落后的反思與書寫。《大漠祭》真實地記錄了一個時代的百姓是如何生存的。婚嫁喪事、傳宗接代、生老病死,當地人恪守著這片黃土地麻木而艱苦的生存下去。由于封建迷信,蘭蘭的男人一定要生兒子,認為女兒是白狐貍精而將其領進沙漠活活凍死,因為愚昧無知,當地人身體不適首先想到的是求神拜佛而不是尋醫問藥。在書寫中作者的情感是深沉的,傳統習俗與人性弱點的袒露,生命力量與客觀世界的激蕩,城市文化對河西農村傳統的沖擊,傳統道德在新時代中的沖突,這些問題在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情感真摯而沉重,引發人們深思。
二、草原上的行吟與尋根
提到河西,首先映入讀者腦海的必定是漫天的黃沙、荒蕪的土地。但溯其根源,早期匈奴、羌、月氏等民族生長并扎根于河西走廊,他們馳騁駿馬,創造了燦爛的游牧文化。然而隨著環境的惡化、戰亂的頻繁,游牧文化逐漸削弱,發展至今,走廊中部的沖積平原上分布著無數大小不一的綠洲草原,游牧文化沿著祁連山麓呈線性散播。草原情愫深埋于河西人胸中,是河西人民無法割舍的情懷,回響在一些作家的文學創作中。
王新軍在《大草灘》[3]中告別現代社會急功近利的意識形態,用其生機盎然的寫作把我們的視域引向廣闊開放的大草灘,成群的牛羊,浮動的白云,這一切都令讀者思緒放飛。王新軍以純粹的方式審視西部獨特的生存環境,筆調清新,為世人展現位于河西走廊獨特的草原風貌。由于他常年扎根在西部大地上,家鄉的呼吸狀貌都浸潤著他,正是有著細心的觀察和感受,他不僅僅是描繪西部的自然環境,更是以批判與沉思的態度,審視著家鄉延續多年的存在。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環境的退化,人心的嬗變,這一切都過于紛擾,詩意的生活已成為現代人地奢望,王新軍對大草灘的描寫是一個回溯、尋根的過程,他在尋找逝去的田園牧歌,尋找心靈棲息的家園。多年生活在牧區的裕固族作家鐵穆爾以其獨特的創作視角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散文作品。他的創作是在恢復關于草原的記憶。裕固族文化與游牧文化緊密相連,一個民族特定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習俗會融入這個族群每個人的心中,成為一個民族抹不去的歷史記憶,它流淌在血液里,日夜呼吸浸潤。毋庸置疑,當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交流碰撞時,會擦出別樣的火花,鐵穆爾作品的美學價值就體現在本民族情節與漢族文化交流融匯而形成的獨特之處。在散文集《北方女王》[4]中,他多以祁連山腹地的肅南草原為創作背景,描寫牧區人民的生活狀貌。《北方女王》是一首堯熬爾的古謠的名稱,鐵穆爾以其作為自己散文集的書名,體現出他對其家園之根的追尋,隱藏著族人的靈魂。牧人善良純樸,情感純粹,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然而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人們卻對大自然開始無節制的索取,于是沉淀于其靈魂深處最本質的情感井涌而出,他用筆記錄下這種原于內心深處的追尋和思考。
永昌籍作家張弛在作品中多描繪草原上雄姿英發的駿馬。馳騁的駿馬斗志昂揚,充滿戰斗力,善戰、英勇亦是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對于草原,他們有著濃的化不開的情結,但也正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里,河西走廊上的先民與寒冷、饑餓頑強斗爭,生生不息。因此,在張弛的諸多作品,如《汗血馬》、《駑馬》[5]中,作者描寫了大量神勇堅忍的馬,臧甲山不斷追尋的天馬,彪壯雄健的黃騸馬已不僅僅是驍勇馳騁的駿馬,更是不屈不撓、有著崇高精神境界的活生生的人。馬兒在荒原上追逐廝殺,牧馬人作者借馬這一意象來塑造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表達對先民的崇敬。
三、多元文化的碰撞與交流
從地域上看,河西走廊處于一個獨特的地理位置。其地形環境復雜,境內有綿延起伏的山脈,積雪終年不化的祁連山雪峰,有雄奇廣袤的戈壁荒漠,一望無垠的遼闊草原,有蜿蜒九曲的黃河,有舉世聞名的敦煌石窟。南北過渡內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有著游牧草原文化的熱情奔放,西銜塔克拉瑪干沙漠和騰格里沙漠,有著大漠戈壁的粗獷豪邁,東部位于黃土高原之上,有著黃土地農耕文化的質樸細膩。在這樣一個貫穿南北,銜接東西的要塞,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此碰撞,儒釋道精神和外傳宗教文化于此交流,秦文化與大地灣文化在河西發展。河西走廊匯聚并兼容著如此多元的文化,賦予此地更加神秘復雜的色彩,體現在不同作家的創作中,閃現著別致而又獨特的火花。這豐富多樣且獨具特色的地域環境影響著本土作家的創作。
河西地區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這里繁衍生息著回、族、蒙、裕固、東鄉等多個民族,涌現出大批優秀的多民族作家,他們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回望自己的民族,書寫民族信仰,保存民族記憶,傳遞并呼喚民族精神。河西走廊詩人群體中一批優秀的民族詩人為河西地區詩歌的創作注入了鮮活的血液,如裕固族的賀中、妥清德、賀繼新,藏族的仁謙才華、旺秀才丹,才旺瑙乳等,他們以獨特的視角和審美展現了河西地區少數民族風情和民族文化特征。裕固族詩人妥清德筆下美麗安謐的草原是世人心中一塵不染的故土,詩人常在詩歌中以寫實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幅生動的景象,緬懷裕固傳統。《大風吹著故鄉》、《裕固民族:藍天上白云》等作品中風吹草原、牛羊漫步的畫面都凝聚著詩人心中對故鄉深深的愛。印度佛教沿著河西走廊東傳,佛教文化在河西地區傳播較廣,底蘊深厚,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便是位于河西走廊一顆璀璨的明珠。在天祝藏族自治縣的藏族詩人才旺瑙乳的詩歌中,有著大量具有藏族特色的意象,雪山、朝圣者、蓮花寶座、佛祖等意象在他的詩歌中隨處可見,民族色彩濃郁。《七朵蓮花盛開》中透露出詩人對于人生無常、一切皆空的感悟,“從蓮花到根,一顆露珠滾過了天空,那碧波蕩漾中盛開的:無生與無痕”具有濃郁的佛教色彩。
從時間上看,歷史的洪流滾滾向前,在此匯集。河西作家回眸歷史,以古觀今;或寄托遙思,沉淀深厚的歷史變遷感,或凸顯理性訴求,展現豐厚的歷史文化。在古馬詩集《西風古馬》中,常有“匈奴”、“單于”、“西夏”、“西涼”[6]等語匯映入讀者眼簾,在西域民族的懷古語境中回望那段戰場風云,感懷歷史。賀曉鐘、賀文龍父子創作的《敦煌頌》,以清代末年敦煌歷史為背景,以敦煌本地的真實社會歷史事件為依托,并采用口傳演繹的生動方式,敘事鋪陳相結合,既客觀地敘述歷史事件,又運用多種寫作技巧渲染氛圍,生動地再現敦煌那個特定年代的情形,歷史的滄桑與現代的反思相互碰撞交織,作者一步步為我們揭開歷史神秘而厚重的面紗。
四、結語
“齊魯的悲愴,秦晉的悲涼,東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異,楚地的絢麗,吳越的逍遙,巴蜀的靈氣。”[7]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作家深受河西土壤的浸潤與培育,將自己創作深深植根于河西這片土地,作品中所反映的內容多是與作家接觸最深最久的地域文化相關。河西地區本土文化資源不僅為作家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原型和素材,而且影響了作家具體創作的寫作風格、思想文化特征、審美精神和語言形式。可以說,沒有獨特的河西文化就沒有河西作家這些優秀的作品創作,無論是民族的、宗教的,還是地域的、自然的特征方面都對作家的創作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尤其在作品中這些文化得到了印證與說明,是不同于西北地域的文化所不能比擬的。
于此同時,作家創作對本土資源文化的補充也是不容忽視的。河西作為古代絲綢之路必經之地,所接受的文化多元融合,零散復雜,更有許多不為大家所知的邊緣文化,發掘了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賢孝這種涼州小調似乎并不為眾所熟知,《大漠祭》、《瑩兒的輪回》等作品中對此進行了一定的描寫,這種粗筆勾勒為我們展示了自由平直曲調敘述“國書”、“家書”的民間口頭藝術,讓我們了解到這種西北小調的獨特魅力和文化價值。而作家的創作不僅是對文化的反映,有時候更多的是一種文化的放大與傳播,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地域特色,讓不同地域的讀者能夠了解河西,了解西北,同時將獨特的西北文化傳播到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國,這既是對當地文化的弘揚,同時也豐富了多元融合的中華文化寶庫。這種文化的敘述和挖掘,整理和傳承,唯河西作家不可為,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先天條件,為本土文化資源的保存和傳承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作家創作與本土文化資源二者的關系相輔相成,共生共榮。作家一方面從本土文化中汲取養分進行創作,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整理和豐富了本土文化資源,他們本身便作為一種寶貴的“本土文化”而存在著,為這片土地添磚加瓦,滋養萬物。二者相互依賴,相輔相成,也只有兩者和諧共生,才能更全面的挖掘探討本土資源,使本土資源煥發新的色澤,使得創作與資源達到最佳水平,繁榮發展。
【參考文獻】
[1]雪漠.大漠三部曲[M].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2]唐達天.沙塵暴[M].現代出版社,2010.
[3]王新軍.大草灘——王新軍短篇小說選[M].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4]鐵穆爾.北方女王[M].甘肅文化出版社,2008.
[5]張弛.張弛西部小說選[M].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
[6]古馬.西風古馬[M].敦煌文藝出版社,2003.
[7]樊星.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