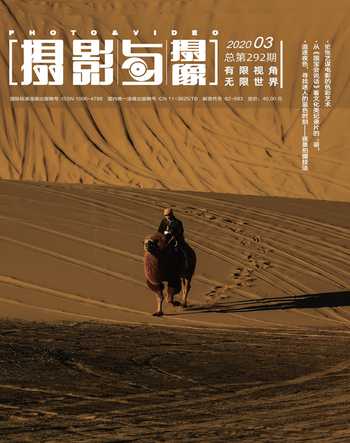攝影書《3DPRK》評析
黎家銘



摘 要:本文以攝影書作品《3DPRK》為對象,從攝影書的形態、觀者的感受、作者的拍攝過程以及拍攝對象進行分析。全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第一部分著重討論立體觀片器的意義和使用感受;第二部分從該攝影書作者的拍攝過程入手,分析被拍攝對象是如何成為立體影像雕塑的;第三部分討論了風景在作品中稀缺的可能原因;第四部分主要從作者過往作品中尋找線索;結語部分進行延伸性的思考。
關鍵詞:攝影書;立體攝影;立體觀片器
中圖分類號:J404 文獻標識碼:A
1 雙目對焦的體驗
《3DPRK》是斯洛文尼亞攝影師馬蒂阿士·坦契奇(Matjaz Tancic,1982出生,下稱馬蒂阿士)的攝影書作品(見圖1),這部攝影書源于朝鮮的官方邀請,經由駐北京的朝鮮高麗藝術工作室Koryo Stuido與馬蒂阿士合作完成,由國內重要攝影獨立出版社出版。馬蒂阿士與一名制作人,在兩名朝鮮向導和朝鮮司機的帶領下,被允許使用3D立體攝影技術對朝鮮人進行拍攝。拍攝計劃于2015年開始,在2018年的“漢朝會晤”前夕依然在進行。《3DPRK》已經出版兩次,攝影書的購買者驚異于這位攝影師可以在朝鮮獲得如此清晰并生動的影像,從3D立體觀片器投射出來的立體影像受到了觀看者極大的歡迎。第一版《3DPRK》攝影書共1000本,在六個月內被搶購一空,在英美攝影書店的熱銷排行榜名列前茅,入選了Lensculture(國際性的攝影組織)2016年度最佳攝影書。
這部攝影書更像是一盒立體觀景卡片套裝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籍,但它在附贈的說明書中保留了翻動書頁的傳統功能。在閱讀和觀看之前,觀者需要把卡片插進一個黃色的立體觀景器,才能把卡片上兩邊略帶差異的照片組合成一幅帶有立體縱深的照片,這個觀景器容易讓人聯想到千禧年時流行于中小學科學課上的立體觀景器(它們自帶的立體照片里通常都是全國各地的景點,幾乎沒有人物出現在照片里),事實上它們也并沒有什么不同,脆弱的折疊結構被沿用至今,看似符合人體工學的鼻梁凹陷處只能起到指示觀看方向的作用。立體觀景器標志性的黃色塑料外殼也沒有改變,2000年前后任天堂的FC主機流入中國后,大量的游戲卡帶被仿制并套上黃色塑料外殼出售,使用黃色塑料的原因是因為黃色能避免廉價塑料老化發黃。某種程度上,黃色塑料外殼已經成為那個時代令青少年歡愉的符號,二十多年過去后,購買《3DPRK》的人極有可能對黃色塑料擁有的美好記憶。
低廉的造價所帶來的是并不完美的光學設計,兩片用于欺騙視覺系統的樹脂鏡片并沒有完美地實現它們的功能,鏡片焦距與觀者眼睛的距離不匹配造成了每次換卡后都需要重新適應才能使立體影像被正常接收。這個過程與正常視力的人戴上近視眼鏡相似,它讓觀者清晰地感覺到晶狀體凸度增加。隨著視覺系統的調整,這個不怎么完美的虛假幻象開始生效,最終完成了一次極具儀式感的視覺上的轉換。與19世紀所流行的立體觀片器不同,雖然二者原理上一致,但顯然19世紀的觀片器被設計得更加精致[1],除了方便調整距離的手柄、合理的遮光罩、仔細研磨生產的非球面光學鏡片外,在立體照片的尺寸大小上同樣體現著過去人們對立體影像的精確呈現的關注。《3DPRK》沒有偏執于“精確性”的討論,而是選擇了更具有懷舊意味的簡單工具來實現立體效果,這種懷舊把觀者帶到了一個因為物資緊缺而粗制濫造的時代,在觀看者失焦并被黃色塑料外殼反光占據視線的同時,狡猾地將隱喻放置眼前并加強印象,直到雙眼對焦完成,大腦接收到符號進而釋放的多巴胺才剛剛到達細胞受體,一場時空被轉換的狂歡即將開始。
2 無法回視的被觀看者本身
在朝鮮進行立體影像的拍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數碼影像技術的發展讓拍攝一件立體影像作品變得十分簡單,但依然需要至少幾分鐘的時間架設相機和調整相機來對準拍攝對象,《3DPRK》里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經過精心排布的(見圖1)。這種設定好姿勢和場景并花費時間的拍攝,有趣地與過去快速感光材料還沒被發明的時代的攝影發生關系——雖然被攝對象不需要被固定在支架上動彈不得,但很顯然這種拍攝過程是攝影師和被攝對象的相互妥協,被攝對象自覺地維持著表情與姿勢,而攝影師則需要盡快完成這一切,試圖在拍攝對象失去耐心之前捕獲令雙方滿意的影像。在朝鮮,妥協的雙方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轉變,由司機規劃路徑,兩位官方向導則選定拍攝的背景和對象,攝影師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將鏡頭慢慢挪向他感興趣的地方,陪同翻譯(一位在當地工作的外籍教師)需要與當地人進行交流,以打破他們對西方面孔的隔閡,拍攝對象則在眾人的圍觀中努力展示大方得體的一面。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論來看,這種拍攝過程毫無疑問地可以被視為客體化的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架設立體攝影設備之前,另外一個“他者化”的過程已經完成。如果說厄里(John Urry)[2]的著作“觀光者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2002)”區分了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界限,那在馬蒂阿士將朝鮮的景象固化之前,一定還存在一個“批準”成為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步驟。這種“批準”顯然是為了避免超越界限的發生而設立的。一方面,標準的制定者們選取合適傳播的景象并進行裁切,另一方面,馬蒂阿士與制作者們又對其進行編碼并立體化,最后成功地制造出一尊尊影像雕塑——處于現場的人。
盡管馬蒂阿士一再強調他在尋找“真實的人”,并希望通過3D技術呈現出他們“真實”的狀態。但作為被攝對象,這些散布在朝鮮各個角落的人們顯然還需要時間來適應面前架起的攝影機和外國人的面孔,即使馬蒂阿士為了讓自己顯得更平易近人而穿上了一件胸前印有中國字樣的運動服。張開的閃光燈反光傘體型龐大,其留下的印象不是幾句輕松的交談就可以消解的。在計劃進行的后期,馬蒂阿士放棄了專業的3D攝影設備,只憑后期處理來模擬兩眼的視差,盡量在獲得可接受的立體影像的同時減少被攝者的壓力。我們能看到照片里的人都細心整理了服裝,以保證自己的形象符合宣傳所需要的氣質。馬蒂阿士曾希望拍攝一位務農者脫去工作制服的照片,而被向導以這位務農者會因此覺得羞愧為由而拒絕,可見即使是介入到“私人空間”或者是通過偶發性地邀請進行拍攝,馬蒂阿士所追求的“真實性”都會受到影響。馬蒂阿士精心挑選拍攝對象與地點,在照片中加入帶有縱深信息的維度以引起興趣,但人文關懷依然難以送達,甚至有被冠以殖民主義者名號的風險。在這里面,最真實的反而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緊張角力關系,但到了最后,這種隱含的力量卻被廉價的樹脂鏡片釋放掉了,被攝者們在小卡片上留存的凝視的目光雖然是精準對焦的目標區域,觀者們卻沉溺于移動眼球來感受虛擬的深淺關系(見圖2)。
被凝視客體的無法回視的狀態是引發窺探快感的一部分[3],而立體觀片器本身亦不是為了“回視”而設計的,相反立體鏡造就的立體虛擬空間會帶來更多的窺探快感。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就習慣使用立體鏡進行娛樂,直到目前為止立體技術的主要功能也依然沒有改變,VR和AR(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正在高速地發展,但這些通過海量采樣而得到的視覺資源絕大部分都被應用于娛樂產業。在人們依舊爭論攝影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的同時,立體攝影卻連同被拍攝對象一起被自覺地排除在外。禁錮在立體空間中的被攝者因此失去了回視的所有可能,即使在照片下方寫著姓名以及拍攝地點,他們還是面臨著與維多利亞時期立體照片中人物相同的被歸類為劇場角色的危險。
3 風景的稀缺
在W.J.T.米切爾討論帝國主義與風景話語之間關系的文章《帝國的風景》中,米切爾主張把風景理解為一種文化表述的媒介,而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在這些照片里面,自然風景是稀缺的。米切爾在《帝國的風景》中對毛利雕像[4]的精彩論述,為對風景的理解開辟了新的道路,甚至在面對“風景的缺少”的時候,依然提供了解讀的可能——風景的稀缺隱含著擔憂與堅決的情緒。
如上文所言,這些立體照片來自于一位外籍(對于朝鮮人而言)攝影師,它們是在官方的邀請和陪同下所拍攝的,這個項目的目的是在朝鮮境內進行展覽和對外宣傳,我們可以認為這些照片是由攝影師和邀請方共同完成的,在取景的方面,攝影師與邀請方互相迂回的過程尤其令人著迷。在作品里,被攝的對象他們工作、學習、生活的城市角落得以被展示,整潔和嚴肅的人造環境作為重要的線索貫穿了幾乎所有的照片(見圖3)。風景從一開始就似乎不在考慮的范圍之內,拍攝計劃幾乎都是圍繞城市開展的。馬蒂阿士敏銳地感知到這一點,他對“真實性”的渴求,驅使他遠離城市,前往更偏遠的農場進行拍攝,他希望得到未被精心布置的場景。在那里,勞動者的外套終于被風掀起一角,泥土也終于沾上他們的防水靴。作為交換條件,自然風景成為被遮擋的對象:丘陵被紅頂白墻的農村民居切斷了,農用牽引車的引擎進氣口仿佛正在吸入遠處的土地,山脈被閱兵時的朝鮮人民大學習堂的微縮模型所阻隔。馬蒂阿士鏡頭里的風景展現出了另外一種被忽略的真實狀況——對未被人造物所界定的領土的擔憂與執著。
一方面,被攝對象似乎被禁止生活在非勞作區域,在宣傳的語境下,人們聚集在一起進行生產才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宣傳者在面對“無人”看守的領地時,則必須證明其擁有改造與管理的能力。于是我們習以為常地以風景作為背景的照片反而成為了矛盾的集中點,它們最后轉化為在鄉間拍攝時陪同人員臉上的不耐煩的表情,并成功地縮短了馬蒂阿士在那里的拍攝時間[5]。
4 過去的嘗試
除了《3DPRK》,馬蒂阿士此前曾進行過一個名為“時間記錄者”的立體拍攝項目。這個項目于2012年開始,2014年完成,有約50個來自中國安徽黟縣的家庭被馬蒂阿士以立體攝影拍下。在這個項目中,村民家庭中的鐘表和家中老人的面孔作為拍攝對象,紅藍立體照片被放置在一本復古封皮的圈裝活頁相冊中。與《3DPRK》不同,這本立體攝影書的觀看需要戴上一副紅藍立體眼鏡,這種觀看方式為觀者留有手捧相冊細細觀看和翻頁的余地,亦對應了對家庭相冊的指涉。從材料的使用和拍攝對象以及呈現方式上來說,馬蒂阿士可能是一位懷舊主義者,把這個結論引申到之后的《3DPRK》上面的話, 在他的眼中,朝鮮應該是一種奇異的平行時空:他出生在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走訪了古巴、俄羅斯等國家,并長期居住在中國,對于他來說,朝鮮的地位無疑是重要的,他所懷念的過去在這片土地上神奇重現了。羅蘭·巴特關于電影截圖的短文著作《第三意義》[6]中指出,攝影中有顯義和鈍義,如果《3DPRK》的顯義是作為異域風情的懷舊觀賞方式,那么隱含在這些照片里的另外的意義很有可能是馬蒂阿士對他所經歷的共產主義國家的追憶和迷思。
5 結語
馬蒂阿士在《3DPRK》中對真實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失敗了,他希望得到展現的個性被掩蓋在緊張的情緒之下,而立體效果也并沒有為真實性帶來任何保證,反而成為一種娛樂手段,這個作品最后成為了邀請方與攝影師共同選擇和生產的奇觀。在展覽和發售會上,好奇的人們沉溺在立體效果與現實的轉換以及馬蒂阿士對拍攝過程的講述,“真實性”在這種情況下變成了自我安慰藥,被凝視的對象在欺騙大腦所生成的視覺幻象中無法言語亦無法行動。
但值得指出的是,馬蒂阿士并非威爾遜爵士般的殖民者,主要的他者化的行為并不是由他進行的。如美國批評家普萊斯(Mary Price)所提出[7],照片的影像能產生怎樣的意義,取決于與它相關的口頭闡述以及它被使用的環境。在以新奇視覺為賣點的展覽和新書發售會上,談及后殖民主義的話題總是會令人尷尬,但無論如何,這種語境之下所誕生的奇觀,仍然需要我們對其抱有警惕。
參考文獻:
[1] Sir David Brewster. The Stereoscope; Its History,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with Its Application to the Fine and Useful Arts and to Education[M]. London:J. Murray.1856:74.
[2]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M]. London:SAGE, 2002.
[3]Liz Well等.攝影批判導論[M].傅琨 左潔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7.
[4]W.J.T.米切爾.帝國的風景.風景與權力[M].南京:譯林出版社,1987.
[5] Matjaz Tancic.3DPRK- Photographing North Korea[O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Wf55kcp2w.2016.
[6]羅蘭·巴特.第三意義——關于愛森斯坦幾格電影截圖的研究筆記[J].李洋,孫啟棟,譯.電影藝術,2012,000(002):102-108.
[7]瑪麗·普萊斯.照片:一個受限的奇異空間[M].帕羅奧多: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