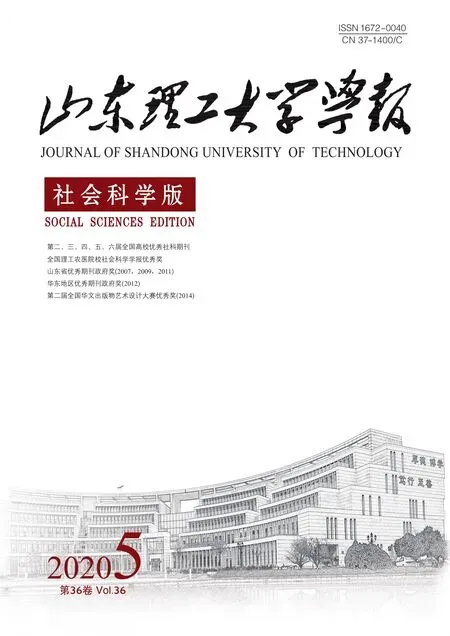齊音正聲
——《詩經·齊風》音高探索
李紅云, 陳曉宇
《詩經》一直以來備受文人、學者、樂者的追捧,它是中華傳統文化瑰寶,是五千年文明遺留下來的精神食糧。《詩經》的音響效果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形態,現如今隨著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復蘇開始逐步進入到人們的視野當中。畢竟原始的曲譜文獻和文物沒有遺存下來,而留于現世的詩經曲譜只有宋元明清時期的,例如:宋代趙彥肅的《風雅十二詩譜》、元代熊朋來的《瑟譜》、明代朱載堉的《鄉飲詩樂譜》、清代乾隆主持編纂的《詩經樂譜》和邱之稑的《律音匯考》都是對《詩經》音樂的描述,《詩經》的音樂形態到底是什么樣的?留存現世的詩經樂譜是根據音律原貌的“文人加工”?還是根據中國審美的“文人創作”?能否把春秋時期的經典文化恢復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所述:“《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1]這對研究詩經的音樂曲體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本文從清代《欽定詩經樂譜》出發,根據宮廷雅樂的制樂規律倒推《詩經》的旋律,以此來探索《詩經·齊風》的音樂形態,為齊地音樂文化的繁榮和發展提供一點新鮮素材。
一、文獻探索:現存樂譜
2019年夏天,在山東濟南的大明湖畔,山東省圖書館尼山書院開設的國學講堂舉辦了一場公益講座,宣講人臺灣南華大學周純一教授在與陳曉宇老師的交流中提道:“中國自古至民國時期,總感覺有一個線在串聯著整個中國音樂體系,音樂的種類雖然繁多,但基本的變化和繁衍都離不開一個穩定的生律系統。”[2]倘若,我們運用古代統一的生律系統去解釋和分析這四個朝代的樂譜,再結合日本遺存下來的“唐樂”、韓國遺存下來的“宋樂”等,能否探詢到春秋時期《詩經》音樂的一點味道,就像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格爾茲所講的:“文化存在于文化持有者的頭腦里,整個社會的每個成員的頭腦里都有一張‘文化地圖’”[3],我們按照這個地圖的表示向后轉,能否看到春秋時期的《詩經》原貌,這是一個值得探求的道路。
距離我們最近的《詩經》曲譜是1788—1789年間完成的《欽定詩經樂譜》三十卷,外加《欽定樂律正俗》一卷。作為當時的皇帝乾隆視《詩經》為中華雅樂之源頭,并認為前朝的樂書不足以說明其音樂的容貌,雖旋律略有變化但節奏尚奉行“一字一音”,特命皇子大臣去重新編撰《詩經》樂譜,從《詩經》的文義來制定宮調,按照康熙皇帝編撰的律制來進行標注——康熙十四律,重新核對詩篇,根據“文義”并用“某宮某調”來注明詩譜,力求接近古代雅樂的審美思想。本文從律學角度出發,研習歷朝歷代的律制,并重新解讀《欽定詩經樂譜》中的《齊風·十一首》,力求用清代的樂譜去置換中國的傳統律制得以還原出詩經樂譜。
二、實踐:《齊風》音高
在武漢音樂學院鄭容達教授的《康熙三分損益十四律解》一文中說道:“陳萬鼎先生認為:‘清制十四律,是因管律的音階而引起,每兩個半音構成一個全音,便有十四個半音,已不是舊制中的五音(全)二變(半)。這種音樂理論,是清朝特有的。’陳先生認為,清朝宮廷用的音樂都是由全音構成的,沒有半音、全音之分。他根據七聲中相鄰二聲相距二律,主觀上認為二半音已變為二全音。”[4]而鄭榮達先生則認為:“‘其數三分損益兩極于十四’的具體寫照,原注中‘正律十二,合變律二,故謂十四’一說,更是已經完全說白了。現在可以肯定地說,康熙主張的十四律,是有序而規范的‘三分損益十四律’。”[4]倘若,我們按照此律的解釋方法來重新解讀此樂譜我們就會發現許多與現代音樂專業不相吻合的音樂線條,與我們記憶中所相識的中國音樂在譜子的音高和調高認知方面有差異。而《欽定詩經樂譜》中的《齊風·十一首》是清朝皇家建制,按照所謂的黃鐘還原,用十四音律的方式結合“十二律呂”“工尺譜”并存的方式來確定每首的具體調名,并分別記錄其音高,但由于中國音樂的古代記譜與現代記譜的理念不同,容易忽視中國古代記譜中的多樣性,在復原南宋雅樂的過程中田耀農教授認為:“在古今音樂觀念中雖然都十分重視旋律的音高規定,但中國古代音樂觀念更加重視旋律音高的絕對性,黃鐘的標準音高概念比西方的標準音概念甚至早出兩千多年。”[5]古代之所以將經典的音樂傳承下來,就是“標準”——絕對音高無太大變化,我們可以從文獻入手,按照中國古音階:1.2.3.#4.5.6.7的角度著手分析, 把康熙十四律的解律手法融入到《欽定詩經樂譜》中,就可以看出《齊風·十一首》的大概面貌。此處翻譯所得到的譜例僅為絕對音高,而呈現的旋律線條的形態是否準確還有待文物的考證,這是因為“中國古代音樂追求同中有變、和而不同,同一母體與眾多變體共存是音樂作品群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用輪廓式的記譜法適應一曲多體作品群的生成需要,不僅不是古代記譜法的原始落后,而是充分體現中國古代音樂旋律學理念的智慧所在”[5]。為了一窺《詩經》的音樂面貌(參見圖1),特此用最簡單的記譜方式翻譯出來,具體如樂譜1-11所示。

圖1 清代《欽定詩經樂譜》局部

樂譜1 雞鳴

樂譜2 敝笱

樂譜3 東方未明

樂譜4 東方之日

樂譜5 甫田

樂譜6 還

樂譜7 盧令

樂譜8 南山

樂譜9 猗嗟

樂譜10 載驅

樂譜11 著
三、余論
清代的《飲定詩經樂譜》只是當時皇家的擬創之作,“康熙十四律”也一直存在爭議,到底是陳萬鼎先生的解讀正確還是鄭榮達先生的解讀正確還有待于考證,就像周純一先生所云:“歷史的痕跡散落于傳統的繼承,如何有序地把這些繼承排列起來才能窺知一二。”(1)周純一于2019年10月被聘為山東理工大學客座教授和山東理工大學齊國雅樂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表述是周純一教授在與該校教師座談時提到的。所以此次翻譯的音高曲譜并不能反映出《詩經·齊風》的真實音樂面貌,但畢竟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對《詩經》進行全面譜樂的樂譜,尤其是代表著皇家,雅樂系統一直存在于宮廷當中,由此我們也可以管窺清代雅樂審美特質。當然在《齊風》音樂研究過程中,根據文獻要盡可能做到對所研究的對象進行細致的分析和合理的解讀,此篇志在于對音高和“絕對聲響”的探索,畢竟中國古代音樂是靠腔調來運行的,由于此類研究文獻相對薄弱,對于整體音樂形態的研究尚在進行當中,后續將從古音和潤腔的角度再對此進行探析。